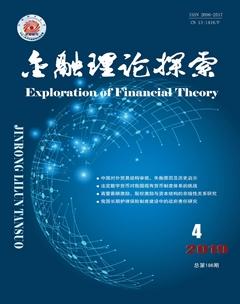南京國民政府初期農村高利貸研究
唐傳炳

關? 鍵? 詞:高利貸;南京國民政府;農村
中圖分類號:F832.9?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2096-2517(2019)04-0073-08
DOI:10.16620/j.cnki.jrjy.2019.04.008
高利貸是阻礙近代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貧窮,農民不得不借高利貸,又因為無法償還高額利息,農民更加貧窮。長期以來,學界對近代農村高利貸制度都有所關注,但所研究的區域過大,非西北即江南,沒有以某一具體地區為例,立足于該地區農村的現實狀況研究高利貸問題。本文以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河北省為例,試圖從高利貸產生的原因、具體運作形式及特征,以及高利貸產生的影響等方面做一系統探討。
一、 高利貸產生的原因
1928年6月28日直隸省改為河北省,并撤銷京兆特別區域,將所轄20縣并入河北。同時將省、道、縣三級改為省縣二級管理,河北全省共轄131縣[1]。南京國民政府初期,河北省農村經濟凋敝,高利貸盛行,究其根本,有以下原因。
(一)天災人禍的破壞
天災為自然災害,不可避免。民國時期的中國經濟落后,戰亂不已,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薄弱,無法有效地抵御災害。據1928—1934年的統計,全國遭災多的縣份占總縣份的50%強[2]。1925年8月2日《申報》報道:近日大雨后,各河暴漲,京漢路沿線,如農樂鎮、北通縣、彰德村等處河堤農田被水淹沒或沖毀,致莊稼損毀[3]。“近日大雨連綿不止,永定河沿岸村莊,又告水災,京兆以西各村落,全浸在水中,幾為最重災區。水深五尺有余,農田淹沒,人畜死傷亦多,其余如大興、宛平等十九縣被災,亦在八九成。統計二十多縣已報被淹村莊,損失財產一千六百零二萬元,死傷無數,尚未統計確切數字”[4]。民國18年(1929年),夏秋之交多雨,河水漫決,50
余縣受災。8月,張北縣陰雨連綿三四日,河水驟漲,兩岸之地沖毀無余。除了水災對農業造成了巨大損失,旱災同樣對農業產生了巨大的破壞。民國17年(1928年),華北大旱,河北省全省春夏之交,雨水稀少,天氣亢旱。寶坻縣禾苗枯萎,并成龜裂大縫,寧河縣春季所種田禾枯旱,昌黎入春夏不能耕田[5]。據《通縣水利志》記載,民國時期有旱災的年份有1920年、1922年、1929年、1930年、1934年、1935年、1936年等十年。 其中1920—1922年和1934—1936年為連續三年干旱[6]。尤其是1934年的特大旱災, 通縣受災田地面積占到了總田地數的80%,高粱、玉米、谷子、棉花、大豆等農作物較平常年收成分別損失了39%、40%、53%、32%、37%[7]。因災荒而導致餓死、淹死、自縊等死亡的不計其數,樹葉、樹皮、稻糠等平時廢棄喂牲口的都被視作珍貴的食物。災荒過后,農民借高利貸以過活,于是高利貸便活躍起來[8]。
人禍,指兵災匪禍。兵災所造成的災害有雙方交戰時造成的災害和士兵劫掠滋事造成的災害。南京國民政府初期, 發生在河北省的戰爭有1927年閻錫山改懸國民政府旗幟后的晉奉戰爭、1928年國民黨新軍閥的伐奉戰爭、1930年各路軍閥反蔣的中原大戰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種農民武裝暴動[9]。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三省淪陷。1935年,日軍攻破長城要隘,占領了河北省大部分地區,農民慘遭日軍殺戮,莊稼被毀壞,土地荒蕪,房屋農具被燒毀損失不計其數。加之國民政府多年的“剿共”內戰,使得農村經濟遭受了極大破壞。經濟落后,社會控制乏力,導致中國成為了匪患肆虐的沃土。南京國民政府初期,一些土匪、地痞、流氓,趁混戰之際占山為王,殺人越貨。規模較大的土匪有張成德(綽號“夜貓張”),招收四周的小股土匪盤踞,販賣大煙,沿路搶劫財物,騷擾百姓[10],給農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二)租稅的盤剝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繁重的地租與政府的苛捐雜稅成了農民身上沉重的負擔。據1934年的統計,河北省實物地租占租地產值的比例為52.9%[11],即一半還多的收獲物都要歸地主所有,再除去繳納政府的賦稅之外,所剩無幾,碰上荒年甚至連飯都吃不飽,因此不得不去向地主借糧。 地主們往往巧取名目提高利率,“每借一斗,年利三升至五升,每借一石,年利五斗至八斗,小斗借出、大斗還入”,除此之外,還以“借青苗、白濟洋”等名目額外征收農民地租[12]。地主對于無力繳納押租的佃戶,要其寫立借票,出息借貸,于翌年夏秋收獲季節后一并償還[13]。如果地主的剝削是一道還能讓農民喘口氣的枷鎖,那么政府的苛捐雜稅則是壓倒農民的一座沉重的大山。根據北通縣1930年財政收入的統計,僅稅收的種類就有地丁、升科糧、軍餉租、買契稅、牲畜牙稅、當稅、契正稅、注冊稅等44種稅收,該年共征得稅款146? 453? 797元[14]。由此可見,農民的賦稅不僅種類多,稅率高,且政府能夠依靠其權威強行征稅。“農民在這樣的繁重賦稅下如何能不貧窮, 如何能不仰賴借貸以維持生活,這是給予高利貸發揚滋長的一個良好機會”[8]38。
(三)婚喪禮俗的浪費
在人們“好面子、講排場、重禮節”的心理作用下,婚喪嫁娶、祭祀等活動鋪張浪費不可避免。費孝通認為造成鋪張的原因是人生禮儀的約束,即“當一種禮儀程序被普遍接受以后,人們就不得不付出這筆開銷, 否則他就不能通過這些人生的關口”[15]。況且中國男女比例失衡,娶妻難,造成了婚姻成本高。“婚嫁富者不重其財,貧者則視家資厚薄與男女年齡而講聘金多寡,男長女幼則聘金特多[16]。”為維持情面,宴請酒席更是一筆巨大的開銷。河北民間鄉村的宴席之禮,受京津兩城市的影響較大,宴席以碟盤組成,碟為下酒小菜,盤為正菜佳肴,通常為“七碟八碗”,即七個涼菜,八個熱菜。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酒席檔次也不斷升級。甚至富裕的人家要擺起“二十四大盤和三十六大盤”[17]。除了婚嫁,喪禮和祭祀禮也非常繁瑣。“人死寢床于堂內,家人哭往五道廟中燒紙,延僧做佛事,男燒紙轎騾車,女燒紙轎牛車……”“正月元旦,設香燭、果餅拜天地,祭祖先;初二日,備酒肉祭祖于堂;十五日,備元宵、燃花燈、放爆竹祭祖……”婚喪、祭祖鋪張的陋
習成為農民沉重的負擔,成為其負債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家庭副業的衰落
家庭副業是農業的輔助, 能增加農民的收入,在遇到災年農業欠收時可以幫助農民家庭暫時度過經濟上的難關。但是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國門被打開,家庭副業與世界市場的聯系日益增強。“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以來,機械勃興,生產技術為之一變,農村副業在此重大壓迫之下,自然日漸褪色,而逐漸衰退矣”[18]94。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到了20世紀30年代,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勢頭急轉直下,農民收入急劇減少。以影響最大的手工織布業為例,河北省1928年土布年產量為2533萬匹,1931年降到了1834萬匹[19]。素來以土布外銷的通縣,這一時期也出現了銷售危機,“通州出產之人工手織土布,向以銷售東三省之官莊為大宗, 自去年九一八事變后,日商竭力傾銷機制之瀛布,致通布被退,營業停頓,布商雖設計競爭,但去路極微”[20]。“七七”事變后,高陽縣棉布業一落千丈, 鄉間各村因遭戰禍和水災,棉紗來源完全斷絕,集日上市棉布不到100匹,線不足400斤[21]。除此之外,農業的經營不能完全依賴人力,尚須有若干資本投入,如購買肥料,修治溝渠,飼養耕牛等,而現金的缺乏又阻礙再生產的進行,農民被迫走上一條借高利貸進行農業生產的道路。
除天災人禍、租稅盤剝、婚喪禮俗鋪張浪費、家庭副業衰落等原因外,土地缺乏、農業生產力低下、賭博吸食鴉片等不良嗜好、銀行等現代金融機構未普及也造成了河北省農村高利貸的盛行。
二、高利貸的具體運作
據1934年的統計, 合作社及銀行借貸在河北農民借貸來源中占比不過15%強, 其余85%全部來自于高利貸[22]。對河北省農村產生影響最大的有兩種借貸形式,即信用借貸和抵押借貸。
(一)借貸的形式
1.信用借貸。是指建立在信用基礎上不需要抵押品的借貸。 如河北定縣,1929、1930、1931年,信用借款分別占借款總額的58.8%、65.8%、68.5%[23],信用借貸占多數。 信用借貸多為小額貸款,如河北薊縣,百元以下的借款就多為信用借貸。 平谷縣及通縣的信用借貸也是在百元以下[24]。印子錢即為信用借貸的一種, 因賬目以印為記號,印章代表還款數目,故稱為印子錢。經營印子錢的印子房都為獨資經營,組織簡單,家庭內部夫妻子女便能經營一個印子房。放印戶的資本在創辦時為數甚少,多者不過150大洋,少者僅250枚銅元,且資本來源不一。 借印戶到放印戶家中借款,如果不認識則請熟人擔保介紹,稱為“中保人”。第一步當面商定借款數目,根據借印戶自行決定;第二步商定還款期限,有60天與100天2種,供借印戶選擇;第三步,商定每天應還的利息;第四步為“過錢”,即借100枚,實付98枚,或借100枚,實付96枚;第五步為立折子,即相當于今天的借條,書明放印戶、借印戶、擔保人、借款總額、借款期限、每天應還之數目[24]59-60。根據1932年河北定縣的調查表明,中保人多是“村中好管閑事者,平素有人緣,愛聯絡,會講話,熟悉地方情形。他們對于各家情況、買賣田地、收入支出,甚至一切瑣碎的事情,了如指掌”[24]16。河北順義縣沙井村,村長楊源在縣城開作坊,常利用關系為村民介紹貸款,欒城縣寺北柴村、昌黎縣侯家營村,村長或村副在村中也常做借貸的中保人[25]。還有一種常見的信用借貸即為私人債,意為只要有錢就可放貸。私人債放款分三種,一為鋪保水印,借款責任由鋪保擔負;二為代還保,可托朋友當中信用較好者代為還保;三為信用放款,既無抵押品,又無鋪保人保,純以信用為主。與印子錢一樣,私人債的資本額較少且來源各不相同[24]59。
2.抵押借貸。在河北、山西的錢莊貸款中,抵押貸款雖然只占4.4%, 但在抵押貸款中農民卻占了96.8%,說明農民向錢莊借錢,抵押借貸的比例非常大[26]。當鋪抵押在民間較為常見,“典當,亦稱當鋪或押店,舊中國以收取衣物等動產做質押,向勞動人民進行放貸的高利貸機構”[27]。抵押當局放貸,一定會收抵押品,抵押品的價值、放款手續、抵押品的保管、期限、利率等都有嚴格規定。抵押品檢
驗完后,其當價以低于物品價值為準則。容易保存的物品當價高,肯定會贖回的物品當價高,容易賣出的物品當價高。抵押品價值即定,則可書寫當票,編號登記,管錢的學徒將錢拿出,并將當價登記在錢賬上。抵押品收入號房之后,必須分類保存,皮、棉類容易潮濕的放在貨架上,不怕潮濕的,則放于底層,每年舉行兩次“過風”①。借貸人贖當時由柜員接票,校對字號、品色、當本,然后將當票放在桌上,檢查無誤后借貸人支付本利即可帶走抵押品,柜員將本利計入錢賬。當物種類以衣服最多,次為金銀首飾、古董、農具等。在通縣的6家押當局中,一天收當物品647件,其中衣服514件,占79.4%;首飾95件,占14.7%;其他雜項僅38件,占5.9%[24]169。除物品抵押,以人口抵押的情形也不少。在河北豐南縣,借債者如無抵押品時就以給債主做工抵償,視債額多少商定做工的時長。在清苑縣,人工抵押的條件非常苛刻,借貸者必須“身強力壯,可以勞動”[28]。在鹽山縣,有的借債者則把子女抵押給債主做傭人,如期滿無力還債,債主就將其子女作為自己的長期傭人或轉賣他人。有的借債者在借債時把子女典當給債主作奴隸或童養媳,如期滿無力還債,債主便將人占為己有或出賣[29]。除了人口抵押外, 典當土地也是常見的一種抵押方式。出當的土地由債主耕種,種地無租糧,借錢無利息。典當土地的價格各地不同,在河北定縣,價值400元的5畝田地,得當價150~200元。清苑縣,有的村子典當價一般為土地價值的60%[28]14。
(二)借貸的利率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河北省農村的借貸利率計算方式各不相同, 且利率變動趨勢多為增長之勢。據河北226村的調查, 年利2分以上者占總村數的83.2%,5分以上者達12.8%之多[30]。臨城縣月利至少3~5分,甚至有借洋1元,月付息1角者[31]。深澤縣普通借款利率為四五分[32]。阜平縣,即使沒有殷實的商號作鋪保,有田房作抵押,利息也得3分、5分、8分,甚至有1元每天1大枚至3大枚銅元②的高利[33]。河北的典當業中,當鋪月利多為3分左右。樂亭縣為2.5分,豐潤縣平時3分,年終2分,玉田縣3.7分,靜海縣本金1元每日利息8分,月利達24分之多[34]。由此可見農村高利貸利息之高。
不同的利息計算方式、還息方式在農村有不同的稱謂。錢債有“大加利”之說,如太行山鄉村又稱“老一分”“十利”,即借1元,月利1角,10個月本對利。甚至有“加十五”“大加二”,即10個月期限,利錢高至150%~200%。河北贊皇縣稱“加五利”,亦名谷利,即借糧1斗還1斗半,且須“尖還”,即平斗借尖斗還[35]。“利滾利”,即屆期不還,以利作本,重計利息,逐期滾算,利息學中稱作“復利”,是債主規避風險的一種有效方式。在河北稱為“臭利蟲”,形容其繁殖過速[36]。另外還有借多付少,即債主付給債戶的數額比約定本金減少, 債戶償還剩余利息和全部本金。此種借貸在河北鹽山縣稱為“回頭扣”,借8元按10元還本付息,有的稱為“九出十歸外加三”,即借9元作10元,月息3元,每月還本利13元[29]468-469。北通縣則是先扣利,提前扣除利息。債主先扣留第一個月利息,如借120元,先扣月利4元,只出116元,或者借120元,10個月為期,月利4元,利息共40元,一并扣留,只付債戶80元,到期還120元[24]93。不僅各種克扣,且利率呈現逐年增長之勢。安國縣100元現洋1月限利3~5元,漲至7~8元;安次縣農民以往借債過年,花4分便可周轉,1932年即以紅契作抵,利達6分;臨城縣1929—1933年,利率也逐年上升,借30~50元,月利由1929年的2%增至1933年的6%[37]。
由表1可知,河北省農村高利貸年利率普遍在30%~60%, 部分地區年利率已經達到了驚人的360%、1080%,利息之高可謂驚人,老百姓所受壓榨可謂之重。 大部分農村高利貸利息都是按月計算,由于民國時期戰亂頻仍,高利貸風險較大,因此高利貸的借貸周期較短。而且有無抵押品對于利息高低起到了決定作用。雖然按月計算利息的方式比較普遍,但在具體放貸過程中,各縣鄉村的手段不一,有少出多進,也有先將利息一并扣留,其目的都
是為了變相克扣,剝削農民。且部分農村年利率增長的速度驚人,令本就處在高利貸重壓之下的貧苦農民生活更加困苦。
(三)借貸的期限與償還
根據《農情報告》雜志1934年的記載,河北省鄉村借貸期限以6個月至1年為最多,合計在1年以下的占比達到了貸款期限總數的91%,可見貸款時間之短。農村的經濟本就貧困不堪,加之民國時期兵荒馬亂,土匪橫行,社會治安沒有保障,縮短貸款期限成為了債權人規避風險的一種方式。河北定縣,根據1929—1931年的調查,在借入次數與借款總額中,都以期限10個月為最多,達到了50%,期限短的僅有1個月,最長也不超過1年。因農村經濟不景氣,償還能力降低,1932年以后,借款期限超過10個月的逐漸減少,6個月以下的不斷增多[23]17。在各種借貸來源中,當鋪的期限比一般私人借貸期限長,河北各縣當期都在1年以上,樂亭縣、昌黎縣、豐潤縣、寧河縣當期分別為2年、18個月、3年、2年[38]。借貸期限短對農民頗為不利,短期內農民難以籌集現金或實物償還, 一旦到期不還,就將失去抵押品或遭受利滾利之剝削。另外,期限短也不利于農民增加農業投資和提高農業生產力[39]。對于印子錢的還債戶, 到了期限仍然欠款的借印戶,若信用好,可以續借,另定期限。對于信用不好的借印戶,放印戶則不得不打錢(向其討債),放印戶需攜帶底賬、印色、戳記、錢袋這四種東西。借印戶多為無積蓄的貧困者,故打錢的最好時間為每日下午有收入之后,冬季為下午3點至5點,夏季為下午4點至7點。對于無款可付的借印戶,則毫無情面可言,立即索取抵押品,以免有所損失。押當局在抵押品10個月期滿以后,若不贖取,稱為“死當”,其抵押品便可出售,增加資本流動。據1932年河北通縣的調查,一債主有91家債戶,不能還款者5戶,僅占總借戶的2.3%[24]105。但隨著農村經濟的
不景氣以及抗日戰爭的爆發,因貧窮、死亡、逃走不能還款的越來越多。
(四)借貸的特點
1.經營范圍小。經營高利貸的放債戶一般熟悉本地的情形及農民的狀況, 如果借款人的距離較遠,收利息與本金時會過于勞頓,增加成本,而且距離過遠,不能掌握借款人的信息,更容易逃賬。對于借款人來說,各放款戶的利率大致相同,不需要舍近求遠,且鄰近的熟人多便于借款時作擔保,因此,借貸經營范圍較小。
2.借款人多為貧苦農民。根據吳志鐸在北通縣第一區的調查,借印戶共有35家,其職業主要為泥瓦匠、人力車夫、沿街叫賣者,小攤販、做針線者。私人債的14戶借債戶中, 收支相抵和家有余款的各只有2戶,入不敷出的占到了10戶[24],他們都是社會最底層人物,沒有固定的收入,缺乏生活保障,對高利貸的依賴性強。
3.放債風險大。高利貸是民間金融組織,缺乏法律的保障,放債戶猶如賭博,需要孤注一擲,風險極大。眼力所及,必須隨機應變,審查入微,放印子錢不收抵押品,卻比有抵押的更可靠,賭的就是眼力,需要觀察借債戶的家庭情況、生意狀況,比如放印戶有“生人不借、澀債不借、有錢者不借、戚友不借”[24]106四條不成文規定。
4.利率高克扣嚴重。印子錢的利率為120%,甚至更高,本利合算,按日攤還,假設放印戶有10元本金,一年利息收入可達56.76元;私人債的利率為“三分三”,每1元合月利三分三厘三毫;押當局的利率以月為單位,每月三分。各種高利貸利率之高甚為驚人。放印戶借款時,還有“過錢”一說,有借100枚,實付96枚、98枚的,也有扣除1份或3份底子錢的,重重盤剝,到了農民手上所剩無幾。
5.高利貸放款額度小、期限短。由于民間高利貸不具有合法性,風險大且利息高,因此造成了高利貸每次放款的額度較小。印子錢的放款額度多者10元,少者只有200枚銅元,一元二元為最普通的額度;私人債額度稍高,也僅限于千元以內;押當局放款則要依據抵押品的價值,又因為抵押品多是一些衣飾,所以放款額度最多也不過十數元[24]133。由于民國時期戰亂,農村經濟衰敗,農民償還高利貸的能力逐漸下降, 民間借貸期限多為6個月至10個月,因此借貸期限極為短暫。
三、高利貸的作用與缺陷
(一)延續簡單再生產
高利貸是一種經濟活動,是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個環節,對于維持農民的生命延續和簡單再生產有一定的促進作用[39]110。從農民借貸的原因來看,高利貸多用于農民因天災人禍而維持日常生活,購買日常必需品,婚喪嫁娶,交租交稅等。高利貸可以使農民暫時度過經濟上的難關,農民的生存生活得以延續。此外,一小部分借貸用于購買種子、耕牛、農具、土地以及副業生產,為家庭經濟的創收提供了資金來源,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北通縣的農民鄭貴就是一例,鄭貴家中只有9畝旱地和1間灰頂房,屬于貧農。鄭貴有“濃厚的發財傾向”,手頭沒有現金就借錢買地,雇短工耕種,秋后還債。因其經營得法,生產效益較高,經營規模逐漸擴大,土地不斷增加,到土地改革前夕,已有旱地38畝,2套膠輪大車[39]190。可見, 高利貸一定程度上能填補現代農村金融奇缺的空白,對農民的生產生活起到救急的作用。
(二)造成農民破產
高利貸在短期內能幫助農民緩解暫時的經濟困難,但農民不得不承受高利貸的高額利率。對于農民來說,其收入的很大部分被債主剝削而去,“農民負債利息之支出,大都等于甚或超過其土地生產量之全額,駢手胝足辛苦一年之所得,償還負債本息尚感不敷”[40]。高利貸“似此層層剝削,不啻三四連乘,始則乘人之危,因人之難,債權者尚博市惠之美名;繼則債務者,售業變產,賣男鬻女,猶難避免其債臺;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40]58。首先,大量債戶的土地被高利貸者掠去,“對于高利貸業,它一般是利用來作為其兼并土地的幫手”[41]。在借貸時,農民往往以土地作為抵押, 高利貸到期無法償還時,土地就歸放貸人所有。 其次,為了償還債務,有人甚至賣房賣女。1932年一佃戶為了償還高利貸,變
賣了5間土屋,僅夠還本,又將9歲的女兒給債主作童養媳,用所得禮金才還了利息[42]。最后,有的高利貸債要求債戶以人工作為抵押,債戶不能如期還債,就為債主做工償還, 視債額多少商定幾年不要工錢,還清債務為止。 有的甚至將妻子兒女送去給債主當傭人, 加強了債戶對債主的人身依附[39]112。最終導致債戶的債務危機進一步加深,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流行各地的民謠表達了農民對高利貸者的痛恨。如河北清苑縣的農民流傳“八斗九年三十石,十個騾子駝不完,二十五年整一萬,升升合合還不算”[28]16。
四、結語
在銀行、 信用社未普及的南京國民政府初期,農村金融機構以民間高利貸為主。 河北省天災人禍、租稅盤剝、婚喪嫁娶的鋪張浪費以及家庭副業衰落等原因使得高利貸行業在該地區盛行。一方面,農民日常的生產生活離不開高利貸,高利貸起到了維持生活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高利貸的高額利息,在度過短暫的危機過后,農民們不得不賣房賣田、 賣兒鬻女來償還高額的利息,最終導致破產。農民因此陷入了貧窮——借貸——更加貧窮的惡性循環, 有的甚至同時背負好幾種高利貸,往往借此貸還彼貸,從而加劇了農民生活的貧困以及農村經濟的衰敗。“只有建立和完善現代金融組織和制度,才是活躍農村金融的根本出路”[30]26。
參考文獻:
[1]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河北省志 民政志[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04.
[2]楊捷先.中國農業倉庫之興起及其評價[J].中國經濟,1935(10):3.
[3]京漢沿線各地被水淹沒[N].申報,1925-08-02(10).
[4]京兆水災之損失[N].申報,1925-08-04(5).
[5]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河北省志 自然災害志[M].石家莊:方志出版社,2009:51.
[6]北京市通縣水利志編輯委員會.通縣水利志[M].北京:北京市通縣水利志編輯委員會,1993:62.
[7]民國二十三年全國旱災調查:(3)冀晉陜三省旱災損失估計:甲:河北省各縣受災面積及作物損失數量與價值[J].農情報告,1934(11):3-5.
[8]余椿壽.高利貸產生之原因及其影響[J].農林新報,1936(14):36.
[9]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河北省志 軍事志[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438.
[10]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河北文史資料 第37輯[M].石家莊:河北文史書店,1991:174.
[11]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303.
[12]也平.農村研究:救濟農村金融問題[J].紡織世界,1936(8):28-29.
[13]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中國經濟年鑒1934-1936[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90.
[14]通州區史志辦公室.民國通縣志稿[M].北京:通州區史志辦公室,2002:76.
[15]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94.
[16]徐白,等.通縣志要[M].臺灣:成文出版社,1968:357.
[17]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河北省志 民俗志[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141-142.
[18]管盂.華北農村金融枯竭問題與農村副業[J].中聯銀行月刊,1943(3):91.
[19]從翰香.近代冀魯豫鄉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368.
[20]通州土布官莊銷路斷絕[J].紡織周刊,1932(43):1225.
[21]高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高陽縣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125.
[22]高利貸之盛行[J].農情報告,1934(11):21.
[23]李景漢.定縣農村借貸調查[J].中國農村,1935(6):13.
[24]吳志鐸.北通縣第一區平民借貸狀況之研究[M].北平:燕京大學經濟學系,1935:102.
[25]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152.
[26]實業部國際貿易局.中國實業志(山西省)[M].實業部,1937:34.
[27]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291.
[28]河北省統計局.28年來保定農村經濟調查報告(1930-1957)[J].中國農業合作史料增刊,1988(2):12.
[29]張愛國.鹽山縣志[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469.
[30]鄭槐.我國目下之鄉村借貸情形[J].農林新報,1936(6):14.
[31]錢俊瑞.目前農業恐慌中的中國農民生活[J].東方雜志,1935(1):6.
[32]吳半農.河北鄉村視察印象記[N].益世報,1934-03-31(5).
[33]李小平.阜平農村素描[N].益世報,1934-11-30(8).
[34]蔡斌咸.救濟農村聲中之典當業[J].新中華,1934(15):7.
[35]魏宏運.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M].北京: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1361.
[36]田文彬.崩潰中的河北小農[N].益世報,1934-04-27(3).
[37]遠.河北省一個農村的經濟調查[J].中國經濟,1934(8):6.
[38]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中國農業金融概要[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93.
[39]李金錚.借貸關系與鄉村變動 民國時期華北鄉村借貸之研究[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83.
[40]劉征.民國時期甘寧青農村高利貸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06:58.
[41]王亞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0.
[42]顧猛.崩潰過程中之河北農村[J].中國經濟,193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