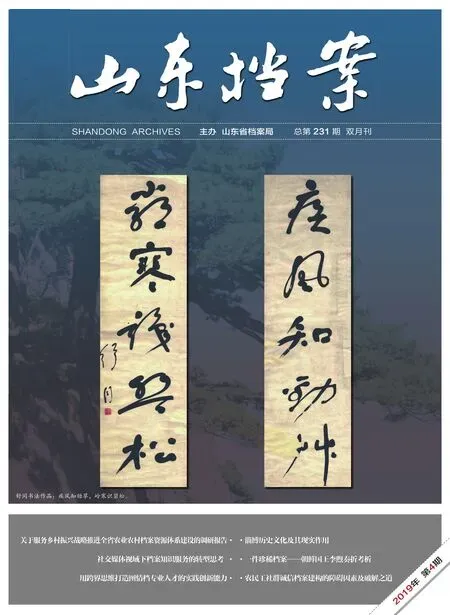農民工社群誠信檔案建構的障礙因素及破解之道
文·楊歡歡
我國農民工群體的數量持續增加。據2019年2月發布《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8836萬人,[1]比上年增加184萬人,其中約占60%的1.7億農民工屬于跨省務工,構成了農民工群體這一流動人口群體的主流人群。實現2020年“全國范圍內自然人信用記錄的覆蓋”[2]的目標不能忽視農民工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但農民工群體面臨著誠信公德意識、素質技術水平、法制觀念欠缺的質疑。農民工誠信檔案不僅僅是農民工行為約束的一紙契約,更是其權益保障的清白憑證。在為農民工提供身份和誠信證明的同時,引導農民工主體身份認同的產生。農民工誠信檔案建設具有必要性,卻存在實踐難點。
一、農民工誠信檔案的內容
農民工是指戶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區別“外出農民工”和“本地農民工”的標準是其戶籍是否在所在鄉鎮地域之外或之內[3]。綜合學界近年討論成果,參考ICE8000國際信用標準體系標準中對個人信用檔案內容的規定[4],將農民工誠信檔案內容總結如下:(1)基本身份信息:姓名、性別、出生日期等;(2)從業相關信息:職業技能鑒定證明、上崗再培訓證明等;(3)信貸交易記錄;(4)用于申請社會救助、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政策的居民家庭經濟情況;(5)社會保險參保繳費信息;(6)犯罪記錄。
二、農民工誠信檔案建設的障礙因素
(一)建檔主體的障礙因素
經過訪問調查,將建檔主體障礙總結為四點。(1)職業特點:農民工流動性強,其個人信息更新快、搜集困難,流動時攜帶誠信檔案不便,可能造成誠信檔案遺漏、丟失等問題。(2)自體差異:不同類型的農民工群體在知識文化水平、專業技能素養、職業價值觀上存在較大差異,集中統一管理難度大。(3)心理層面:一部分農民工對被貶抑和偏見化的“農民工”概念存在抵觸情緒,不認同自己的農民工身份。出于對個人隱私泄露、失信懲戒的顧慮,部分農民工對建檔的設想不夠支持。
農民工誠信檔案的內容也可能來自農民工以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然而這些相關者采集的信息各有區別,他們作為農民工誠信檔案的建檔主體也各有優勢和缺陷,如表1所示。

負責社會救濟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工會組織[5],社會保險協議服務機構[6]居民家庭經濟情況,身體健康狀況,參保繳費信息農民工配合積極性高,信息更新及時檔案信息收集需要相關部門協調配合,管理不夠規范檔案行政部門及各級各類檔案館、博物館身份信息、文化狀況、培訓經歷、技能特長、求職經歷[7],勞動合同、工資單、欠條、假錢、工傷證明、超長加班記錄、罰款單、暫住證、被收容證明等[8]民生檔案政策幫扶,具備檔案管理人才及經驗物理空間局限很難做到檔隨人走
(二)客體層面的障礙因素
一是農民工誠信檔案有機聯系屬性的保障障礙。從實踐的角度來說,農民工在社會生活中的各類誠信行為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應被割裂看待。然而實際工作中往往難以做到。原因有三:一是大多數農民工沒有固定的單位,很難將農民工誠信檔案按照其來源(形成單位)和原有次序進行收集、區分和整理。二是農民工誠信檔案的形成者并非唯一,已收集到的誠信信息零散分布在多個形成主體手中。三是農民工的流動性強,各項信息的更新和保存困難,檔案信息丟失遺漏的風險較大。
二是農民工誠信檔案征信全面完整要求的完成障礙。我國規范征信活動的法規僅有一部2013年3月15日起施行的《征信業管理條例》。該條例禁止個人病史信息、個人收入、證券、房地產信息和稅收等信息的采集,除非明確告知當事人提供該信息可能產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其書面同意[9]。條例對于征信活動中產生的文件、資料的收集起止時間并未作出明確規定。如果農民工本人不配合不良信息的征信農民工誠信檔案就很難收集到完整的誠信信息,主體的誠信狀況有可能存在時間上的斷層。
三是農民工誠信檔案開放利用需求的滿足障礙。誠信檔案必須開放可獲取渠道,能夠為公眾查詢、查證和利用,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國際信用標準規定應該公開免費查詢個人信用檔案的公開內容……按征集規則的有關規定處理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信息[10]。目前我國一些法律法規的部分條款對收集、使用、披露個人信息等行為作出了相關規定。但是法規對于涉及隱私的信息與可以公開的內容的概念界定和區分仍不夠明確具體,對于公民主體主動支配個人信息、控制隱私不被擴散的權利則較少提及。在實際工作中,包含農民工個人信息的檔案一般被“限制公開”。
三、農民工誠信檔案建設障礙的破解之道
(一)意識:提高農民工的主動建檔意識
一方面,“農民工”并非該群體自主命名,群體對此稱謂缺失身份認同感。另一方面,被檔案工作者冠以“邊緣化”的名義實際上反而更加重了他們的邊緣化。[11]因此,應加強檔案教育宣傳,幫助農民工認識到:誠信檔案有利于幫助農民工實現平等就業,為其爭取權益提供系統規范的憑證依據,記錄下他們建設城市過程中完成市民化的記憶。儼然已成為農民工群體社會融入的“名片”,求職就業的“敲門磚”,維權護益的“保障卡”,群體自信的“光榮榜”。
(二)方法:探尋多主體合作方法
雖然農民工主體對群體建檔尚無明確強烈的意識,但政府和學界對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問題表現出了高探索性和高承諾性,積極致力于農民工理想身份的實現。[12]作為檔案服務國家治理的創新形式,農民工社群誠信檔案的建立首先離不開政府主導并提供政策、資金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借鑒現有國內外社群檔案項目經驗,檔案部門和檔案工作者可逐步由建檔實踐先行者轉變為管檔輔導合作者,引導農民工社群自主建檔,為其提供業務指導。利用現有誠信檔案平臺,各利益相關者應緊密合作,推動誠信數據庫資源的整合與共享利用。
(三)原則:靈活應用來源原則
“尊重來源”,更多地是在強調文件檔案原有形成主體較其他形成主體更為優越的權力和地位。但當檔案形成主體不唯一,難以辨別哪一主體作用更突出的情況下,更應“尊重過程”,平等地看待檔案共同形成主體在構建檔案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重視社會記憶構建中多元主體所形成的話語,深入挖掘、剖析檔案中相關敘述所體現的多元檔案背景,進而歸納出誠信檔案中的聯系。農民工社區成員加入其個人誠信檔案的鑒定、整理及著錄過程,有利于加強他們對自己重新檔案的重視,配合各部門的工作,合作共同完成誠信檔案形成的全過程,減少農民工主觀上輕視個人檔案、“棄檔”現象的發生。
(四)內容:補充完善其他專門檔案
我國國家衛生計生委定期會組織全國性的流動人口健康狀況調查,尤其重視公共場所內從事餐飲工作的農民工健康狀況的記錄與更新。我國社會保障機構統一用社會保障管理系統管理地方社保人員的相關檔案信息。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內容詳實豐富。除國家民生相關的行政及事業單位,部分社會研究團體開展的針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調研項目都能夠補充農民工誠信檔案的內容,起到完善充實的作用。
(五)規則:細化明確誠信檔案開放利用規則
信用信息處于大數據環境下,農民工在網絡平臺上的借貸等金融活動、社交等業余生活的記錄等,在沒有被法規界定是否涉及公民個人隱私之前,可能就已經被廣泛傳播并利用了。為及時修改完善實際工作中不合理的利用條款和制定違規利用農民工誠信檔案的懲罰措施,首先需要盡快在衡量公共利益和隱私保護的前提下界定農民工個人誠信隱私范圍。其次,增強對農民工的個人誠信信息自決權的保護。例如,盡快在相關法規中落實農民工本人對自己誠信檔案的查閱權、不實信息的舉報權等。
四、結語
農民工誠信檔案的構建有利于誠信社會的完善,改善農民工群體身份邊緣化的現象,以誠信檔案為載體,豐富農民工集體記憶。本文從農民工誠信檔案的構建所涉及的主體、客體出發,分析了農民工誠信檔案的實施難題,并針對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意見,以期為社會流動人口誠信檔案體系的構建工作貢獻微薄力量。但單學科觀點難免有失偏頗,農民工誠信檔案的研究可以同智慧城市建設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有效促進勞動力的高效輸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