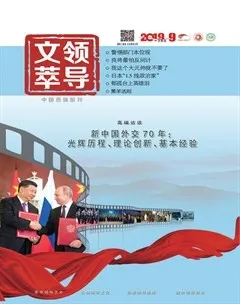中國經濟:突圍與抉擇
周其仁
中國該如何突圍
首先是靠改革突圍。中國的改革,總是在沒辦法的時候,被逼到了墻角才真正推動的,因為改革是要觸動利益的。要不是餓到糧食供應不上,怎么會同意包產到戶?要不是幾億人的就業沒法解決,怎么會開放民營經濟?
改革開放40年了,我們是否真的把改革開放這件事從制度、法律、文化、思想上想通?依照我的觀察,還沒有。
我們絕不能只要形勢一好,就忘乎所以,甚至對我們在國際競爭中的位置作出脫離實際的判斷。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國際競爭中,我們還沒有形成獨到性的優勢。如果沒有長期的艱苦奮斗,我們是無法成為世界前沿國家的。中國還只是一個人均GDP 9000美元的國家,但社會上已經出現未富先奢的苗頭,形勢一轉好,就自我得意。我們要看到,在稅收結構、國民經濟分配構造中還存在各種失衡;連續增長的稅收與我們的發展階段和國力水平還存在不相匹配的地方……需要靠改革實現突破,實現突圍。
其次是應對戰略突圍。我認為,這兩年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不能因為特朗普在國內壓力下收縮,我們就也跟著收縮。中國以更大的開放來應對貿易摩擦的戰略是正確的。
對中國而言,在改革開放中的收益遠遠大于它所帶來的成本。如果不繼續開放,中國下一步的現代化是不可能找出一條關起門來自己發展的路的。這個問題一定要清醒,要繼續堅持開放。開放是改變不了的,沒有哪一個行政權力有能力把這種局面再拉回去。全球分工帶來的全球生產力的提高,是未來全球福祉的基礎。特朗普繼續鬧下去,說不定會導致一個相反的局面——全球關稅有可能繼續降低。美國以提高關稅開的頭,最后有可能以繼續降低關稅結局,當然這要看協商各方怎么去看這個問題。
這兩年我看了不少基礎設施,從上海港一直看到鹿特丹港,全球的大船越造越大,單位成本中的貨物轉運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技術的變化加速了中國公司在全球布局。我看,特朗普還有一個貢獻,就是把一批中國公司打成跨國公司。不可能全世界都收25%的關稅,哪里不收,我們就到哪里布局。我訪問過一批中國公司,很多都是貿易摩擦后加快了全球布局。它們去越南、去墨西哥等地開公司,逼出了一批跨國公司。
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我們的抉擇 ?
面對新的國際局勢,中國需要有新的全球觀,不要糾結于某個國家與另個國家之間的所謂“貿易戰”。國別政治這種東西很容易上新聞標題,但今天的世界不完全如此,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當下,全球化雖然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從根本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各國都從全球化中得到了好處。統一的市場,有分工、深化,生產率得以提高,這是人類未來福祉的可靠基礎,這個趨勢是擋不住的。
中國現在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圍住了,被我們的成就圍住了。之所以被圍住,是因為我們真的有兩下子了,夠一定份量了。問題是,我們要挺得住這一關——被圍住了就要突圍出去,要改革突圍、開放突圍、創新突圍。
至于在這場突圍中有沒有勝算,比較好的答案是“不確定”。突不出去的話,無非就起個名目,叫它什么“陷阱”算了,有多少國家都是到了臨門一腳,踢不出去了。中國的大歷史上也發生過這種事情。比如宋朝,在當時看來已經具備了一切進入現代化的條件,但臨門一腳卻踢不出去,裹足不前,停在了門外。這也是研究中國科技史的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李約瑟的一個問號。
那么這一次會怎么樣?很有希望。我們從那么窮的一個國家變成現在的世界第二大,人均GDP水平從兩三百美元上升到九千美元,可以說中國現在是歷史上離成為現代化偉大國家最近的時候,但沒有人能保證我們一定贏。
看看歷史就知道,不是第二大都變成了第一大。從戰后算,第二大變成第一大的只有美國,前面的幾個第二大都是往后面走了。并不是像做算術一樣,中國現在第二大,多推幾年就是第一大了,上帝沒有給出這種保單。這要取決于我們的努力,取決于我們的抉擇——政府怎么做,企業怎么做,還有高校怎么做。做得對,是一個結果,做得不對,則是另外一個結果。
如果非要坐下來說我們的前景會怎么樣?我愿意把寶押在我們的突圍能夠成功這一面。道理在哪里呢?因為我觀察中國經濟,觀察我們國人,有一個明顯的文化心理特點,就是形勢差的時候我們的表現會比較好,甚至是形勢越差,表現越好。什么時候形勢好了,我們的表現也比較好,那就是中國真正進入世界強國的一天。
(摘自《改革內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