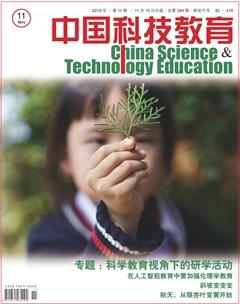諾貝爾獎對中國科學界的啟示
鄭永春,博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副理事長,青年科學家社會責任聯盟理事長,“科普中國”形象大使。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秋天是收獲的季節。每年的10月是諾貝爾獎公布的時間,但因為評獎標準不同,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經濟學獎有時候會引起較大的爭議,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等自然科學類獎項,卻很少引起爭議,因而備受科技界認可。
關于諾貝爾獎的新聞報道在社交媒體已經鋪天蓋地,不管平時是不是關注科技,都注意到了相關報道。哪些人獲獎了?新聞媒體已經作了很多的報道。因為什么成果獲獎?各領域的專家們都已經作了詳細解讀。這些都不用我再贅述,我更關心的,是從這每年一次科技新聞傳播和科學普及的盛宴中,思考諾貝爾獎對中國科學界的啟示。
首先是對不同學科專業的啟示。諾貝爾獎雖然重要,但并不能涵蓋科學領域的方方面面。各個科研領域和不同的學科專業,都有各自受認可的方式,諾貝爾獎不應該成為整個科技界追求的唯一共同目標。比方說,諾貝爾獎并沒有設置地球科學獎,也沒有設置數學、計算機和信息科學方面的獎項,這些領域有各自廣受認可的獎項。計算機和信息科學領域最受認可的獎項是圖靈獎,數學領域最受認可的是菲爾茨獎等。而且,諾貝爾獎重點表彰原創性的基礎科學發現,技術發明也不在獎勵之列,發明大家愛迪生就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而且,我們看到,公布諾貝爾獎獲得者時,只公布他們的獲獎成果,并沒有說這些成果發表在哪些權威期刊上。因此,努力在本學科領域做到前幾名,在本領域得到認可,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追求的目標。再延伸一點,用論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評價一個科學家或一項科研工作,實在是本末倒置。因為不同學科和研究領域的期刊,影響因子差異很大,科研發現的重要性、論文中的原創性貢獻,才是評價科研成果的關鍵。
其次是對設立科技獎勵的啟示。諾貝爾獎自1901年12月10日、諾貝爾逝世5周年時首次頒發以來,歷經100多年的積淀,才有了今天在全球范圍內廣受認可的影響力,堪稱科技獎勵的皇冠,備受社會各界追捧。但一項科技獎勵的聲譽,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絕不是只靠巨額獎金就能砸出來的。2012年設立的科學突破獎,單項獎金300萬美元,遠超諾貝爾獎,堪稱科學界“第一巨獎”。2016年起由中國科學家和企業家發起的“未來科學大獎”,單項獎金100萬美元。2019年騰訊基金會首次頒發的“科學探索獎”,每位獲獎者資助300萬人民幣。雖然獎金都很豐厚,但這些科技獎勵相比諾貝爾獎而言,都還很年輕,需要數十年的積累,才能建立足夠的影響力和美譽度。因此,一方面,改府需要積極鼓勵和引導民間資金和社會力量設立科技獎勵,改變科技獎勵只由官方認可的現狀。對于由企業和社會出資設立的科技獎項,需在稅收方面予以扣減。另一方面,要建立獨立、公正的評獎機制,既要獎勵過去,錦上添花,對科技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終身成就,要通過頒獎予以承認;更要獎勵未來,雪中送炭,對具有極強創新欲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及時給予扶持。只有足夠的耐心,才能建設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和延續百年的科技大獎。
第三是對普通科技工作者的啟示。諾貝爾獎獎勵的往往是獲獎者幾十年前取得的成就,從目前的頒獎情況看,大多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取得的成果。這次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發現第1顆環繞類太陽恒星的系外行星的瑞士天文學家,是1995年做出的成果,已經是非常快的獲獎速度了。某種程度上,發現系外行星的成就,與哥白尼的日心說可以比擬,都是改變人類世界觀的重大成就。日心說證明我們的地球在太陽系中并不特殊,系外行星證明宇宙中可能有無數個“地球”。獲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古迪納夫,已是97歲高齡,創下最年長獲獎者的紀錄。很多人用他的名字Goodenough開玩笑,認為要獲諾貝爾獎,不僅科研要做得足夠好,還要活得足夠長。當然,這跟諾貝爾獎的性質有關,諾貝爾獎是終身成就獎,不僅要有重大發現和原創性貢獻,而且還要經歷很長時間的充分驗證。
為此,應大力營造認真做事、求真求實的科研作風。既要有天馬行空的暢想,又要有腳踏實地的行動。不少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經歷,給了我們很多啟示。這些科學家在獲獎之前很少被公眾所關注,似乎是一夜成名,但翻看他們的科研經歷不難發現,他們首先都是兢兢業業的科研工作者,都經歷了幾十年的刻苦鉆研。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要永遠保持對科學的熱愛,永遠保持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這才是科技工作者最寶貴的素質。今天可以出現在領獎臺上,明天應該繼續回到實驗室里。畢竟,科學研究才是科學家的生命。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做國家有需求、社會有用處、個人感興趣的研究。如果不是熱愛,就很難堅持下去。
今年的諾貝爾獎,又沒中國人什么事。很多人又開始反思,為什么日本在18年內獲得18個諾貝爾獎,而如果查閱去年的文章,就會發現“日本17年獲17個諾貝爾獎”的啟示。這樣的標題,明年改改數字,還可以接著再用。于是乎,似乎中國科學界可以以日本為師了。但是,創新道路千萬條,條條道路都不同,無論哪一個國家的成功經驗,都是無法完全照搬和復制的。作為一個泱泱大國,既要有向世界先進學習的胸懷,又要有矢志不渝的定力。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過分自信。
第四,要淡化對諾貝爾獎獲得者個人的關注,保持平常心。地方改府、各類科技平臺和科研項目等,不應以引進諾貝爾獎獲得者、設立院士工作站等方式造勢,而應注重實實在在的科研績效。以我的觀察,與其引進到處走穴、徒有虛名的名人大家,不如引進創新意識強、真正能干活的科研骨干,實際效果也要好得多。引進幾十位有潛力的年輕科研人員,花錢比引進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更少,綜合回報反而更豐厚。畢竟,每一項實驗和研究,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個體做出來的。推動科學的進步,既要有天才式的科學家作出突破性的貢獻,同時也要有步兵式的科技工作者在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經過長期努力,一點點獲得新進展。畢竟,愛因斯坦式的人物不常有,但一個個科研工作者,每天進步一點點,最終也能攻下一個堡壘。
最后,也是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要營造崇尚科學的氛圍,要認識到科學的發展需要經歷長時間的積累。2019年是代表現代科學的“賽先生”進入中國100年,重視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的現代科學,與中國古代崇尚實用的傳統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人類對未知世界的了解是逐漸建立起來的,一個民族對人類知識庫的積累貢獻越大,這個民族就越能贏得尊重。那種認為科學沒用,或者一定要問有什么用,實際上是對科學最大的誤解。因為,讓未知變成已知,就是科學對人類最大的功用。
從某種程度而言,現代科學在中國屬于舶來品。我們國家從事系統性、連續性科學研究的歷史還不長,而且期間還經歷過很長時間的斷檔,從1978年“科學的春天”開始,經歷的時間還只有短短的41年。隨著時代的進步,迫切需要重建新的科學文化。但科學文化的建設,崇尚科學氛圍的營造,都不是一日之功。各級科技主管部門要在改善科研環境上下功夫,營造人盡其才的氛圍,要關注他們能否放開手腳創新,鼓勵年輕人通過努力脫穎而出。科研人員也要養家糊口,“板凳要坐十年冷”不是一句口號,要讓科研人員能靜下心來刻苦攻關,就要關注科研人員的薪資水平,能否讓他們衣食無憂,要關注他們的獲得感和成就感。播好每一粒種子,養護好每一顆幼苗,到了秋天,自然就會有收獲。
獲得諾貝爾獎當然是好事,但獲不獲獎不應該成為中國科學界最重要的追求目標。中國科學的發展,要以追求原始創新和影響社會發展作為目標,凡是能夠改寫或寫入教科書,能夠影響人類世界觀,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成果,都是重要成果。享譽世界的霍金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卡爾·薩根沒有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屠呦呦沒有當選院士,這些絲毫都不影響他們對科學和人類的貢獻。
多發揚自身的優勢,多反省自身的不足。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我們理應保持定力,求真求實,努力走出屬于自己的中國特色科技創新之路,就是諾貝爾獎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