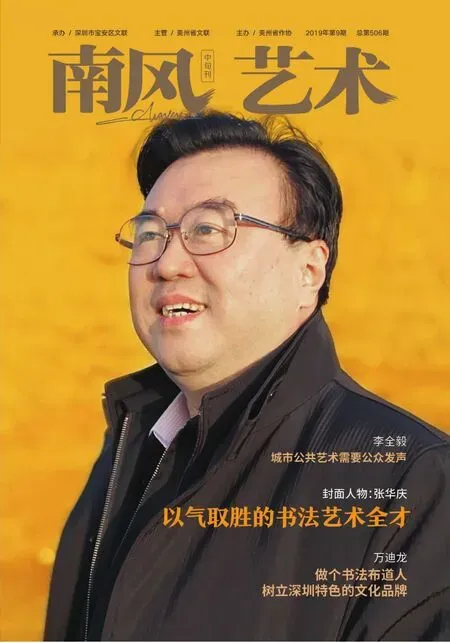縱向切入的斷面呈現:碎片、關鍵詞、話題、詞條
文/謝端平
蕭相風這樣解釋《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以下簡稱《詞典》)的創作:“是生活碎片化的結果。不單是與現代工業相關的生活,其實現代社會的一般生活是瑣碎的、混沌的。盡管在全媒體時代,人們了解更多聽到更多,但是生活充滿了關鍵詞。”“一開始,我寫了一個‘打工’詞條,作為第一個詞條自然牽引出另一個或兩個,就這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詞典了。其實散文形式更適合用詞典的形式。同時,我借用ISO標準中系統文件的做法,在各詞條間建立聯系。”“每一個詞條都是一個話題,我的想法是如何將個人經歷與公眾話題相互結合。”(見《蕭相風:記錄詞典中的南方》,《中國改革》2013年第4期)從碎片到關鍵詞再到話題進而形成詞條,四十六個詞條中除了ISO、QC、走柜等幾個詞條屬于外延較廣的工業生活外,其他皆與打工生活有關。《詞典》對打工生活進行了高度概括和升華,不僅是了解深圳的一個窗口,而且對整個時代,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數以億計的以打工為目的的人口流動,作了非常精細的記錄,正如2010年度人民文學獎非虛構作品獎的頒獎詞所稱:“從無可置疑的個人體驗出發對這個時代工業生活做出了大規模表現和思考。”
在《詞典》中,打工不再是生活所迫的結果,而是在工業中勞作和生活的自然存在,就像柴米油鹽一樣實在,有苦必定也有樂。這種對待打工生活的態度在打工作家中是非常特別的,難能可貴的。“集體宿舍”詞條中老賈覺得集體宿舍挺好,經常帶老婆來睡覺。“我”回來后細想,這個老賈也真的是集體慣了,大概喜歡在集體宿舍里吹牛海侃,可以和眾工友窩成一圈斗地主,順便可以和老婆開火車。至今“我”覺得他的手勢很瀟灑:“各位兄弟,沒事!將就了。”詞條結尾將一首詩送給流水拉,似乎流水拉是他的故友或新朋。陶潛歌頌田園,彭斯歌頌土地,哈亞姆歌頌美酒,李白歌頌大自然,而蕭相風歌頌以流水拉為典型物象的工業生活,每個時代都有獨有的文學,也都有獨有的作家。對一些不平等或不合理社會現象,《詞典》作了獨到的分析,“摩的”字條中摩的是窮人的工具,也方便了大眾,摩的禁止后升級版和低碳版電動車上路,“我”坐電動車和三輪摩托車的經歷有驚無險并充滿趣味,“我”斷言摩的無法在珠三角大地上消失。

蕭相風對詩歌情有獨鐘,著有《中國現代詩歌普及十講》,自印詩集《噪音2.0》。《辭典》中穿插了他的四首詩,用婉轉曼妙的詩意化的語言,表達了他自己對南方工業生活的深切感受。“這樣詩化的語言,是一種寫實中的親切與堅韌的魅力。”(見《體驗的現場/讀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文藝爭鳴》2011年第3期。)很多詞條就是充滿激情的詩,“技術員或扳手”詞條中扳手不再是冷冰冰的鋼鐵物品,而與他相融、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扳手是一件多么詩意的工具,在詩歌中我多次使用到它,我用它拆掉那些陳舊的比喻和繁冗的句式,再擰緊我身體里那些松動的螺絲。”他在一線生產員工崗位做了五年多,后來做的管理工作也與一線生產緊密關聯,見慣了太多的鋼鐵設備,這些設備在他筆下都成了溫暖的存在,賦予了生命和活力。“螺絲只是機器里無處不在的助詞,不,是連詞。也不,是標點符號。螺絲構成大工業,構成世界的存在。”“每天不斷地彈動,受壓,再彈回,彈簧被賦予了最堅韌的品質。”“機油又是另一個溫柔的元素。”“流水拉”詞條有考據有見聞,并聯想到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和唐詩宋詞里欸乃一聲的漁船,動情吟詠:“在流水線上沒有轉折符號、頓號和逗號,流水線就是一篇沒有標點符號的文言文,甚至一氣呵成而沒有句讀。” 試圖對工業生活作出概括,必然要涉及丑惡事物,可《詞典》刻意隱惡揚善。“老鄉”詞條歌頌了純潔的老鄉情:“在異鄉的土地,我們似乎找到了一盆家鄉盆景,大家共同的方言聚在一起,攏成一片故鄉的云。”“老鄉是一個出門在外的生詞,一雙漂泊異鄉的布鞋,一頂土祠或公社時期的破帽氈,是一粒臨時抵御鄉愁的安定。”該詞條堅決否定“老鄉老鄉,背后一槍”說法,認為放槍是人性問題,與是否“老鄉”無關。
《詞典》致力于記錄與表現,以素描手法臨摹現實或真實。蕭相風自稱進行了“縱向切入”,“非虛構作品與小說相比,它的取勝點在哪里?虛構的魅力是多么不可抗拒,對于作者而言,可以大開大合,選擇不同的敘述視角,利用豐富多樣的技法,揮灑自如而淋漓盡致,結構自己的文本;對于讀者而言,可以在閱讀期待中獲得更多的傳奇、巧遇和戲劇性。而非虛構呢?的確,非虛構作品的魅力是真實,但是難道僅僅在于真實嗎?如果這種真實沒有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真實就會淪為一種平庸的真實。在立足于有限真實的基礎之上,它需要作者更多的藝術構造能力和付出。撇開寫作能力不談,首先需要在取材上獲得較大優勢,這是決定非虛構能否成功的首要條件。盡管現實生活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題材,但是如果不與之主動建立廣泛而巧妙的聯系,作者就無法自覺地發現美、成型美。因此,‘介入’和‘行動’成為目前非虛構作品的關鍵詞,行動力也就被提上了日程。”(見《從〈詞典:南方工業生活〉出發》,《文藝報》2011年4月20日) 《詞典》是來自內部的書寫,表現之一是作者身處“內部”,二是以“內部”的姿態,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審視。“‘現場’,在這里是一種被記錄的‘現場’,而這種記錄,又是體驗中的記錄,故這種現場感的獲得,是記錄現實與體驗現實相結合的產物。‘行動’,顧名思義,是要以實際行動代替‘書齋式’的空想,代替一葉障目式的書寫,離開數字化、電子化的媒體和信息來源,到真實的‘現場’去體驗、去感悟、去書寫,用‘行動’進入文學的‘現場’,再用‘非虛構’的方式把這種原生態或者說粗糲的‘現場’體現出來。”“他以自己豐富而典型的打工經歷為主要內容,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的南方工業生活場景,一個他所親身經歷的南方工業生活的場域。這種極具‘現場’感的敘說,讓我們感受到一種真摯的生活體驗、蓬勃的生命氣息、向上的進取與探尋狀態。正像有人所說的,蕭相風不是到現場去,而是本身他就浸泡、裹挾在這種工業生活中,對生活是零距離的感悟。” (見《體驗的現場/讀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文藝爭鳴》2011年第3期)
一直以來,打工文學存在“概念化”的問題,但《詞典》基本上走出了概念化的泥淖,人物和故事情節復雜多樣,打工生活豐富全面,看法比較客觀,并帶有一定的歷史觀。“打工詩人”詞條中批評了打工詩歌中普遍存在的“苦難敘述”嗜好:“大概不直白、不憤怒、不宣泄苦難就不是打工詩歌,甚至在部分打工詩歌界內部也形成這樣的認識誤區。”“打工作家”詞條這樣分析:“有趣的角色轉換讓打工作家有別于傳統作家,即創作者與創作對象是同一的,自己寫自己。打工者寫打工者的生活,無需他人代言。”“保持自己的個性和生活的血性,是打工作家必須堅持的一點精神。進步和包容不是向某個方向媚俗。” 打工文學至今已經35年,打工作家作了多方面的探索,《詞典》以別具一格的方式縱向切入改革開放,切入工業生產現場,切入打工生活,切下的碎片(細節和觀點)金光閃閃,組成的關鍵詞林林總總,建立的話題沉重而新鮮,成就的詞條各有春秋。賀紹俊認為《詞典》是“非常有創意的一部作品,不遜色于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詞典》在打工文學史上具有象征意義,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意義將更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