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的典故與翻譯
金其斌
網絡會話中的流行詞語“呵呵”想來大家都不陌生。2012年華東師范大學的一篇碩士論文《網絡會話中“呵呵”的功能研究》更是助推了“呵呵”的知名度。目前,該文在中國知網已下載30,100次,被引17次(2019年5月27日檢索)。李倩把“呵呵”的功能總結為:輕微的贊同,更多時候是禮貌的反對,模糊的不置可否,避免尷尬的虛假應和,轉移話題的狡黠伎倆。(李倩:《回鍋肉和香菇菜心的語言等級》,商務印書館,2015,P148)
“呵呵”雖然興起于網絡,實則古已有之。對“呵呵”的源起,錢鍾書、陳寅恪使用“呵呵”的典故(更時新的說法叫“段子”)以及“呵呵”的翻譯作一番梳理,筆者認為很有必要。
“呵呵”的集大成者首推蘇東坡。看來林語堂給蘇軾所列的19個頭銜,應再加上“段子手”一項。
《蘇軾全集校注》中,《與李公擇十七首》《與錢穆父二十八首》《與文與可三首》《與王定國四十一首》《與趙德麟十七首》等45篇文章都寫有“呵呵”。蘇東坡曾給因“河東獅吼”出名的好友陳季常寫信:“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呵呵。”意思是只要晚上睡得舒爽,寫詞只是小意思。中國蘇軾研究會副秘書長劉清泉感嘆說:“‘呵呵一詞大多出自蘇軾與友人的書信,和朋友聊天常常‘呵呵一笑,其含義和現在差不多。他的‘呵呵笑聲,穿越千年時空,如今似乎仍然余音裊裊。”(楊帆:《“呵呵”竟是蘇東坡損朋友時發明的,寫信常用》,網絡文獻)
那么,“呵呵”的創造者是不是就是蘇軾呢?霍忠義一路考證,探尋“呵呵”的出處。他先是找到了比蘇軾早生201年的韋莊,又發現了比韋莊早生145年的唐代的寒山和尚,隨后追溯到比寒山出生早43年成書的《晉書》。最后,他感慨道:“如此看來,呵呵體的鼻祖就是《晉書》的編撰者房玄齡、褚遂良等人了,呵呵!”(霍忠義:《“呵呵”探源》《光明日報》,2018年7月27日,16版)
到了近代,“呵呵”則又出現在錢鍾書和陳寅恪兩位文史大家的筆下。1989年1月15日,錢鍾書在給好友宋淇的最后一封信中寫道:
然精力大不如前,應酬已全謝絕。客來亦多不見,幾欲借Greta Garbo(葛麗泰·嘉寶)“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個兒待著)為口號,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P106)
多年后,宋以朗在整理父親宋淇的書信時,有感而發:
最后那個“呵呵”,用法一如我們在網上常用的表情符號,信中流露的風趣語調、跳躍思想,實在讓人難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筆寫文言文的老人!(同上)
“呵呵”二字是錢鍾書的自我解嘲和調侃,同時也道出了錢氏與宋淇之間私交甚篤。無獨有偶,“呵呵”在史學大家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中也頻頻現身。
據陳寅恪考證,為柳如是制作弓鞋者為濮仲謙,濮為柳如是制鞋時年齡已過六十。對于明末清初詩人錢謙益(號牧齋,夫人為柳如是,又稱河東君)“晚向蓮花結凈因”一句中的“蓮花”,陳寅恪認為可作雙關解讀:
以老叟而為此,可謂難能之事。然則牧齋詩“晚向蓮花結凈因”之句,不但如遵王注本,解作結遠公蓮社之凈因,亦兼可釋為助美潘妃細步之妙跡矣。呵呵!(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270—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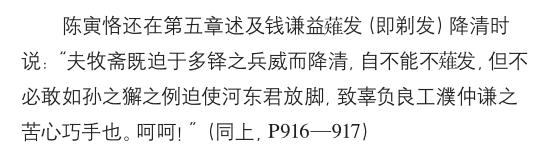
陸灝指出,陳寅恪給人的印象是個嚴肅刻板的老學究,而在其史學著作中,居然出現“呵呵”二字,可見他也不乏俏皮風趣。(陸灝:《聽水讀鈔》,海豚出版社,2014,P75)
其實,一些網絡潮語都能在歷史的長河中找到其蹤影。略帶嘲諷戲謔意味的“濕人”(“詩人”的諧音)近來在網絡語言中頻頻現身。李家真指出,拿“濕”和“詩”的諧音來揶揄詩人,并非今人的發明。晚唐詩人許渾就因詩中頻頻使用“水”字而“濕”名大噪。(李家真:《最美的“濕”意靠雨水帶來》《晶報》,2018年3月4日,B06版)
據南宋佚名作者的《桐江詩話》所載,晚唐詩人許渾寫出了許多佳句,“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許渾寫“濕”寫成了后人的話柄,但他寫的“濕”往往稱得上精彩之筆,比如已經濕了的“水聲東去市朝變”,以及將濕未濕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關于“呵呵”的翻譯,英文的“Its interesting”,可謂銖兩悉稱。馮 乾對此作了解釋:
有人嘲諷:英人說“Very interesting.”,不代表他真覺得有趣,只意味著“That is clearly nonsense.”;又或他們說“I am sure its my fault.”時,實際上等于說“Its your fault.”。這些話往往像《老子》所謂“正言若反”,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馮乾:《神級翻譯》)
“interesting”和“nonsense”畫上等號,與上文提到呵呵表示“禮貌的反對”相吻合,同時也將“呵呵”所傳達的“不置可否”和“虛假應和”的潛臺詞傳神地表達出來,用來翻譯“呵呵”,可謂再恰當不過。
馮文中關于“I love you”的文藝腔譯法,讀來也十分有趣。夏目漱石、張愛玲、錢鍾書和楊絳等文學大家一一登場,與本文“典故”的題旨相近,轉錄于此,以饗讀者:
夏目漱石曾問學生:“I love you該如何翻譯?”學生理所當然地答道:“我愛你。”夏目漱石覺得譯法太乏味,竟提議翻成“月色很美麗”。這種神翻譯也許有人會不以為然,但我卻十分欣賞──同一個意思,在不同時空,出自不同的人,面向不同的對象,都應該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因為翻譯不僅表達人生,同時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賈寶玉要說I love you,自然是:“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張愛玲也許就說:“噢,你也在這里嗎?”錢鍾書是霸氣的“我沒有訂婚”,楊絳則是坦率的“我沒有男朋友”──據聞錢、楊初次約會,雙方開場白的確就是這樣。
一句“I love you”(李連杰飾演的電影《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中戲稱為“愛老虎油”)竟然衍生出了這么多的軼事趣聞,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