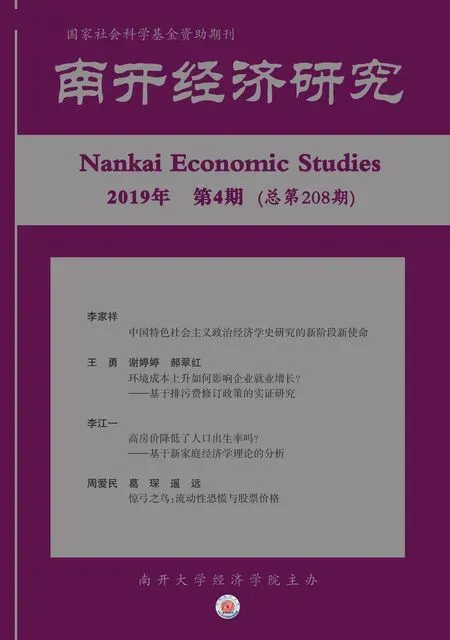驚弓之鳥:流動性恐慌與股票價格
周愛民 葛 琛 遙 遠
一、引 言
流動性是金融資產的重要特征,也是風險的重要來源。研究表明,流動性對資產價格存在顯著影響,不可分散的流動性風險是系統性風險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次貸危機以來的眾多研究表明,傳統的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存在缺陷。一方面,危機時期的資產流動性打破了均值回復性,呈現出自我強化加速下滑的特征。另一方面,投資者存在“驚弓之鳥”的特征,對可能出現的危機的恐懼,即使在正常時期也會產生風險溢價。這些特征既會對投資實務造成重大影響,也表明傳統的流動性資產定價理論仍有進一步擴展的空間。特別是2015年和2016年中國股票市場發生的市場流動性枯竭與股市暴跌,更突出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關于流動性風險與資產價格的關系問題,已有充分的理論和實證研究。Acharya和Pedersen(2005)建立的LCAPM(liquidity adjusted CAPM)是其中的代表,其將流動性成本引入投資者效用函數,從效用最大化出發,建立了包含四個 beta值的結構化定價模型。此后,Liu(2006)簡化了 LCAPM,建立了包含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兩因子模型,發現其比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有更好的擬合效果和解釋異象的能力。此外,黃峰和楊朝軍(2007)以及周芳和張維(2011)等學者均認為,中國股票市場有明顯的流動性驅動特征,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顯著優于其他傳統模型。
但若與次貸危機以來關于流動性危機和尾端風險的文獻相結合,則可發現傳統的流動性資產定價理論仍有缺陷。
一方面,極端狀況下的流動性水平和流動性風險,表現出與正常時期完全不同的特征,而具有均值回復性的傳統流動性因子不足以描述危機時的特征,可能在危機時期失效。流動性風險超過一定閾值后不再均值回復而是加速下滑,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形成“流動性黑洞”或“流動性螺旋(liquidity spiral)”,最終造成流動性危機。流動性負向的自我強化可能由以下機制造成。第一,Morris和 Shin(2004)以及郭乃幸和楊朝軍(2011)的“流動性黑洞”模型表明,當資產價格下降到短期投資者的止損線時,就會發生大規模的流動性踩踏。投資者的止損拋售造成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從而觸發更多投資者的止損操作,出現資產價格和流動性相互影響的負向螺旋,最終造成流動性危機。第二,Brunnermeier和 Pedersen(2008)發現,存在融資交易時,融資流動性(funding liquidity)和市場流動性會形成相互強化的負向螺旋。在融資融券交易實行后,這一機制在中國市場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在該模型中,市場流動性下滑,資產價格下跌時,投資者的融資能力受限,迫使其賣出資產,使市場流動性進一步下滑。第三,Garleanu和 Pedersen(2007)發現,市場低迷風險激增時,所有機構同時采取嚴格的風控措施,會進一步加劇流動性緊張。以上三個理論均表明,均值回復特征明顯的傳統的流動性風險因子在危機時期會失靈。
另一方面,投資者對可能出現的危機的恐懼,是系統性風險的來源,即使在正常時期,也存在對極端風險的溢價,存在“驚弓之鳥”的特征,而傳統的定價模型遺漏了這部分系統性風險。該思想源于 Barro(2006)、Bollerslev和 Todorov(2011)以及 Gabaix(2012)對罕見災害(rare disaster)和股權溢價之謎的研究,投資者對難以預期的極端事件的恐懼造成了過高的風險溢價。基于該思想,Bali等(2009,2014)以及Huang等(2012)發現,由 VaR、Shortfall和極值理論等方法構造的尾端風險指標,均對收益率有顯著的影響,這對傳統的資產定價模型而言是一種難以解釋的異象。Kelly和 Jiang (2014)是這一問題的集大成者,其基于冪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假設和Hill估計量構造了收益率的尾端風險因子,發現該因子對個股和市場收益率均存在顯著的解釋能力,是不可分散的系統性風險。Kelly和Jiang(2014)以及Van Oordt和Zhou (2016)均認為系統性的尾端風險在市場下跌期間對資產價格具有重要的解釋能力,相比傳統因子而言顯著增大,加入這些因子可以解決傳統定價模型在危機期間失效的問題。
綜上所述,傳統的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存在兩個重要缺陷,即難以描述極端情況下的流動性風險變化規律且遺漏了部分風險溢價,故有必要進行修正,以應對類似2015年和 2016年中國股票市場流動性枯竭的極端情況。正如趙勝民等(2016)指出,因子模型的有效程度因市場特征和投資理念而異,中國股票市場有明顯的流動性驅動特征,流動性波動性較大。這表明考慮極端情況的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有更好的適用性。
本文將Kelly和Jiang(2014)以及Wu(2017)的框架進一步推廣到中國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問題中,基于冪律分布假設和 Hill估計量構造了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相較于傳統的流動性因子,本文所構造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克服了上文所述的兩個缺陷。在實證檢驗中本文發現了以下結論。第一,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市場流動性恐慌時期顯著增強,能提前指示2007年到2008年和2015年到2016年的兩次危機,而傳統的流動性因子在危機時期并未明顯增強。第二,基于投資組合法和Fama-MacBeth回歸法,本文發現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橫截面上存在顯著的風險溢價,年化等權重組合約有9%的超額收益率,且可以消除反轉效應等傳統定價模型難以解釋的市場異象。第三,將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市場因子相結合構建的兩因子模型,對橫截面收益率的解釋力高于其他經典模型,兼顧了解釋力與簡潔性。第四,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未來市場收益率有顯著的解釋力,與 Welch和 Goyal(2008)以及姜富偉等(2011)的市場收益率可預測性框架相結合,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預測的貢獻度約為 15%。第五,由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反映了投資者的預期,且股票市場的劇烈波動可能對宏觀經濟造成影響,基于脈沖響應圖可發現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沖擊將伴隨著未來一個月產出和投資的下滑,并有未來四個月的通貨緊縮和資金面緊張。以上結論表明,本文構造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理論上完善了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深化了對危機時期流動性特殊性質的認識,也對投資實務有一定應用價值。
二、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構造
(一)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基本假設
本文構造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思路,源于 Kelly和 Jiang(2014)以及 Wu(2017)。Kelly和 Jiang(2014)最早用該思路構造了極端收益率風險因子。由于極端事件極少發生,樣本積累稀少,故估計時變的尾端風險是困難的。為解決這一問題,Kelly和Jiang(2014)假設收益率的尾端服從冪律分布,該分布的關鍵參數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個股因素決定,另一部分由市場因素決定,此時便可從日常收益率中獲得大量樣本。據此,可使用 Hill(1975)的估計方法,從個股的尾端分布中計算由市場因素決定的參數,定義為極端收益率風險因子。這一方法簡單便捷,得到了廣泛應用。
與此同時,眾多學者指出冪律分布是金融變量的普遍特征,不僅收益率的尾端服從冪律分布,流動性成本和價格沖擊的尾端同樣服從冪律分布。Plerou等(2004)發現,交易的價格沖擊的尾端服從冪律分布,故傳統的正態分布假設無法很好地描述流動性成本的尾端特征。Gabaix等(2003,2006)進一步指出,投資者的最優化交易行為,特別是大機構的行為,是形成冪律分布特征的原因。陳收等(2008)以及曹宏鐸等(2011)發現中國市場的眾多變量也廣泛存在冪律分布特征。據此,我們可以直接將 Kelly和Jiang(2014)的理論擴展到流動性問題中。
綜上所述,可以假設流動性成本的尾端分布如下:

其中Ci,t表示股票i在t時刻的流動性成本,為某一閾值,要求為信息集,參數決定了尾端分布的形狀。由于故應有保證概率取值在0到1之間。參數由兩部分構成,其中iα由個股因素決定,tλ由市場因素決定并隨It變化。
(二)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估計方法
定義tλ為市場在t時刻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則可使用Hill(1975)提出的分布尾端估計方法來估計tλ,即:

其中Ck,t是超過閾值的日度流動性成本。將每個月內所有股票的日度流動性成本帶入式(2),即可得到該月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值,Kt為月內符合條件的日觀測值的數量。在每個月內,個股出現極端低的日流動性水平的頻率越高,則加總而成的統計量就越顯著,全市場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就越大。個股的流動性水平是投資者預期和交易行為的結果,故式(2)在本質上也反映了全市場范圍內投資者的預期和交易行為,這是其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的來源。
由于冪律分布的對數服從同參數的指數分布,根據指數分布的性質可知:


三、樣本與指標定義
(一)樣本區間的選擇
本文選取的樣本區間為2005年1月到2016年12月。由于股權分置改革對流動性影響較大,且 2005年之前樣本量較少,不利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估計,故樣本時間從 2005年開始。該區間包含了中國股票市場最為標志性的兩次暴跌,具有代表性。此外,我們刪除了金融股和當年上市的股票樣本,但在穩健性檢驗中加入這些樣本后并不影響結論。
(二)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及其beta值的計算
基于式(2)可由個股的日度流動性成本計算出市場的月度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值。張崢等(2013)比較了各種度量方法在中國股票市場上的適用性,認為 Amihud指標適用性最好。該指標的計算方法如式(5)。

其中 daysi為個股月內有效交易天數。
圖1即為按以上方法計算所得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陰影區域表示數次股災,左軸為極端流動性因子值和 LCAPM 的傳統流動性因子值,右軸為市場收益率。一方面,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正常時期的波動率與傳統流動性因子相當,但在危機前以及危機時期出現劇烈震蕩,幅度遠超傳統的流動性因子。特別是 2015年到 2016年的股災表現出明顯的流動性枯竭特征,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震蕩更加明顯,這說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能更準確地描述流動性恐慌期的市場特征。另一方面,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于兩次大規模的股災具有一定的提前指示作用,提前期約一個月。特別是2015年5月出現的劇變,預示大規模的流動性枯竭即將到來。

圖1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圖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于危機的提前指示能力,可能源于其在微觀層面捕捉了投資者的預期和交易行為。當市場狂熱接近末期,投資者,特別是理性程度更高的機構投資者,對于顯著高估的股票的預期和交易行為逐漸趨同,出現“逃往質量(flight to quality)”現象。這種同質化的拋售行為使月內流動性樣本的尾端顯著增厚,從而使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出現劇變。
為計算個股對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beta值,我們用個股超額收益率與該因子的非預期變化(unexpected innovation)做了 24個月的滾動回歸。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也嘗試了 60個月的滾動回歸,結果并無區別。求因子非預期變化的常用方法主要有Pastor和 Stambaugh(2003)以及 Sadka(2006)。我們采用了 Sadka(2006)的 ARIMA模型殘差法。具體而言,我們對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序列建立ARIMA模型①基于Box-Jenkins方法最終選擇的最優模型為ARIMA(2,1,2)。,取殘差作為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非預期變化,與個股超額收益率做滾動回歸。
(三)其他變量定義
在個股層面,我們選取的控制變量包括:流通市值(Size)、賬面市值比(Bmratio)、動量效應(Momentum)、盈利性(Roe)、換手率(Turnover)、流動性水平(Liquidity)和波動率(Volatility)。在市場層面,我們參考了Welch和Goyal(2008)以及姜富偉等(2011)的市場收益率可預測性框架,選擇的控制變量包括:平均市盈率(Peratio_m)、平均賬面市值比(Bmratio_m)、市值變動率(Size_delta_m)、平均股利支付率(Dividend_m)、平均換手率(Turnover_m)、平均流動性水平(Liquidity_m)、通貨膨脹率(Inflation_m)和貨幣供應量(M2_m)。
四、個股層面的實證分析
(一)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橫截面風險溢價
為驗證本文所構造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存在顯著的風險溢價,我們首先使用單變量組合分析法。具體而言,我們在每個月將樣本按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 beta值從大到小排序,等分為五個組合,分別計算各組合持有一定期限后的平均超額收益率,最后求各月各組合的均值。若按順序排列的各組合的平均超額收益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遞增關系,且最高組與最低組的平均超額收益率之差顯著大于零,則可認為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存在顯著的風險溢價。為確保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采用了多種組合構造方法:持有期限包括1個月、3個月、6個月和12個月;超額收益率包括基于Fama-French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型調整的 alpha;加權方法包括等權重加權、流通市值權重加權和總市值權重加權。計算結果見表1。
為更直觀地展示表1的結果,我們還依據各組的平均超額收益率繪制了圖2,橫軸為五個組合,縱軸為加權平均超額收益率。

表1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個股收益率的投資組合分析
表1的計算結果顯示,在24種不同組合構造方式下,最高組與最低組的平均超額收益率之差基本都顯著大于零,表明該因子存在顯著的風險溢價,且結果非常穩健。從圖2可觀察到,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beta值與超額收益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①等權重的組合下可以保證單調性,但市值權重組合下,第4組的超額收益率往往是最高的。這可能是因為大市值的股票波動率相對較低,從而在加權后拉低了第5組的加權平均超額收益率。。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存在橫截面的風險溢價,對于傳統資產定價模型而言是一種異象。這種溢價的來源,可能是由于投資者對于流動性枯竭出現的恐懼,即使在正常時期,也會因恐懼而影響交易行為,存在“驚弓之鳥”的特征。這與 Bali等(2009,2014)、Huang等(2012)、Kelly和 Jiang(2014)、陳國進等(2015)、Van Oordt和 Zhou(2016)、劉圣堯等(2016)以及 Wu(2017)的發現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只是這些研究更加關注收益率的尾端特征及其風險溢價,而本文則是從流動性的角度入手。該思想根源于對股權溢價之謎的研究。Barro(2006)、Bollerslev和 Todorov(2011)以及 Gabaix(2012)認為,由于罕見災害難等極端事件難以被估計且危害性巨大,投資者對這類事件的恐懼造成了過高的風險溢價,即使在正常時期這種溢價依然存在,因此形成了股權溢價之謎。該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傳統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存在的缺陷,更好地描述了危機時期的特征,補充了這部分缺失的風險溢價。

圖2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個股收益率的關系圖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收益率的解釋能力是否會被其他因素覆蓋?為考察這一問題,我們進一步采用了 Fama-MacBeth回歸方法,以便引入其他控制變量。除上文所述的常規控制變量外,我們還控制了Kelly和Jiang(2014)構造的極端收益率風險因子beta值。具體而言,極端收益率因子(KJ_factor)的計算方法與上文類似,只是將流動性成本改為收益率,在每月匯總所有樣本的日收益率,基于同樣的閾值確定尾端,并使用Hill估計量計算極端收益率風險因子,并求其beta值。
表2的回歸結果表明,在加入眾多控制變量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風險溢價依舊在1個月、3個月和6個月的持有期限上顯著,這種定價能力獨立于極端收益率風險因子和其他因素,是一種全新的效應。

表2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個股收益率的Fama-MacBeth回歸分析
(二)極端流動性風險與反轉效應
能否解釋各類市場異象,是評價資產定價模型優劣的重要方面。盡管 LCAPM 模型在解釋規模效應和估值效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其能否解釋中國市場上的反轉效應仍存在爭議。如陳青和李子白(2008)認為 LCAPM 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反轉效應,但李宏等(2016)基于更廣泛的數據和更嚴謹的分析發現,LCAPM模型對于反轉效應的解釋很不充分。根據李宏等(2016)的定義,可用過去兩個月的累計超額收益率代表短期反轉效應(Reversal)。本文基于簡單的方法發現,在控制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后,反轉效應在各期限下均不再顯著,這說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可以解釋短期反轉效應,結果見表3。

表3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反轉效應的回歸分析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反轉效應的解釋能力,可能源于 Avramov等(2006)以及Nagel(2012)的理論。Avramov等(2006)認為,反轉策略的收益在本質上可視為提供流動性獲得的補償。當投資者在下跌時買入資產,即提供了流動性,并可能獲得反轉的收益,以補償其提供流動性的交易行為。Nagel(2012)發現,反轉策略的收益是很不穩定的,與 VIX指數高度相關。市場恐慌時期的抄底行為是反轉策略收益的最主要來源,因為此時提供的流動性最為寶貴,風險也最大。綜合這兩種理論即可發現,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和反轉策略收益率高度相關,反轉策略收益主要源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劇變的時期,因此在控制了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后,反轉效應不再顯著。
(三)幾種資產定價模型的對比
鑒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描述危機特征與補充風險溢價兩個方面對傳統流動性因子做了改進,以下我們嘗試基于該因子構造新的定價模型,并與經典的定價模型進行對比。正如趙勝民等(2016)指出,因子定價模型的有效程度因市場發展水平和投資理念而異。中國股票市場存在明顯的流動性驅動特征,且有較大的流動性波動性,這可能意味著考慮極端情況的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有更好的適用性。
我們分別將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加入CAPM和LCAPM中,構造了新的兩因子模型(包含市場風險因子和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和三因子模型(包含市場風險因子、流動性風險因子和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隨后根據流通市值和賬面市值比分組構建Fama-French的5×5組合。最后利用這25個組合,分別計算這兩個新模型、LCPA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以及 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的 Gibbons統計量。較大的Gibbons統計量表明各組合截距項聯合不等于零,該定價模型產生的 alpha越高,擬合程度越低,模型越差。該統計量的定義如下如式(6):

其中,t為時間序列期數,n為組合數,f為因子個數,為各組合截距項的列向量,為殘差的協方差矩陣的無偏估計,為因子的樣本均值的列向量,為因子的協方差矩陣的無偏估計,該統計量服從自由度為n和t-n-f的F分布。表4為本文所構造的兩個新模型與 CAPM、L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和 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的對比。
基于表4可得到以下結論。在各種期限下,加入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模型都明顯優于其他經典模型。將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加入CAPM和LCAPM后各有優劣,事實上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傳統流動性因子在正常時期的趨勢是基本一致的,只有在危機時期才出現較大區別,出于模型簡潔性的考慮,EL+CAPM 的形式是最優的。流動性模型的良好表現,說明中國股票市場流動性驅動的特征更為明顯。加入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新模型不僅符合流動性驅動的特征,也更好地描述了危機時的規律,故有更好的實證效果。

表4 幾類資產定價模型的對比分析
五、市場層面的實證分析
(一)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市場收益率
上文證實了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橫截面層面存在顯著的風險溢價,那么該因子在市場層面是否存在同樣的現象?該因子是否可以進一步加強對市場收益率的預測能力?下文在市場層面進一步展開檢驗。
Welch和 Goyal(2008)以及姜富偉等(2011)分別研究了美國和中國股票市場收益率的可預測性,認為估值水平、市值變化、股利水平以及通脹和貨幣供應量等宏觀變量對市場收益率有預測作用。我們在姜富偉等(2011)所選定的變量基礎上,加入了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為了與 Kelly和 Jiang(2014)的結論進行對比,我們還在其中控制了極端收益率風險因子。
我們用流通市值權重和等權重方法重新計算了樣本范圍內的全市場收益率,并取5種不同的期限。結果顯示,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未來1個月到12個月的市場收益率具有解釋能力;而在 12個月后,因子的解釋能力逐漸減弱直至消失。此外我們還計算了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和極端收益率風險因子對解釋市場收益率所貢獻的比例。結果顯示,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解釋能力的比例約為 10%到 17%,與其他經典的預測變量基本相當,且在絕大多數形式下都高于 Kelly和 Jiang(2014)的極端收益率因子,說明了該因子的重要作用和在中國市場上的適用性。

表5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市場收益率的回歸分析

續表5

續表5
(二)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宏觀經濟
參考 Kelly和 Jiang(2014)以及 Wu(2017)的研究框架,我們進一步探討了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一些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聯系。我們選擇了總產出、固定資產投資、居民消費、通貨膨脹、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 6個宏觀變量,建立 VAR模型①多數情況下的最優模型為VAR(3),個別為VAR(2)。,進行Granger檢驗,并求這些宏觀變量對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沖擊的脈沖響應圖(圖3)。
表6的結果顯示,極端流動性因子是總產出、通貨膨脹、貨幣供應和經濟景氣指數的Granger原因,表明極端流動性因子對這些變量有一定的領先和預測作用。

表6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宏觀經濟變量的Granger檢驗
圖3的結果顯示,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沖擊對多數宏觀變量都存在影響②當然,這種影響只是單純的領先滯后關系,并非因果關系。這種領先滯后關系反映了投資者的預期。。首先,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沖擊意味著總產出、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景氣指數在1到2個月的短期下滑,并在6期之后基本收斂為零。其次,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沖擊意味著未來 1到 4個月存在非常明顯的通貨緊縮和資金面緊張,并在 8期之后基本收斂為零。最后,居民消費的結果較為異常,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沖擊意味著未來1個月的居民消費增長,并在 3期之后基本收斂為零。我們認為,這一異常結果的可能原因有:從幅度上看對居民消費的沖擊作用很小,且 Granger檢驗未通過,說明這種沖擊并不顯著;此外,由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危機有提前約1個月的指示性,此時市場仍處在最后的上漲期,仍然存在一定的財富效應,故居民消費在1個月后才出現拐點。

圖3 宏觀經濟變量對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脈沖響應圖
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各宏觀變量之間的領先滯后關系表明,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可能是極端流動性出現波動并存在風險溢價的原因。以貨幣供應為例,投資者預期未來數月可能會出現資金面的緊張,對市場造成影響,故選擇提前賣出資產。當市場狂熱接近末期,投資者間的預期和交易行為趨同時,會優先選擇賣出估值過高質量不佳的資產,出現“逃往質量(flight to quality)”現象,月內流動性觀測的值的尾端顯著增厚,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出現劇變。這種對未來宏觀形勢預期的自我實現,可能是該因子能夠指示危機并存在風險溢價的深層原因。
六、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確保結論的可靠性,我們還進行了以下多組穩健性檢驗。
我們考慮引入一些與極端流動性風險相似的概念,考察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解釋力是否能夠獨立于這些研究。除正文中考慮的Kelly和Jiang(2014)的極端收益率風險指標外,我們進一步考慮了 Chen等(2001)、Hutton等(2009)、代冰彬和岳衡(2015)以及褚劍和方軍雄(2016)的股價崩盤風險指標。股價崩盤風險同樣反映了出現極端負收益率的可能性,近年來在學術界和實務界對此有極高的研究頻率。股價崩盤風險指標的計算方法可參考 Chen等(2001)的負偏度系數(Crash_ns)與收益上下波動比率(Crash_ud)。首先應根據Hutton等(2009)的研究,按式(7)計算特質收益率。

其中Rit和Rm,t分別為個股和市場的日收益率①引入市場收益率的提前和滯后期是為調整非同步交易的影響。Chen等(2001)以及Hutton等(2009)是基于周度數據計算年度股價崩盤風險,而本文的頻率更高,故非同步交易的調整更為重要。,回歸所得殘差即為特質收益率rit。隨后,可根據式(8)和式(9)計算負偏度系數和收益上下波動比率。

其中nu和nd分別為月內上漲和下跌的天數。
我們引入 Crash_ns以及 Crash_ud指標重復了表2的回歸。表7的回歸結果顯示,控制這些變量并不影響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的顯著性。

表7 加入類似指標后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beta與個股收益率的Fama-MacBeth回歸分析
此外,我們還嘗試了不同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 beta值的計算方法。首先,我們采用滾動60期計算beta,此時得到的beta值更為穩定,但也包含了更多的陳舊信息。其次,我們提高了流動性尾端的閾值標準,將其設定為 99%,并重新計算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其beta值。最后,我們在beta計算時與Fama-French三因子同時進行多元回歸。表8的結果顯示,各類beta值的計算方法基本不影響本文的結果。

表8 其他beta計算方法下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beta與個股收益率的Fama-MacBeth回歸分析
七、結 論
2015年到 2016年中國股票市場的流動性枯竭,給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帶來了深刻的沖擊。然而,傳統理論中的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并不能很好地預測和解釋這次大規模的流動性恐慌。本文基于這一出發點,結合次貸危機以來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傳統的流動性因子存在兩個缺陷。一方面,危機時期的流動性打破了均值回復性,呈現出自我強化加速下滑的特征,傳統的流動性因子無法描述危機時期的特殊性質。另一方面,投資者存在“驚弓之鳥”的特征,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恐懼,即使在正常時期也存在顯著的風險溢價,傳統的流動性因子遺漏了這部分風險溢價。為解決以上問題,本文將Kelly和 Jiang(2014)以及 Wu(2017)的框架進一步推廣到了中國股票市場流動性中,基于冪律分布假設和 Hill估計量,構造了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以上兩個方面擴展了傳統的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
在實證檢驗中,本文得到了以下結論。第一,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相較于傳統的流動性因子在市場流動性恐慌期顯著增大,且有約一個月的提前期,對重大的危機具有提前指示作用。第二,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橫截面上存在顯著的風險溢價,且可以消除傳統資產定價模型難以消除的反轉效應異象。第三,將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與CAPM 的市場因子相結合構建的兩因子定價模型,解釋能力顯著高于其他經典模型。第四,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未來市場收益率有顯著的預測能力,并對經典的市場收益率可預測性框架提供了補充。第五,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對未來宏觀經濟變量具有一定指示作用,極端流動性的沖擊預示著未來 1個月的產出、投資和經濟景氣指數的下滑以及未來 4個月的通貨緊縮和資金面緊張。這些結論表明,本文所構造的極端流動性風險因子在理論上擴展了流動性資產定價模型,深化了對危機時期流動性特殊性質的認識,也對投資實務有一定應用價值。
正如前文所言,資產定價模型的適用性取決于市場特征與投資風格。從本質上講,中國股票市場上明顯的流動性驅動特征和劇烈的流動性波動性,起源于明顯的投機性特征,劇烈的股價波動并非由基本面引起,而是由短期投機性的資金流動引起。因此,定價模型的構建應充分考慮市場與投資者的特征,并非放之四海皆準,這也是本文結論有效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