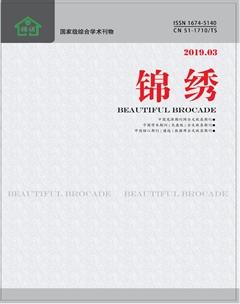淺談網絡服務提供者刑事責任問題
嚴煥麗
關鍵詞:網絡服務提供者;刑事責任;歸責路徑
(一)網絡服務提供者刑事責任的限度
對于網絡接入服務提供者,他們僅僅是提供一般意義上為社會生活所容許的、不具有社會相當性風險的中立技術服務,用戶之后的使用方式就脫離了技術接入者的控制,無論是在時間還是空間方面都已經無法將二者湊成具有刑法意義上的連接關系。在技術接入服務既成之后,該項服務的提供者已經不再具有制造或者增加危險的可能性。根據刑法對網絡服務提供者制裁的相關條文來看,其可罰性來源于在提供網絡接入服務時主觀上具有為他人實施犯罪貢獻便利促成的意識,除此之外的網絡接入技術提供者都應被歸屬為中性行為,不應當入罪答責。
對于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既然這類主體提供的服務是將廣泛的用戶點對點地聯結起來使其在一定的網絡空間中實現信息資源共享,類似于現實社會的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公共場所,場所的管理者對其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管理能力與保障場所內游客的普遍安全的義務。當用戶在網絡平臺上相互作用、將社會活動的很大部分搬入網絡空間的過程中,離不開網絡平臺提供的持續性服務,這就會產生制造或增加社會風險的可能,如果用戶通過微信界面、“抖音”“快手”客戶端分享傳播一些有損社會風化的信息或實施煽動國家分裂民族仇恨之類的危險行為,這些軟件平臺若是沒有進行實時的審查過濾工作,就可以評價為對社會增加了刑法需要規制的風險,相應的作為義務則構成網絡平臺服務者可罰性的來源。基于法不強人所難的原則,應對施加于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的法定義務有所限制。利益平衡點的尋求是一個比較困難的歷程,嚴加重視權衡要保護的權益與規制行為人所帶來損耗之間的取舍,同時審慎地選擇懲罰的方式,踐行罪責刑相適應。最后,通過以上所有要件依然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結合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的認識與意志分析其是否能夠運用中立幫助行為限制處罰論解決刑事歸責問題。
對于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當然就是提供內容方面的服務,那么就與發布在網絡中的資源存在直接的密切聯系,這種“產品輸出”的功能特征就賦予了輸出主體更多的義務與責任,相對于前兩種網絡服務提供者,內容服務提供者對其服務項目應負有最為嚴格的審查監管義務,但凡是內容出現有違社會正當風化與刑法不容許的危險,就可以直接認定危險與網絡服務提供行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其可罰性即來源于所提供信息內容本身。因為上傳并發布網絡信息資源的服務者在提供相關內容時都會在主觀上對所發布事項具有明確的認知與推定的審查義務,摻入了主觀色彩的業務行為人從自然意義的角度己經喪失了中立性地位,完全可以作為一般刑事歸責程序的適用對象。對于從他處獲取信息內容的提供,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需要履行嚴格的監管義務,對獲取的信息內容進行過濾、篩選,因為可以推定主體此時具有更為清晰的主觀心態并在此意識的支配下實施了相應作為。
(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歸責路徑
1.獨立成罪
作為形式的獨立犯罪。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的刑事可罰性來源于該類主體對于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具有完全的自主權,所以當這類主體發布不法內容時有理由推定其主觀上具有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對危害后果的預見,在這樣的主觀意志支配下行為主體在客觀上實施了與主觀心態一致的作為行為,所以理所當然地獨立成罪。對于網絡接入服務提供者,如果電信經營者在事先未通知的情況下中斷網絡和通訊服務,給廣大網絡用戶造成巨大損失的,應該就其中斷網絡連接服務的行為承擔獨立的刑事責任;對于網絡平臺提供者,雖然其不直接提供或者產生信息內容,但可能因介入網絡內容的生成而發生身份轉換,由此承擔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的刑事責任。
不作為形式的獨立成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是網絡服務提供者以不作為形式獨立成罪模式的先河,每一種罪名的設置都有其價值判斷的考量,在我國當前互聯網空間的作用模式中,普遍是網絡服務提供者仿佛具有“上帝般的視角與境地”,他們無論是技術還是地位都存在著相對于網絡用戶而言的壓倒性優勢,擁有足夠的能力運用監管技術對在互聯網環境中實施的犯罪行為進行必要的管控。如同道德底端封鎖線般的法律從不應施加行為人履行做不到的義務,通常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有能力去履行的社會相當性義務,因此當行為人在怠于履行該類義務且經有關部門責令更正后仍然不采取相應措施(在此過程中被官方性的通知完全可以證明行為人主觀的明知狀態),造成嚴重后果的,就合乎法理地作為犯罪行為予以評價。
2.共犯責任
此種模式是網絡服務提供者刑事責任的常態選擇。盡管在司法實踐中已經適用得很順暢,但是部分學者仍然持有異議,認為傳統的共犯理論要求二人以上行為人持有共同的犯意,然而網絡服務提供者與用戶之間的意思聯絡往往極為微弱,充其量僅能被評價為不以為意的“默契”,因此提出片面的共犯理論予以糾正。基于這種問題,應當意識到法律相較于社會發展是頗具滯后性的,較之于互聯網科技發展的速度更是難以望其項背,此時應當認識到理論只有與時俱進才具有存在的價值。不必要隨便就將難以適用的理論連根拔起,適當的修正才是正確選擇,考慮到網絡社會具有比現實社會更強大的便捷性與更容易達成會意的傾向性等效應,可以通過對傳統刑法理論作出更為貼切網絡時代的理解,而我國司法實踐正是體現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歸責模式尚可依據共犯理論,以實際行動承認了網絡服務提供者與網絡用戶之間的某種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