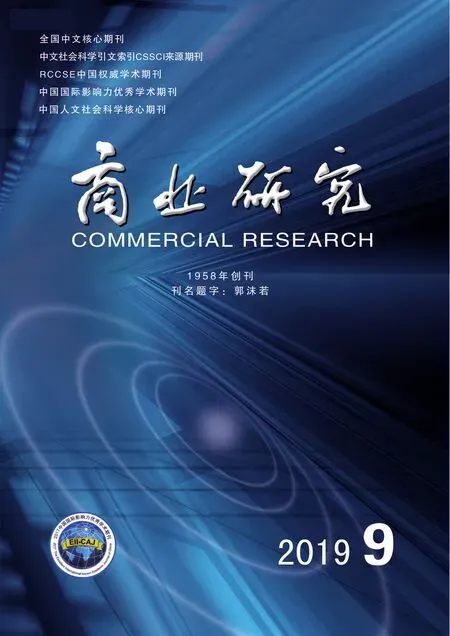異質委托情境下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研究
劉新民,孫向彥,吳士健
(山東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山東青島 266590)
內容提要:基于商業類國企運營治理過程中政府股東、社會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雙委托代理關系,及政府股東與社會股東在經濟效益創造、社會福利創造與政策性義務承擔的異質性訴求,本文構建了異質委托情境下的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模型。通過將政府股東的解聘補償機制引入到模型設計,探討各利益主體的行為選擇。研究發現:政府股東解聘傾向對三邊治理結構具有雙重影響。隨著政府股東解聘傾向的增加,政府股東在經濟效益創造上的努力投入先上升后下降,并抑制了商業類國企高管、社會股東努力投入水平及政府股東社會福利創造上的努力投入;解聘補償機制的引入可以有效規制各方不道德行為;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一定損害其他參與方利益的說法不成立,隨著其經濟努力投入的增加,其他各參與方利益由損轉益。
一、引言
商業類國企(Commerci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CSE)在創造社會福利的同時,以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為目標。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1]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與物質資本所有者一樣,同樣對企業擁有所有權,因此,政府股東(Government Shareholders,GS)和社會股東(Social Shareholders,SS)給予商業類國企高管一定的股權激勵對于企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出資者的特殊地位決定了政府股東和社會股東治理的內在必然性,人力資本的特殊性和契約的不完備性也決定了商業類國企高管治理的內在必然性。商業類國企的股份制改革形成了政府股東、社會股東雙委托,與商業類國企高管共同對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的復雜的三邊治理(trilateral governance)體系,完善和優化了商業類國企的治理結構。當前,我國的商業類國企主要包括軍工、石油、電力等具有特定功能和自然壟斷能力的國有企業,它們具備得天獨厚的資源和國家信用雙重優勢。但是,實踐表明,我國目前仍然存在部分商業類國企運營效率低下的狀況。2017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資產總額2.4萬億元,負債總額突破1萬億元,凈資產收益率僅為1.9%,而同期格力電器凈資產收益率為37.44%,同為國企,其經營狀況卻存在如此巨大差異。
導致商業類國企運營效率低下的原因除參與商業類國企運營治理的各方能力、素質參差不齊外,運營模式自身所存在的契約不完備性更是關鍵。市場經濟中,股份制公司在運營模式及治理過程中遵循傳統的委托代理關系。委托代理理論常被契約制定者用來設計薪酬激勵和道德風險規制機制,以誘導契約的其他執行者按照契約制定者的意愿行事[2-3]。但是,對于中國情境下的商業類國企而言,政府股東往往是一家獨大,在其控股公司的運營治理過程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然而,部分政府股東仍然無法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演變,“角色”定位出現錯位。政府股東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過程中仍對商業類國企高管布置較大的政策性義務,以謀求社會福利,而非經濟效益為首要目標[4]。同時,由于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擁有絕對的任免權,因此,商業類國企高管出于政治升遷及經濟效益的綜合考量,在商業類國企運營治理過程中不得不在追求盈利目的的同時,兼顧政策性義務的承擔。基于此,構建中國情境下的政府股東、社會股東雙委托,與商業類國企高管共同對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的三邊治理分析模型,防范各方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是必要的。
本研究試圖構建一個三邊治理分析模型,通過引入政府股東違約補償機制,對商業類國企運營過程中的多目標決策、雙委托三邊治理問題及其道德風險規制進行分析。政府通過股權出讓,社會股東通過投資、知識轉移,參與商業類國企的監督治理;政府股東和社會股東通過股權激勵的方式聘任商業類國企高管。模型假定政府股東和社會股東為雙委托人,委托商業類國企高管對商業類國企進行運營治理。基于理性人假設,政府股東作為委托人之一,在商業類國企治理契約中居于主導地位,負責契約制定,對商業類國企具有社會福利和經濟效益創造的雙重訴求,既存在私自解聘商業類國企高管的道德風險問題,又面臨著社會股東和商業類國企高管在商業類國企治理過程中的努力懈怠問題。社會股東作為另一委托人,以謀求自身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為目標,但自身存在努力懈怠問題,同時要面臨政府股東道德風險問題和商業類國企高管過度承擔政策性義務的問題。商業類國企高管作為代理人,既要通過商業類國企治理創造經濟效益以回報政府股東和社會股東,又要承擔政府股東要求的政策性義務。商業類國企高管自身存在努力懈怠問題,具有機會主義行為特性,同時面臨政府股東的解聘風險。
二、基本假設與三邊道德風險模型構建
(一)模型基本假設
考慮到商業類國企的實際運營情況,為便于分析,假設商業類國企高管在商業類國企治理的過程中,追逐經濟利益的同時,需要兼顧政策性義務的承擔。同時,模型有如下研究假設:
(1)假設商業類國企股份制改革后,政府股東持有的股權比例為αG。根據社會股東的資金投入、知識轉移的力度等指標,確定社會股東可以獲得的股權比例為αS。將社會股東為獲取商業類國企股權所投入的資金、知識等要素,歸結為社會股東初始投入成本CSI。社會股東和政府股東賦予商業類國企高管股權,以激勵其努力工作,賦予股權比例為αE。因此,有αG+αE+αS=1。




本文中有關參數符號及含義如表1所示。

表1 參數符號及含義
(二)三邊道德風險模型的構建
根據模型假設條件可得:
商業類國企創造的社會福利期望:
商業類國企的經濟效益期望:
將政府股東、社會股東、商業類國企高管各自成本函數帶入,分別可得:
(1)商業類國企高管的經濟效益期望:
商業類國企高管創造的社會福利期望:
SS=EEs-CEp
(2)社會股東的經濟效益期望:
(3)政府股東的經濟效益期望:
政府股東的社會福利期望:
EGs=EEs-CGp
基于政府股東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過程中,優先考慮商業類國企承擔政策性義務創造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假設,可知政府股東最優效益模型為:
maxEGe
s.t. maxEGs
(1)
基于社會股東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過程中的經濟人假定,可知社會股東最優效益模型為:
maxSE
(2)
基于商業類國企高管在商業類國企運營治理過程中,將綜合考慮商業類國企承擔政策性義務創造的社會福利與經濟效益關系,可知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效益模型為(假定,商業類國企高管從社會福利創造和經濟效益產出這兩個屬性中獲得的效用偏好是相互獨立且滿足湯姆森條件的[5],那么,本研究即可認為商業類國企高管從社會福利創造和經濟效益產出這兩個屬性中獲得的效用是可加的[6]):
maxβSS+(1-β)SE
(3)
政府股東作為政府股權出讓與商業類國企高管聘任三邊治理激勵契約的最終制定者,通過股權轉讓吸引社會股東參與并激勵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發展注入資金、轉移知識,通過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聘任與激勵促使其為實現政府股東目標做出努力。在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體制下,政府股東考慮社會股東、商業類國企高管參與約束IR與激勵相容約束IC的共同作用,政府股東面臨的非線性最優約束模型為:
(4)

代入參與約束IR和激勵相容約束IC,可得政府股東的最優目標函數為:
(5)
上述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模型涵蓋了政府股東多決策準則最優目標函數、社會股東及S商業類國企的參與約束與激勵相容約束,并充分考慮了各方道德風險問題。在保證商業類國企正常運作的基礎上,決策目標以實現政府股東、社會股東及S商業類國企目標函數的帕累托最優為依據。
三、解聘補償、道德風險與三邊治理分析
信息不對稱情境下,社會股東努力程度,商業類國企高管政策性義務承擔及經濟效益追求努力程度θEp、θEe等參數作為私有信息,對政府股東來說是不可觀測的。因此,政府股東只能根據事前的有限信息確定他們之間的契約關系。根據所構建的雙委托、多目標三邊治理模型,由最優一階最優條件可得信息不對稱情境下存在如下關系:
(6)
(7)
(8)
(9)
(10)
(11)

(一)商業類國企高管多目標決策與最優收益分析

由上述一階最優條件可知,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經濟努力程度與其持股比例呈正相關關系,與其經濟努力成本系數呈負相關關系,與其單位經濟努力創造的經濟效益呈正相關關系。商業類國企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使得商業類國企高管自身利益與商業類國企利益愈加緊密。因此,商業類國企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提升了其為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付出努力的積極性,有效地降低了商業類國企高管的道德風險問題。商業類國企高管單位經濟努力創造的經濟效益越高,通過商業類國企治理為自身贏得的回報越大;但是,商業類國企高管經濟努力成本系數的增加會抑制商業類國企高管的經濟努力程度,加劇了商業類國企高管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商業類國企高管必須提升經濟效益創造能力,降低經濟努力成本系數。
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經濟努力程度與政府股東解聘傾向呈負相關關系。商業類國企高管在商業類國企的運營治理過程中付出努力以贏得回報,需要付出經濟努力成本,政府股東的道德風險行為使得商業類國企高管在投入經濟努力成本后無法獲得相應回報,增加了商業類國企高管投入風險,因此,當政府股東表現出較強的解聘傾向時,商業類國企高管將減少經濟成本投入以規避損失。因此,三邊治理契約必須充分體現出對政府股東解聘行為的制約機制,以提升商業類國企高管信心。

由上述一階最優條件可知,商業類國企高管為承擔政策性義務付出的努力與政府股東解聘傾向呈負相關關系。商業類國企高管在商業類國企的運營治理過程中通過服從政府股東指令以獲得政治升遷回報,但是,與此同時,商業類國企高管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成本,還將面臨政府股東的道德風險行為,因此,當政府股東表現出較強的解聘傾向時,商業類國企高管將減少對政策性義務的承擔以規避損失。因此,無論從商業類國企高管經濟努力、還是政策性義務承擔的角度來看,三邊治理契約必須充分體現出對政府股東解聘行為的制約機制。
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承擔政策性義務付出的努力與其對政策性義務的重視程度呈正相關關系。當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控制力度提高時,商業類國企高管對政策性義務的重視程度提升,因此,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承擔政策性義務付出的努力會跟隨其對政策性義務重視程度的提高而提升。
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承擔政策性義務付出的努力與其承擔政策性義務的成本系數呈負相關關系,與其承擔政策性義務單位努力創造的社會福利呈正相關關系。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單位努力創造的社會福利越高,通過商業類國企治理獲得政治升遷的機遇更高;但是,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的努力成本系數的增加會抑制商業類國企高管的承擔政策性義務的積極性,加了商業類國企高管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商業類國企高管必須提升社會福利創造能力,降低承擔政策性義務的努力成本系數。
綜上(1)、(2)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1:商業類國企高管持股比例增加,經濟努力程度上升,道德風險下降。
結論2:商業類國企高管經濟努力成本系數下降,單位經濟努力創造的經濟效益上升,商業類國企高管的經濟努力程度上升。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的努力成本系數下降,承擔政策性義務的單位努力創造的社會福利效益上升,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的積極性上升。
結論3: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傾向增加,商業類國企高管的經濟努力程度和承擔政策性義務的努力程度下降,道德風險增加。
結論4:商業類國企高管對政策性義務的重視程度提高,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的努力程度提高。
(3)通過 MATLAB 仿真,可以得到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及對政策性義務重視程度的變化曲線,如圖1所示。

圖1 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及對政策性義務重視程度的變化曲線
根據圖1可知,當商業類國企高管對政策性義務的重視程度處于不同階段時,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的變化存在差異。當商業類國企高管對政策性義務的重視程度較高時,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的增加總體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反之,當商業類國企高管對政策性義務的重視程度較低時,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的增加總體呈現出下降趨勢。從中可以發現,商業類國企高管的經濟努力程度對最優期望效益的影響,并不會因為其對商業類國企經濟效益重視程度的降低而降低;相反,商業類國企高管對政策性義務的重視反而刺激商業類國企高管付出了更多的經濟努力,實現了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期望效益的提升。商業類國企高管過度承擔政策性義務,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嚴重損害社會股東和商業類國企高管利益的行為,在這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悖論。因為,當商業類國企高管經濟努力程度較低時,從圖1中本研究確實也可以發現這種現象,但是,當商業類國企高管經濟努力程度繼續增加時,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期望效益會快速的掉頭回升。商業類國企高管對承擔政策性義務的重視程度提升,不僅沒有抑制商業類國企高管通過付出經濟努力以實現其最優期望效益的提升,反而可以促使商業類國企高管通過付出更多的經濟努力以實現最優期望效益的提升。所以本研究認為,現如今出現的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損害其他參與方利益的現象,是由于商業類國企高管在承擔政策性義務時,未能及時付出相應的經濟努力造成的。
綜上(3)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5:我國現如今出現的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損害其他參與方利益現象,是由于商業類國企高管在承擔政策性義務時,未能及時付出相應的經濟努力造成的。若商業類國企高管經濟努力程度繼續增加,商業類國企高管承擔政策性義務的行為反而會助推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期望效益的提升。
(二)政府股東多目標決策與最優收益分析





由上述一階最優條件可知,政府股東所付出的社會福利努力與其解聘傾向呈負相關關系。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擁有絕對的任免權,相較于謀求經濟效益的目的,政府股東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過程中更注重于追求創造社會福利的目的。由此可知,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行為更多的是對社會福利的訴求所致使的,因此,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解聘傾向較高時,政府股東以較低的社會福利努力便可以實現自身對商業類國企創造社會福利的目的。
政府股東所付出的社會福利努力與其單位社會福利努力創造的社會福利呈正相關關系,與其單位社會福利努力成本呈負相關關系。政府股東的單位社會福利努力成本和其單位社會福利努力創造的社會福利都反映了政府股東創造社會福利的能力,政府股東的單位社會福利福利努力成本越低和其單位社會福利努力創造的社會福利越高代表了政府股東創造社會福利的能力越強。當政府股東創造社會福利的能力越強時,政府股東謀求社會福利努力的積極性越高。
綜上(1)、(2)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6:政府股東持股比例的降低使得政府股東為商業類國企付出經濟努力的積極性降低。
結論7:政府股東提高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標準,會抑制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傾向,緩解政府股東的道德風險問題;若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傾向增加,政府股東必須對商業類國企付出更高的經濟努力以維護自身利益,但是,解聘傾向的增加會抑制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的社會福利努力投入。
結論8:政府股東在商業類國企運營過程中帶來社會福利的能力越強,政府股東謀求社會福利努力的積極性越高。
(3)為規制政府股東的道德風險問題,就政府股東最優解聘傾向ω*分別對bGe、θGe、αG、λEg求導,可得最優一階條件為:
由上述一階最優條件可知,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最優解聘傾向與其經濟努力程度和單位經濟努力成本呈負相關關系,與其持股比例呈正相關關系,與其貢獻經濟效益的能力呈正相關關系。政府股東的經濟努力程度和單位經濟努力成本越高,政府股東的經濟努力成本越高,即政府股東貢獻經濟效益的能力越低,其解聘商業類國企高管的代價越高。因此,在政府股東自身創造經濟效益的能力較低時,政府股東更傾向于通過聘任專業的商業類國企高管以維護自身利益。當政府股東貢獻經濟效益的能力較高時,基于機會主義行為,其解聘商業類國企高管以謀求更多利益的傾向越高。
綜上(3)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9: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傾向取決于政府股東在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中所扮演的角色。若政府股東在商業類國企中占有較高的持股比例,或在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則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具有較高的解聘傾向。
(4)通過 MATLAB 仿真,可以得到政府股東最優經濟期望效益隨補償標準及解聘傾向變化曲線,如圖2所示。
根據圖2可知,政府股東最優經濟期望效益隨著解聘傾向的增加先是快速的下降,然后是逐漸的趨向于平穩。政府股東通過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行為實現其謀求更高社會福利的目的,因此,政府股東解聘傾向的增加降低了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同時,根據仿真結果可以發現,隨著政府股東解聘傾向的增加,解聘補償標準對政府股東最優經濟期望效益的影響降低,因此,本研究認為,解聘補償可以緩解政府股東的道德風險問題,但是,若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傾向較高時,解聘補償對政府股東的解聘行為的抑制效果降低。

圖2 政府股東最優經濟期望效益隨補償標準及解聘傾向變化曲線
通過 MATLAB 仿真,可以得到政府股東最優經濟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及努力成本系數變化曲線,如圖3所示。

圖3 政府股東最優經濟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及努力成本系數變化曲線
根據圖3可知,政府股東最優經濟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的增加先下降后快速上升。這反映了經濟社會中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當政府股東的經濟努力付出低于某一臨界值時,政府股東經濟努力付出的增加不但不會提升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反而會降低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但是當政府股東的經濟努力付出突破這一臨界值時,政府股東的經濟努力付出對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的提升效用會迅速增加。
同時,根據圖3發現,政府股東單位經濟努力成本的增加不但不會降低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反而會大幅度的提升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政府股東單位經濟努力成本雖然增加了,但這同時降低了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傾向;政府股東的解聘傾向越低,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越高。因此,政府股東的單位經濟努力成本的增加不但不會降低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反而會提升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的論斷是正確的。
綜上(4)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10:政府股東的最優經濟期望效益隨其經濟努力程度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隨解聘傾向的上升而下降;政府股東的單位經濟努力成本的增加提升了其最優經濟期望效益。
結論11:隨著解聘傾向的上升,解聘補償機制對政府股東道德風險的規制作用降低。
(三)社會股東最優收益分析

由上述一階最優條件可知,社會股東最優努力程度與其努力成本系數呈負相關關系,與其單位經濟努力為商業類國企帶來的經濟效益呈正相關關系,與其持股比例呈正相關關系。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條件下,社會股東努力成本系數的增加,意味著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帶來經濟效益的技術能力下降,降低了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貢獻經濟效益的積極性。但是,當社會股東單位經濟努力為商業類國企帶來的經濟效益增加,亦或社會股東持股比例上升時,社會股東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提高,提升了社會股東努力為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的積極性。
社會股東最優努力程度與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解聘傾向呈反相關關系。政府股東解聘傾向的上升意味著政府股東為謀求更高社會福利效益的傾向上升,因此損害商業類國企高管和社會股東經濟利益的可能性上升,故政府股東解聘傾向的上升抑制了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帶來經濟效益的積極性。
綜上(1)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12: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框架下,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解聘傾向上升抑制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的積極性。
結論13: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能力的提高,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提高,提升了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的積極性。
(2)通過 MATLAB 仿真,可以得到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隨其努力程度及努力成本系數變化曲線,如圖4所示。

圖4 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隨其努力程度及努力成本系數變化曲線
根據圖4可知,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與其努力程度間呈現出復雜的非線性關系。
當社會股東努力成本系數較小時,社會股東努力程度的增加提升了其最優期望效益。社會股東努力成本系數在社會股東努力程度對最優期望效益的提升過程中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即在社會股東努力程度一定的條件下,社會股東努力成本系數越大, 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越高。
當社會股東努力成本系數較大時,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隨其努力程度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且努力成本系數越大,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上升和下降的趨勢越快。從圖4中可以發現,當社會股東努力程度較低時,努力成本系數越大,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越大;但是,隨著社會股東努力程度的增加,社會股東單位努力成本對其最優期望效益增長的制約愈加明顯。因此,當社會股東努力程度較高時,社會股東必須提升自身技術能力,控制努力成本系數。
結論14: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隨其努力程度的變化受到其努力成本系數的影響。
四、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基于商業類國企運營治理過程中政府股東、社會股東和商業類國企高管三方之間復雜的委托代理關系,構建了一個雙委托、多目標的三邊治理分析模型,通過將政府股東的解聘補償機制引入到模型設計,探討了各利益主體的行為選擇和道德風險規制。研究發現: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體系下,信息的不對稱使得各利益主體存在道德風險和不作為現象,這是制約商業類國企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現實原因。政府股東的解聘傾向源于其對經濟效益及社會福利創造的訴求,解聘傾向的大小取決于其在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結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政府股東的解聘傾向對商業類國企的三邊治理結構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解聘傾向的增加可能會提高政府股東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上的經濟努力投入,同時,也存在抑制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解聘傾向抑制了商業類國企高管在商業類國企治理過程中經濟努力投入與政策性義務承擔的積極性,增加了商業類國企高管的道德風險;同時抑制了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的積極性;降低了政府股東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上的社會福利努力投入。解聘補償機制的引入,增加了政府股東對商業類國企高管的解聘成本,提高了商業類國企高管在治理過程中的經濟努力投入,有助于規制政府股東的道德風險問題,但是,隨著解聘傾向的增加,解聘補償機制對政府股東道德風險的規制作用降低。當前,我國所出現的商業類國企高管在承擔政策性義務時損害其他參與方利益的現象,是由于其在承擔政策性義務時,未能付出相應的經濟努力造成的。若商業類國企高管在承擔政策性義務的同時,付出相應的經濟努力,承擔政策性義務的行為反而會助推其最優期望效益的提升。社會股東最優期望效益隨其努力程度的變化受到其努力成本系數的影響。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能力的提高,在商業類國企監督治理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越高,社會股東為商業類國企創造經濟效益的積極性越高。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要推動商業類國企的良性發展,可以有如下管理啟示:一是要提高各利益主體間信息的透明性,可以通過外部監督、定期發布信用評估信息[7-8],約束各方不道德行為,提高履約傾向。二是各利益主體應注重提高自身技術能力,降低努力成本。三是商業類國企高管在承擔政策性義務,謀求更高的社會福利產出時,必須相應的提高經濟努力投入,防止一邊倒現象的發生。四是要完善、優化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體系,通過引入政府股東解聘補償機制并設計合理的補償標準,提高社會股東及商業類國企高管在商業類國企運營治理過程中的積極性,規制政府股東道德風險問題,提高契約的穩定性。五是嘗試建立新的利益分配機制[9],以實現商業類國企三邊治理體系的全局最優為目標,而非當前的個體利益最優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