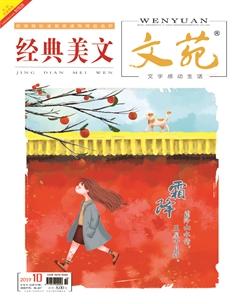寒夜巴士上,兩本并排的書
本期客座主編:劉荒田
2019年1月,號稱“四季如春”的舊金山,也有了標準的冬天。晚上7時多,寒風刺骨,市場街的行人裹緊大衣,微低著頭,鼻頭通紅,往各種車站趕。這陣子,唯家中燒旺了壁爐的起居室有強烈的吸引力。我從唐人街走出,跳上7號巴士,馬上感到暖烘烘的,興許明亮的燈光就是熱量。巴士往海濱開,這一趟乘客不多,誰都有座位。45分鐘以后到家,我在空著的雙人座上坐下。
掏出一本小說,是兩個月前江南采風途中,一位女作家送的簽名本,名字叫《情愛懺悔錄》。在開往蘇州的巴士上,這位虔誠的基督徒一板一眼地對我說:“你該從中看出信徒救贖的心路。”為了這一提示,我讀得格外鄭重。文革的背景,多難的青春,我親歷的故國歷史如車窗外的冷風。7號巴士開到下一站,停下,乘客上下,我沒有理會,沉浸在男女主角的第一次爭吵中。隱隱感到旁邊的空位坐下一個人,白色大衣的下擺掃到我的褲腿。
巴士上坡,換擋時顛了一下,我的頭偏了偏,發現我手拿的書旁邊,并排著一本書,橫排,英文字母歷歷可見,和我的書距離只有兩三英寸。持書的手白皙,比我帶老年斑的手小,是女性。她光顧看書,我明白,老朽如我,是沒有絲毫叫芳鄰看一眼的資本的。
然而,不能抑制好奇心。只因車上讀紙質書的人越來越少了,即如眼下,車廂內看書的只有我和她。抬頭環顧,乘客中,滑手機的十多位,聽音樂的三四位,瞇眼養神的兩三位。不過,讀白花花的紙頁不意味著“高級”,手機里有的是電子書。我還發現,她翻書的左手,貼著三塊以上的“創可貼”。
這么想著,忍不住脧了鄰座幾眼,三四十歲的女子,素面,顏值中等,鼻子大、高且微勾,應該是猶太人。白大衣里面是高領羊毛衣,和舊金山的藍領上班族沒什么區別。觸目的是短短的頭發,雖經梳理,仍嫌散亂,借此可判斷,她上車前戴帽。如果在餐館當廚師,高高的紙帽子是免不了的。難得的是她心無旁騖,沒發現一位好事者在窺視她的書。
她的書出格地破舊,沾上斑點,興許是油漬或汗跡,卷角,多皺,許多頁折起,還看到好幾種墨水的劃線,一些段落涂抹上紅、綠、粉紅色。可見,讀了無數遍,在各種場合。如果她真的在廚房干活,這本書,很可能擱在煤氣灶旁邊,受爐火烘烤和油星濺射。
本來,兩本書可相安無事下去,直到她或者我下車,兩條人生平行線永不交匯。她不會和我攀談,我更無意于“吊膀子”。她讀到一處,從手袋里掏出一支顏色筆,欲標出重點。車拐彎,筆拋下地,滾到我的鞋子旁邊。她對我說“對不起”,作勢彎腰。我搶先撿起,交給她。她第一次正眼向我,說一聲:“謝謝!”
老天爺送來的機會。我說:“不客氣,我有點好奇,你的書……”她爽快地遞給我。書名是 《關于寫作——創作生涯回憶錄》,作者是斯蒂芬·金。“名作家呢!”我贊嘆一聲。
“你讀過他的小說嗎?比如,《閃靈》《末日逼近》《死光》 《世事無常》……”她頓時熱情起來,側著臉孔,藍瞳閃出活潑的光,擺出和我“好好談談”的架勢。我把自己的一本合上,有點不情愿,因為被書里男女主人公的命運牽扯著。
她正要就斯蒂芬·金這些暢銷書作發揮,被我截住。我說這些書名,略略知道,但都沒讀過。她“哦”一聲,頓住了。
對這位“金粉”,我該如何措辭?要不要對她招供:我雖然老出飽經世故的模樣,但關于那位被《紐約時報》譽為“現代恐怖小說大師”的作家,限于英文水準和詞匯量,更限于謀生的壓力,只讀過《肖申克的救贖》,那是許多年前,為的是學英語而不是欣賞。但為了面子,文不對題地回答:“我不喜歡恐怖小說,因離現實太遠,我極少讀中國的武俠小說,出于同樣的心態。”她的手按在膝上書的封面,微笑著說:“沒問題啊,各有所好嘛!我喜歡的作家也不只金一個。”
“看樣子,你也是作家?”我的語氣平淡,但心里涌起波瀾。她眨了眨眼睛,神情變得莊重,臉相頓時老了一點,可見玩世使人年輕。
“我想當作家……現在還不是,將來,誰說得準呢?”她的右手拿著剛才我撿起的筆,下意識地作了“寫”的姿勢。
我記起39年前,我剛定居于舊金山,在一家西餐館當練習生,同事中有一位來自愛爾蘭的俏麗侍應生,名叫凱黎,她打兩份工,丈夫無業,天天宅在家里寫作。我見過她丈夫幾次,英俊的小伙子,眼神恍惚,模樣比年齡大了10歲。
“呵呵,代理商剛剛拿走他一本長篇小說,還沒有回復,估計行!”有一次,科恩先生來就餐。科恩在舊金山《記事報》頭版開專欄開了20年,大名誰人不曉?凱黎早就巴結上他。科恩向凱黎問起,她這般回答。她還把丈夫的小說的名字寫在賬單存根上,請對方“多多推薦”。因為凱黎成天把丈夫的筆名掛在嘴上,我記下了,至今未忘——石坦·拜爾。這么多年過去,也不知靠老婆養活的拜爾先生出名了沒有?不過,這一記憶,我沒對陌生的同座道及,只不痛不癢地說:“努力寫,寫!一定有那一天。”
“你怎么知道我會成功?”她的微笑帶著黑色幽默,讓我想起已退隱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深夜脫口秀”男主持大衛·萊特曼。
隨即,她提高嗓門,生怕我誤會似的:“哎,我可不是為成功而寫,不要誤會。我的心結解不開,找誰都沒辦法,才想到寫作。”
我的臉無端發紅。最近又冒頭的老癥結——寫了一輩子還是沒名堂,被她無意點中了。
“有意思,如果不介意,你能不能把這‘心結告訴我一二。我要從你的人生學習一些道理呢!”我懇切地說。
看窗外,巴士行走在“海街”。40多年前,這兒是席卷全美的嬉皮士運動的策源地。如果她晚生數十年,可能是那個“垮掉的一代”的活躍人物。閃亮的彩色招牌映在車窗上,旋轉著。巴士靠站,胡子拉碴的男子,鼻子帶鐵環的女子嘻嘻哈哈地上車,冷風從打開的車門呼地灌入。
“我在猶他州出生,父母是摩門教徒,我在那里從幼兒園直上到大學,主科是農業。我大學畢業那年,父母分居,我哪個也不靠,搬到加州來了。在舊金山待了7年,換了好幾種工作。你問我拿農科學位來大城市有什么用?有的,去賣花草樹木的商店當售貨員,肯定優先被錄用。”我沒來得及品出她的自嘲,她先笑起來。
“扯遠了,我興起寫小說的念頭,是去年圣誕節。我接到約翰從猶他州打來的電話。約翰是我上大學時交的男朋友,我父母管教嚴,我上到高中也不敢和男孩子約會,離開家去上大學,才和他好上,交往了兩年,畢業前分手了。他是詩人,瘦高個子。蠻可愛的。”她又下意識地拿起筆,作出“寫”的姿勢。
“我來到舊金山以后,和他斷了聯系。我在這里,男朋友換了3個。3年前,留在家鄉的約翰通過‘臉書找到我,有時問問近況,有時談談他自己。他一直單身。去年,感恩節剛過,他和我通電話,說他的母親快不行了。他6歲起沒了父親,和母親感情好得不得了,這我知道。他說他傷心極了,我安慰他。兩個星期后,他又來電話,說母親走了。他受不了,躲在家,好多天沒上班,想自殺。我對他說,你千萬不要想不開,我去陪你。我把這事情告訴若瑟夫。若瑟夫是我現在的未婚夫,他半年前向我求婚,我答應了。若瑟夫說,我和約翰過去怎么交往他不管,但現在我要去約翰那里,他沒法答應。我不肯讓步,我們吵了幾天。我的理由是,我不去,他會死掉,我去當心理輔導義工,能救回一條年輕的性命。他說,天知道你們在一起會發生什么。我說我發誓不越界。他說,不是你的問題,我信任你。但我能夠信任男人嗎?最后,我摔門走了。本來說好,趁元旦假期去費城見他父母,計劃婚禮,這一鬧,擱下來了。”
她不說下去,拿起書,把書頁翻得沙沙響。我的手按著下巴。這妞兒,可不是初學寫作的,正在賣關子呢!一定從斯蒂芬·金的書里學會一招:制造懸念。短暫的沉默,各自翻書。
“喂,你不問我去了猶他州沒有?猜猜嘛。”她的腔調,把我當成童年時的鄰家大叔。
我搖頭,說:“等著你揭開謎底。”
她無言。藍眼珠晶瑩,在燈光中格外搶眼。看來不想觸及這個話題。我想,算了,人家有難言之隱。不知不覺間,巴士上的乘客下去大半。進入日落區的地界時,只剩6位。
為了打破僵局,我沒話找話說我住在35街車站一帶。她說她住在48街。我曉得,那街和太平洋只隔一條公路。
我問:“像今晚這樣的滔天巨浪,你習慣嗎?”
她說:“住了6年,沒感覺了,沒濤聲伴著,反而睡不好。”
我打開書,男主人公從上海飛抵舊金山機場,即將遇到分別多年的初戀情人。我忽然想起什么,把書合上,讓她看封面的名字——《愛情懺悔錄》。把意思告訴她,說:“你的愛情也好,這本書里頭的中國人的愛情也好,是近似的。”隨后,我把這本書的梗概略略說了。此舉藏著我不失狡詐的心機——引導她把自己的故事說完。
她呢,對作者的好奇超過了對這本直排的漢字書,“你見過作者嗎?”她問。
“當然,我和她一起,參加一個采風團,3個月前,在中國長江以南旅游。”
“哎喲,你真幸運!我可沒有和出過書的‘作家面對面說過話呢!”作家,她用的詞是“Author”而不是“Writer”,且加重語氣,她認為“Author”更具權威,更值得尊重。我暗里為我的朋友高興。
“對了,你剛才說,你也是寫作人,寫了什么?出版過沒有?”巴士穿過洛頓街時,她問。
離下車只有四五分鐘,我只好大而化之:“是的,我從16歲起就立志當作家了,和你一樣,一輩子是業余。你該是在餐館的廚房上班的吧?我猜你是新手。我退休以前的職業和你的近似,但是在餐廳。”
她問:“你怎么知道的?是啊!我在休爾頓旅館的大廚房當切肉師,3個月前進去的。”
我指了指她手指上的“創可貼”。
她笑了,說:“沒辦法,凍肉太硬。”
“繼續說你。”她不肯放過。
“我32歲移民美國,如今71歲,英語只夠混飯吃,所以無法像你一般寫作。中文書,在中國內地出了30多本,沒有一本暢銷。就這樣。”
巴士在28街的街口停站,離家還有兩站。我對她說:“你說完你的故事吧!我快下車了。”
“哦,那樁事,最后這樣:我沒有去猶太州。約翰失蹤了,怎么也找不到。我也沒有和若瑟夫在一起,訂婚戒指快遞給他——他搬到洛杉磯去了。為什么我要寫小說,就是想要給自己的感情找個出口。”
我下車時,小心地握了一下她帶“創可貼”的小手,沒有留下任何聯系信息。
寒夜,巴士上兩本并排過的書,就是這一趟的意象。
劉荒田喜歡的書:
書 名:《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作 者:王鼎鈞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3年01月
這套書包括四本:《昨天的云》《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堪稱中國當代紀實文學的巔峰之作。一生經歷和文學成就都不同凡響的王鼎鈞,為完成這一系列,用了17年。他人在紐約,回憶之筆從內地一路追索到中國臺灣。《昨天的云》寫山東故鄉幼年;《怒目少年》著墨抗戰時的流亡學生經歷;《關山奪路》寫內戰;在中國臺灣生活30年,由于頭緒紛繁,只好單單截取“文學”,寫成最后一部,以個人的賣文生涯為主線,展示中國臺灣“江湖”的人文年輪。
以第三部為例,《關山奪路》寫的是作者親歷的4年內戰。由于大環境變化極大,血火人間充滿他稱為“精彩人生”的三要素——對照、危機、沖突。圍繞這個“每一天都可以寫成一本書,每一個小時都可以寫成一本書”的大變局,作者“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覽眾山小”。以幾十年修煉出的審美理想,穿越歷史,在傳統與現代、文學與歷史、匡時濟世與終極關懷的交匯點上,用大手筆表現大時代。這樣厚重與美善的非虛構作品,“五四”以來,中國為數不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是為養家活口而忙的新移民,從那個年代起,我在舊金山的中文書店購買了王鼎鈞先生的著作,從此成為他的忠實讀者。他對我的影響之重大,從做人到為文,勝似知青時代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后者以長篇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為我一生確定價值取向;前者的精神與文風,持續地為我的異國文學長途灌注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