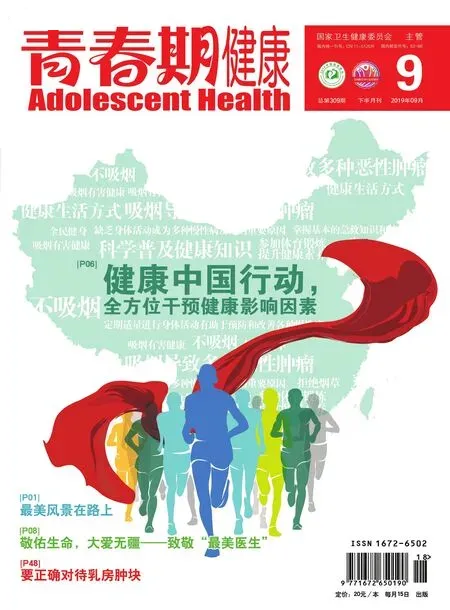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痛風的幾點梳理與新思路
■ 文 張元秋

痛風是一種代謝性疾病,嘌呤代謝障礙和(或)尿酸排泄減少,從而導致過量的尿酸鹽沉積于骨關節、皮下、腎臟等部位,引發以關節炎、痛風性腎病、痛風石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各種急、慢性炎癥及組織損傷。
隨著生活方式和飲食結構的改變,我國痛風患病率有逐年升高的趨勢,目前男性患病率約為1.26%~1.59%,且發病年齡也呈現出年輕化態勢。目前現代醫學治療原則以急性期使用非甾體抗炎藥、秋水仙堿等控制發作,緩解期抑制尿酸生成、促進尿酸排泄控制高尿酸血癥為主。雖已取得顯著臨床療效,但由于藥品種類較少、適應證有限以及藥物本身存在或不合理用藥帶來的不良反應,限制了痛風病療效的提高。中醫自先秦以來對痛風一病有著獨到見解,在廣泛的臨床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經驗。對中醫藥治療痛風病的梳理,可以為疾病診治提供新思路,同時也有望填補藥物開發的空白。
一、痛風的病因病機
中醫對痛風的認識由來已久,《張氏醫通-痛風》有云:“痛風一證,《靈樞》謂之賊風,《素問》謂之痹,《金匱》名曰歷節,后世更名曰白虎歷節。”中醫對痛風病因病機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秦漢時期《素問》“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的外感風寒濕立論;到隋唐《備急千金藥方》“熱毒流注”,《外臺秘要》“經脈結滯,血氣不行,蓄于骨節之間”的濕邪熱毒痹阻學說,主張在利濕基礎上加以清熱解毒;再到金元朱丹溪“熱血得寒,汗濁凝澀”首次將痛風的病因與“痰”相連,其針對“外感六淫、內生痰濕”的病因,辨證治療“上中下痛風方”等方劑。明清張景岳注重通利疏導、填補真元,“治痹之法,最宜峻補真陰,使血氣流行,則寒邪隨去”“有濕熱之為病者,必見內熱之證,滑數之脈,方可治以清源,宜二妙散及加味二妙丸、當歸拈痛湯之類主之”。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提出了“痹證有淤血”的觀點,明確化瘀通絡的治法。
近代以來,痛風的治療范圍不局限于痛風性關節炎,中醫在痛風性腎病的療效中也收到很好的療效。中醫學認為,濕邪是痛風的主要致病因素,痰濕熱瘀是病理產物,脈絡瘀阻是其基本病機。脾虛不運,或感外邪,濕邪偏勝;脾腎陽虛,氣化失司,寒濕內盛,阻滯于經絡骨節,氣血運行不暢,出現關節疼痛,且濕性粘滯,易致病情反復發作纏綿難愈,若病情遷延,痰濁瘀血相互搏結,留于皮下關節,產生痛風結節。在治療方面,現代醫家大多采用辨病和辨證相結合的方式,分期分型治療。
二、痛風的中醫治療
根據諸多醫家對痛風的認識以及中醫藥行業標準《中醫內科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圍繞“痰濕熱瘀虛”進行辨證論治,歸納如下:
1.辨證分型
(1)濕熱蘊結型。濕熱蘊結證是急性發作期的主要證型。癥見關節紅腫熱痛,觸之灼熱拒按,伴發熱口渴,汗出心煩,小便短黃;舌紅,苔黃膩,買弦滑或滑數。治以清熱除濕、通絡止痛。四妙散是清熱燥濕代表方,主治濕熱下注之癥,是清張秉承在二妙散基礎上加川牛膝、薏苡仁而成。
研究顯示,與秋水仙堿對照組相比,單用四妙散加減治療痛風總有效率更高(P<0.05),四妙散降尿酸(UA)效果更優于秋水仙堿,且以胃腸道反應為主的不良反應發生率低。動物實驗顯示,加味四妙散能夠在尿酸鈉晶體關節腔注射造模后24小時緩解關節腫脹的局部癥狀,且高劑量組可使腫脹的關節在第48小時恢復正常。對濕熱蘊結型痛風性關節炎的療效觀察,針對122例痛風性關節炎患者展開研究,結果顯示在秋水仙堿聯合美洛昔康片常規治療基礎上,配合使用當歸拈痛湯合三妙丸能更有效控制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的臨床癥狀,減少疼痛,降低血尿酸(BUA)含量,61例治療組中,臨床控制21例,顯效29例,有效8例,總有效率95.08%,優于對照組80.33%。“諸肢節疼痛,身體尪羸,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出自《金匱要略》。

(2)寒濕痹阻型。癥見關節腫脹疼痛,痛有定處,屈伸不利,肌膚麻木,局部無發熱癥狀;舌質淡,苔薄白或薄膩,脈弦或濡緩。陽衰土濕、痰濕痹阻是慢性痛風的主要病機。常用附子、烏頭等辛熱之品可散寒止痛、溫化痰濁。甘草附子湯,由炙甘草、制附子、白術、桂枝四味組成,溫陽祛濕。研究顯示,甘草附子湯能夠迅速改善痛風性關節炎臨床癥狀,降低C反應蛋白指標,且具有良好鎮痛作用。通過在治療慢性痛風性關節炎40例臨床觀察,在甘草附子湯基礎上配伍崇陽補火、健脾化濕的姜苓半夏湯,40例患者常規治療1~2個月,總有效率為87.5%,高于別嘌醇聯合塞來昔布的西醫治療(72.5%)。對80例痛風患者血脂與痛風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血脂異常與痛風性關節炎之間存在密切關系,這可能與高血脂能夠加重腎臟對尿酸的排泄量有關,隨后加味桂枝附子湯療效研究顯示,其治療痛風性關節炎在疼痛緩解和降尿酸水平上療效確切,且在甘油三酯、血清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指標改善方面明顯優于對照組。因此,加味桂枝附子湯能綜合調節機體代謝的紊亂狀態,這可能是中藥區別于西醫靶向治療的獨特機制。
(3)痰瘀痹阻型。癥見關節腫脹,甚則關節周圍漫腫,局部酸麻腫痛,或見塊瘰,硬結不紅,或伴目眩,胸脘痞悶,面浮足腫,舌胖質暗苔白膩,脈弦滑或緩。“痰濕阻滯于脈道之中,難以排泄,與血互結而為濁瘀,痹阻于經絡,則骨節腫痛、結節畸形,甚則潰破,流溢脂膏”。國醫大師朱良春在《丹溪心法》基礎上進行了發展,創立“濁瘀痹”理論,將病機概括為“濁毒瘀滯”:濁瘀從陽化熱,則炎癥反應明顯,關節紅腫;濁瘀從陰化寒,則炎癥反應和緩,關節腫脹皮色不變,設立“痛風方”泄化濁瘀。運用朱教授經驗,觀察由痛風方制成的痛風顆粒的臨床療效,發現該藥物能夠降低急性期、緩解期和慢性期的疼痛評分,且對于慢性期疼痛緩解效果優于與西藥組。
(4)瘀熱阻滯型。癥見關節紅腫刺痛,腫脹變形,屈伸不利,肌膚紫暗或干燥,病灶周圍或有硬結塊瘰。舌質紫暗或有瘀斑,苔薄黃,脈細澀或沉弦。使用犀角散聯合三棱針穴位點刺放血的方法治療22例濕熱瘀阻型痛風性關節炎患者,治愈13例,顯效8例,總有效率達95.45%。藥對是方劑組成的基本單位,對虎杖-茵陳配伍比例與關節炎療效間關系進行了相關研究,發現按照1:3比例配伍虎杖和茵陳時能夠最高效地降低炎性介質前列腺素的釋放,改善關節炎大鼠足趾腫脹度,取得最佳療效。
(5)脾腎虧虛。病程日久,關節疼痛變性,晝輕夜重,筋脈拘急,屈伸不利,步履維艱,頭暈目眩,顴紅口干。舌紅少苔,脈弦細或細數。脾主運化、腎司開闔,運化失調,開闔失司則聚生痰濕。金匱腎氣丸載于《金匱要略》,具有溫補腎陽,化氣行水之功。對金匱腎氣丸的臨床療效進行評價,數據表明,金匱腎氣丸治療痛風性腎病安全有效,尤其在保護腎功能、改善血肌酐、尿素氮、24蛋白尿指標方面,有著僅別嘌醇治療無可比擬的優勢。將獨活寄生湯、五苓散和三妙散融合成三五獨活寄生湯,三方化裁,針對腎元虛衰、痰濕痹阻而設,補益先天,活血化瘀,利濕清熱,與單純使用西藥相比,該方能顯著提高臨床總有效率(71.88%),改善患者腎功能及臨床癥狀,關節腫痛、腰酸乏力、夜尿頻多效果尤著。
2.中藥單體
痛形成機制較復雜,血液中高尿酸(UA)導致滑膜組織中尿酸鈉晶體(SMU)沉積而引發的炎癥是痛風性關節炎形成的主要病理機制。SMU導致巨噬細胞toll樣受體家庭成員TLR2和TLR4活化,進而激活核因子-κB(NF-κB)信號通路。同時SMU還能夠促進線粒體活性氧的生成和釋放,進一步增強NLRP3的活性。此外,CARD結構域凋亡相關顆粒樣蛋白(ASC)激活NLRP3炎性體復合物,從而募集、激活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aspase-1)致白介素-1β(IL-1β)前體轉換為具有生物活性的IL-1β,其造成血管舒張和中性粒細胞趨向性遷移,形成急性炎癥反應。
針對以上機制,許多學者圍繞促進尿酸代謝、控制炎癥遞質轉錄、抑制炎性反應、調節致痛因子等方面對中藥提取物或中藥成分進行了研究。研究表示,虎杖提取物的藥理作用可能與下調黃嘌呤氧化酶表達,抑制尿酸生成,降低IL-1β、IL-6以及NLRP3/ASC/caspase-1軸蛋白、mRNA表達有關。萆薢總皂苷能夠抑制腎小管上皮細胞尿酸鹽陰離子轉運體1(URAT1)的表達從而起到降尿酸的作用,并且可以通過作用于NALP3炎性體減少IL-1β生成,丹皮酚抑制NF-κB活化,從而降低炎性介質表達。
3.中醫針灸外治法
針灸刺激特定腧穴或局部病變部位,調和氣血、舒經通絡,通則不痛;現代醫學研究也表明,針灸能夠通過調節神經內分泌,改變局部微循環、電生理等方式發揮作用。毫針是臨床最常用的針具。治療痛風性關節炎患者120例,其中60例采用毫針療法,穴位主要選取足三里、曲池、陰陵泉等穴針刺,總有效率達96.67%,且治療后患者疼痛、焦慮程度均得到改善。火針亦稱“燔針”,是古代九針中的一種,具有溫經通脈、活血行氣的功效。采用火針圍刺痛風性關節炎患者關節紅腫處阿是穴、大椎、足三里、委中、陰陵泉等穴位,同時使用腹針直刺中脘、下脘、關元、氣海等穴,研究結果顯示,單純采用火針和腹針治療,患者疼痛感覺、尿酸水平、血沉水平均較治療前有明顯改善,但火針、腹針聯合使用療程最短、臨床效果最好,有效率最高(98.9%)。刺絡放血療法能排出局部惡血邪氣,暢通經脈氣血,直接祛除“毒”“瘀”之邪,緩解局部癥狀。對刺血療法治療急性期痛風性關節炎的臨床療效進行觀察,試驗表明刺血能夠減輕患者關節紅腫熱痛的癥狀,有效降低UA、CPR、ESR及疼痛評分,35例患者總有效率94.28%,且安全性高,無不良反應事件發生。
中醫藥治療痛風緊緊圍繞“痰熱瘀毒”進行論治,急性期以濕熱蘊結最為常見,慢性期多為寒濕痹阻、瘀熱阻滯證型,緩解期大多辨證為脾腎虧虛、痰瘀互結等,這種分期、辨證治療的方式取得良好的治療效果。雖然近年來對中藥治療痛風開展了大量臨床研究和分子生物學機制探討,但中藥治療痛風的前景仍然充滿疑慮。首先,臨床研究的數量雖多,但由于原始研究多為單中心、小樣本研究,且在實施過程中方法學設計、實施的不規范,從而導致無法基于當前證據對中藥治療痛風的療效作出確切的結論,而相應的痛風診療指南中也沒有建議臨床醫師采用中藥治療痛風,因此在中藥治療痛風的循證體系建設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不足。其次,在機制研究中藥雖進行了大量動物實驗,證明了中藥能夠有效控制炎性因子、炎癥小體的生成,緩解炎癥反應的發生,但研究尚不深入,分子機制仍然不明,臨床轉化率較低,尚無中藥單體成功治療痛風的報道。此外,中醫藥研究目前主要圍繞中藥藥效及藥理展開,證候學研究、藥物配伍比例、中藥量效關系及毒性研究較少。

在未來研究中,應以傳統中醫自身特色為基礎,以現代臨床流行病學和循證醫學的原則,開展更多高質量的臨床研究,為中藥治療痛風提供科學客觀的臨床證據。在機制探索方面,基于中藥多組分、多靶點的特點,整合多組學數據,識別作用靶點及其相互作用網絡,進行系統而深入的分生機制實驗研究,推進科研成果有效的臨床轉化。當然,在臨床研究、機制探討的同時,不能忽視痛風證候學生物標志物的標準化工作及中藥量效關系、劑量配比、毒理等方面研究,從而發揮中醫藥的優勢,更好地指導臨床準確辨證治療、增效減毒精準用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