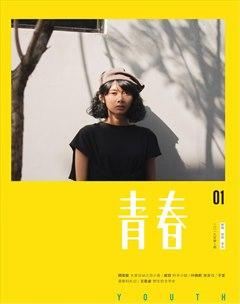范小青訪談:“時代發生轉變的時候會形成縫隙”
Question:南京師大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 顧奕俊
Answer: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著名作家 范小青
Q:范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受《青春》的專訪。因為今年恰逢《青春》雜志創刊四十周年,我們不妨就從您在《青春》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上弦月》開始聊起吧。《上弦月》這篇小說發表距今已有近四十年,您能和我們回憶下第一次向《青春》雜志投稿時的情形嗎?
A:《上弦月》發表在《青春》1981年第2期,這也是我創作生涯中發表的第二篇小說(第一篇是發表在《上海文學》1980年第9期的《夜歸》)。《青春》創刊于1979年,八十年代初在全國已經非常具有影響力。那時我向《青春》投稿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沒有去考慮會不會退稿的問題。沒想到第一次投的稿子就被《青春》錄用了。這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事情。《上弦月》發表的年份是1981年,那時候我還是一名在校大學生。當時大學生里能在文學刊物發表作品的人還是不多的,所以《青春》對我走上文學道路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很大。
Q:《上弦月》盡管大體上還是沿襲了當時盛行的“知青文學”的路子,但細讀以后又會感到和多數“苦大仇深”的“知青文學”作品有所不同。因為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已經具有了某種朦朧的“世界”意識。盡管她也會為了難以決斷的兒女情長而自我糾結,但同時她會去思考自己生活的那個當下,作為參照系的世界正在發生什么,不斷變動的世界與個體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能談下您在創作這篇小說時的一些背景嗎?
A:《上弦月》其實和之前發表在《上海文學》的《夜歸》有些相似。那個時代,大部分作家都是從“寫知青”“寫農民”起步的。原因很簡單,我們身邊只有知青、農民這兩類主要的書寫對象。但我覺得我最初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并沒有過多地去模仿當時特別主流的作家作品。那時候的“傷痕文學”“知青文學”主要寫的是一種“痛”。盡管“痛”是必然的,但我寫小說的時候著重點卻不在“痛”,而是個體的內心掙扎。這可能和我自己的經歷也有關系。我有過兩次下鄉經歷:第一次是童年跟隨父母“下放”;第二次是我回到縣城,縣中畢業后又一個人插隊下鄉。當時年輕人內心里其實是充滿困惑的。一方面年輕人會有扎根農村的念頭,一方面又會為了自己的前途而感到焦慮。人就是在一種矛盾的狀態中徘徊。現在的年輕人讀了《上弦月》可能會感到不可思議,但這的的確確就是當時青年人的真實寫照。
Q:您發表在《青春》雜志的這些作品里,有哪篇讓您印象特別深刻?
A:在《青春》發表的這些小說里,我印象最深的應該是《路邊的故事》(《青春》2001年第9期)。當時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用了一種散狀的寫法,并沒有走常規的現實主義套路。直到現在,《路邊的故事》依舊是我比較偏愛的短篇小說。
Q.:您如何評價《青春》這本已創辦了四十年的文學刊物?
A:《青春》最初的主編是斯群老師,當時斯群老師和顧小虎等編輯都對我非常關心。1982年我大學畢業留校以后,《青春》在這一年的三四月份組織了一次作家筆會,邀請我參加。這件事讓我非常感動,因為當時我還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作者。但《青春》有大胸懷,積極地鼓勵年輕作者,給年輕作者提供理想的創作環境與交流平臺。其實不光是我,現在文壇上成名的一批作家,當初剛走上文學之路的時候,幾乎都在《青春》發表過作品。因為《青春》雜志在全國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在作者、讀者心目中是非常具有分量的。很多代人都是在《青春》這本老牌文學刊物的陪伴下成長起來。從這個意義而言,《青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Q:能否結合您的經歷,談談在您的青春歲月里,文學發揮著怎樣的影響?
A:剛開始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我并沒有認為這會是自己一輩子去堅持的事情。但慢慢的,我意識到自己離不開文學了。我還記得自己大學畢業以后留校工作,既要做輔導員、班主任,又要學習業務,還要進修外語。從1982年到1985年,我寫了不少作品,但內心也十分焦慮。1985年以后,江蘇省作協開始調動一批青年作家去當專業作家,我聽到這個消息就下定決心要去作協。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沒有那么多精力能夠同時到兼顧日常教學與文學創作。那時候我只有一個信念:我要寫作。
Q:值得注意的是,在1985年前后,您從《夜歸》《上弦月》《迎面吹來涼爽的風》這一類青春寫作逐漸轉向“蘇州故事”書寫。您當時為何會產生這種轉向?
A:我的寫作從最初到現在,基本都是現實題材。絕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來自生活。1985年之前我還在學校,1985年之后我成了省作協的專業作家。那時我住在蘇州的小巷里,常常會跑到居委會去和居委會干部一起工作,有時也會跟著他們出去走訪。我記得大概是1985年,我跟隨居委會干部參加了一個全國房屋普查的活動,普查人員需要挨家挨戶去統計居民住房的實際面積,這個走訪過程對我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影響。盡管當時我也住在蘇州小巷里,但小巷里每家每戶的生活情況我是不太熟悉的。當我真的有機會去觀察那些小巷居民的生活狀況后,我的寫作題材也就開始發生變化。應該說1985年以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我基本寫的都是蘇州。
Q:您在八九十年代發表的一批“蘇州故事”小說,會時常使用到蘇白。您怎么看待作家與地域文化、地域方言之間的聯系?
A:我從小就生活在蘇州,因此我和蘇州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其中濃厚的世情文化,必然無法擺脫。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那批寫蘇州的作品里,我會比較多地使用蘇州方言。自己當時也蠻得意,因為讀者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蘇州作家寫的小說。那時候我對于地方文化的理解就是:形式。方言其實也是一種形式。通過這種形式,讀者知道我來自蘇州。至于后來為何我會減少對于蘇白的使用,是因為我開始意識到要從“形似”轉向“神似”。有時候我即便不用方言,讀者還是可以通過我寫的某個小說人物看出來:這是一個蘇州人。現如今,我可能會在敘述中最為合適的地方使用蘇白,這也表達了我骨子里深受吳語文化浸染的那部分。當然,現在我的確比較慎重地使用方言,因為我會更強調小說的現代性。相對的,地方特色或者方言就不能太過強烈了。
Q:讀了您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到你們這一代作家是自年輕時期就有意識地在文學創作中將個人命運、集體命運與國家命運聯系起來。討論個人的出路,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討論國家的出路。但當下的青年作家似乎更偏向于去書寫“小我”在“小時代”里的心理結構與情感經歷。您怎樣看待當下的青年寫作?
A:我想,這不是青年作家個人的問題,而更多還是時代發展的關系。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成長經歷。現在“80后”“90后”“00后”,他們出生的時候基本已經處在一個多元、開放的現代社會。他們成長中接觸到的事物可能是比較開放的,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又可能是比較自我的。相比較而言,我們這一代人在生活中是會考慮到其它的方方面面,更加強調一種需要去踐履的責任意識。
談到當下的青年寫作,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寫作應該要“以小見大”。你寫“小時代”,寫“小我”沒有任何問題。但“小我”背后應該要有大的時代意義去支撐。比如我的小說里大多數是小人物。但這些小人物處于時代潮流之中,他們的喜怒哀愁與時代相互捆綁。年輕作家寫人物當然也不會脫離時代,但在寫作的主觀意識上,青年作家們能不能通過“小我”從而更多地去反映現實與時代,反映現實與時代背后那種形而上的內質?
Q:《作家》雜志今年第4期發表了您的最新長篇小說《滅籍記》,據說單行本也很快將和讀者見面。《滅籍記》關乎“尋找”,而相類似的主題、結構在您之前的小說《赤腳醫生萬泉和》《我的名字叫王村》里都有不同程度的顯現。這一次您通過《滅籍記》想要“尋找”什么?能談談您創作這部小說的動因嗎?
A:我創作《滅籍記》的初衷就是想寫一個以“回到蘇州”為主題的故事。蘇州是一個特色非常鮮明的城市。比如說蘇州的老宅,在我的心里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也寫過很多關于蘇州老宅的小說、散文。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褲襠巷風流記》就是寫蘇州老宅的。到了《滅籍記》,我想用當下的眼光再去重新打量那些記憶中的蘇州老宅。
Q:《滅籍記》里有一些非常有意味的細節,比如電梯里的蝙蝠,比如亡者在生者夢中的述說。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您怎樣看待《滅籍記》里這些偏離現實邏輯結構的細節或意象?換言之,您是如何處理小說中的“紀實”與“虛構”?
A:《滅籍記》其實建立在“實”的基礎之上,就是蘇州老宅在今天碰到的那些普遍性問題。在動筆寫《滅籍記》之前,我是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發現正面去“強攻”這些問題好像行不通。所以我就換了一個思路,使用現代的手法寫《滅籍記》。其實最初“尋找”這一主題只是小說的引子,但繞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原先那個“尋找”主題。
這部小說里想象的部分我自己還是比較滿意的,因為這些想象的部分體現出了現代社會的荒誕性。《滅籍記》的鄭永梅是一個不存在的“人”,但他居然“活”了那么久,即使到小說結尾依然發揮著關鍵作用。還有一個鄭見桃,因為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只能冒名頂替他人。這也是我在當下社會中感受到的荒誕性。
Q:《滅籍記》的鄭見桃與鄭永梅是一組形成互補結構的對象:實際存在于世、卻無法擁有自己身份的鄭見桃;并不存在于世、卻有著無比詳實“經歷”的鄭永梅(相類似的例子還包括《桂香街》里的蔣主任)。您為何會選擇在《滅籍記》設置出這組涉及身份悖論的人物形象?
A:時代發生轉變的時候會形成縫隙。舊時代有舊規則,新時代有新規則。在“新”與“舊”交替的時候,舊規則沒有被完全打破,新規則也沒有完全得到確立,這時候就會產生縫隙,縫隙里滲透出來的就是荒誕,而這些荒誕之處就是文學創作的源泉。這也是我在塑造鄭見桃、鄭永梅這組人物時的考量。我自己就碰到過由于“新”“舊”沖突所帶來的困擾:我們小時候要填各種各樣的表格,比如籍貫、出生地、出生日期。但大家那時候填表都不太認真。所以我就成了三個地方的人:上海、蘇州、南通。一會兒我是上海人,一會兒我是蘇州人,一會兒又成了南通人。因為我父母是南通籍,我出生在上海松江,我又從小在蘇州長大。別人也會好奇:你到底是哪里人?此外,我們小時候是不存在“過生日”一說的,大人也不過生日。我們家五口人,其中三人的出生日期都是2月1日,但都不是2月1日出生的。過去的材料并不在意這些個人信息。但現在的規定肯定是不允許的。
Q:《滅籍記》里寫鄭永梅的大學同學開同學會。那些大學同學爭相回憶自己與鄭永梅的過往,并且通過這種方式“信誓旦旦”地“還原”出鄭永梅的面貌。鄭永梅并不存在,但關于鄭永梅的“歷史”卻因為這些漏洞百出的“記憶集合”真真切切地建構起來了。這也涉及到歷史與記憶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A:事實上,對于那些有關歷史的敘述,我通常持一種較為懷疑的態度,所以我會在《滅籍記》里有這樣的情節安排。你必須要認識到,即使是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在記憶上也會有誤差。在我的小說里,關于歷史的部分,從來不會作出特別確切的判斷。因為有些事情即使是你親身經歷過的,你也很難做出百分之百的精準判斷,更何況很多事情是他人經歷的,而你只是一個身處其外的聽眾。
Q:您去年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城市人群,是文學創作的原鄉和支點》的創作談。在文章里,您提到自己“對城市題材著了迷”,甚至是“有點一發不可收拾”的。應該看到,我們當下所討論的“城市”顯然已經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明顯區別。那時我們還可以較明晰地辨認“我城”“我鄉”,而現在,探究“誰的城”“誰的鄉”就顯得異常復雜而艱難。您的小說一直在探究城市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變遷。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這部《滅籍記》,您如何看待城市在您小說中的這種變遷?
A:在我之前一系列有關城市書寫的作品中,就體現出了你所提出的這個問題。因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主要還是關注城市小巷中的人事。我最近因為要寫一篇創作談特意去查了下資料,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1986年的時候,美國上映了一部機器人題材的電影《砍槌》,那部電影非常生動地設想了人類對于現代科技的濫用所可能觸發的種種后果。那么同一年我又在寫什么呢?我在寫一個叫作《過界》的小說,講述了街巷間的家長里短。八十年代開始,蘇州小巷里很多家庭的孩子長大了,要分房睡,但房子小,怎么辦?有些家庭就會搭違章建筑。你搭你的,我搭我的,過了界,雙方就產生了矛盾。這就是八十年代中國的現實情景。而同期的美國電影人已經在討論機器人的問題了。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蘇州還是“老蘇州”。因為還沒有開始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但后來我為什么不寫“老蘇州”了呢?因為“老蘇州”消失了。盡管現在蘇州還保存著幾條老街,但是這些老街保存下來的主要功能只是供人觀賞,而不是讓人生活在里面。同時,現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差別也越來越小。
Q:您現在對城市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A:我現在特別關注那些出生于邊遠地區,但經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他們留在城市打拼,這批人的生活還是比較艱辛的。他們有了知識,有了學歷,他們的理想就自然而然會比較高。但理想一高,壓力也會隨之增大。這里所說的“壓力”也包括現實層面的部分,比如租房買房,結婚生子。這些都很值得關注。
Q:據說您現在正在創作的一部小說,就是關于青年群體在城市里打拼創業的。能和我們小小透露一下嗎?
A:這是我現在在寫的短篇小說,主要講述了幾個外鄉的知識青年在城市里開辦搬家公司的故事。我寫小說往往希望透過這些人物,看到他們背后一些深層次的東西。搬家公司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很多家庭搬家都必定要找搬家公司,而搬家公司內部也有很多“玄機”,非常值得我們去了解。但問題在于,假如你無法寫出這些表層背后的“形而上”,那就沒有任何價值。
Q:您似乎非常有意識地在自己的小說中去平衡“形而上”與“形而下”?
A:其實在我早期的小說創作生涯中,并沒有真正意識到要去平衡“形而上”與“形而下”。也許那時我的小說里會有“形而上”的因素,但完全是不自覺的。比如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一批小說,寫的比較“淡”,但這里面其實包含著某種“形而上”的內質。但這種“形而上”的內質又說不清。這其實是一種特殊的小說樣式。但另一方面來看,這樣的小說又可能不太受讀者歡迎。比如北方人喝碧螺春,他會覺得喝不出什么味道,因此覺得不好喝。我現在回頭來看上世紀九十年代寫的那批作品,我會覺得這是自己較為喜歡的小說。現在我在寫的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你看題材和人物,好像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你假如無法通過小說傳遞出一些“形而上”的東西,這種寫作就不具備太多意義。
Q:最后一個問題還是回到了“青春”這一話題。對于那些打算從事文學創作的年輕人,您會提出哪些建議?
A:光鼓勵是沒有用的。只有靠年輕的寫作者自己去摸索,去找到門道。到了一定階段,你就會清楚地知道自己適不適合走這條路。我覺得這是最為重要的。
主持人 何平
責任編輯 李檣
附:范小青在《青春》發表作品名錄
《上弦月》,《青春》1981年第2期,短篇小說
《迎面吹來涼爽的風》,《青春》1983年第11期,短篇小說
《拐彎就是大街》,《青春》1985年第9期,短篇小說
《片段》,《青春》1990年第12期,中篇小說
《路邊的故事》,《青春》2001年第9期,短篇小說
《行走在東山》,《青春》2017年第1期,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