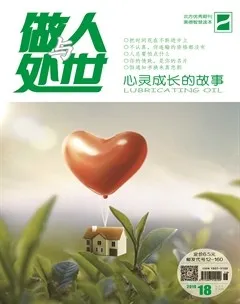穿越《聊齋》
臧建立

蒲家莊,一個普通村莊,但因有了蒲松齡而聞名遐邇。蒲松齡故居以聊齋為主題,向外輻射,院落門庭錯落有致,青色的磚墻,黑色的方格木窗欞,青綠扶桑藤爬滿了墻和窗,池橋掩映,山石堆疊。
在一個明朗的日子,我們來會晤那個寫妖寫魔的蒲老夫子,來聆聽布滿恐怖又充滿魅力的鬼怪故事。我們悄悄地來,不要驚醒蒲老夫子的冥想構思,不要騷擾狐仙妹子那執著的愛情……擺攤賣工藝品的,可不管這些,只顧高聲叫賣,長腔短聲,此起彼伏。工藝品做工考究,琳瑯滿目,最吸引眼球的當數大大小小各式各樣各色的狐貍,或憨態可掬,或滿臉的嫵媚,或滿身的妖氣,有絨毛的,有陶瓷的,有塑料的,還有泥塑的。
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居士,室名聊齋,世稱聊齋先生。他出生于一個逐漸敗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舊志稱其“性厚樸,篤交游,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 。19歲應童子試,接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名震一時。以后屢試不第,直至71歲時才成歲貢生。迫于生活,他除了為同邑人寶應縣知縣孫蕙做幕賓數年之外,主要是在本縣西鋪村畢際友家做塾師,舌耕40余年,直至69歲撤帳歸家。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歲。其詩句“世上何人解憐才”“痛哭遙追阮嗣宗”“獨向隴頭悲燕雀,憑誰為解子云嘲”,抒發了他壯志難酬且不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視世俗平庸和懷揣理想之火的卓高情懷。
“一生無緣附驥尾,三生有幸落孫山。”蒲松齡寫《聊齋》,除了天分、愛好,更多的是無奈。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和“學而優則仕”的封建社會,一生未能中舉的蒲松齡又能做何選擇?從來就沒有救贖主,人的靈魂最終只能靠自己來拯救。“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寒來暑往,日復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載筆”,終于完成了他的“孤憤之書”。他以畢生精力完成《聊齋志異》8卷、491篇,約40萬字。內容豐富多彩,情節幻異曲折,跌宕多變,文筆簡練,敘次井然,被譽為我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此書是“專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為其故居題聯,贊其著作“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評價其“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
《聊齋志異》中的女主角,大多為狐貍、鬼魅、神仙等異類,應叫另類,因為“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怪,牛鬼蛇神倒比正人君子更可愛”。他們純潔、善良、癡情,為了愛情不畏生死,不畏寂滅,不畏強權,不計得失,縱魂飛魄散,終是癡心一片,情深如許,不改初衷,矢志不渝,堅定不移,無怨無悔。法國著名作家雨果說:“想象是偉大的潛水者。”蒲松齡雖然貧困不得志,但是他特別擅長想象,《聊齋志異》就是一個天才作家的想象才能和藝術才能的集中表現。
蒲翁在自序中說自在寫這本“孤憤”之書時是“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懷,癡且不諱”。癡是一份執著,一份耐性,鍥而不舍,持之以恒。正如曹雪芹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此中味?”濃濃的筆墨就是漫天飛翔的云朵,演說著人世間的真善與丑惡,酣暢地盡抒人世的滄桑與蠱惑。蒲翁、曹翁,還有許多。他們不為職級待遇,不為稿費版金,不獻媚高官,不謀求聞達。他們的所作所為,怎一個癡字了得!他們不僅是為了一片自己的性情,更是為了那種高貴的和高尚的歷史責任感,還有悲天憫人的終極關懷和宇宙意識。
傳說蒲翁在柳泉旁邊擺茶攤,供奉清茶一杯,請過路人講奇異的故事,講完了回家加工。路人秀口一吐,就是故事;蒲翁秀手一寫,就是經典;清茶一杯,那是故事生生不息的源泉;抖抖衣衫,灑落那么多栩栩如生的經典。水還是往日的水,依舊澄澈如昨;風還是昨日的風,搖曳柳眉如歌。單薄的柳樹也蔥蘢成當代的紳士,我們游人是來取經的,滿腹的故事也想向老夫子講講,讓老夫子加工成經典。
我們站在樹下,蒲翁今何在?清瘦的身影,為誰守候一個傳奇的人生?空蕩蕩的衣袖,像一株經年的老柳,在柳泉邊佇立,須發冉冉的老翁為誰執手相送?荷花仙子的嬌羞,嶗山道士的空靈,誰在夢里追尋聶小倩單薄而美麗的身影?
一卷線裝的《聊齋》,讓我的思緒穿越滾滾紅塵,走過一彎曲徑,抵達一個個夢幻的迷宮,有散失的迷離,有無奈的彷徨,有觸目的驚悚,有凄美的訴說,有固執的執著,有執拗的憧憬,有縹緲的希冀,有羽化成仙,有仙風道骨,有不知今夕何夕。疲憊的蒲翁在蒼茫的夜色里點化一只狐,或通體如火,或雪白似玉,娉娉婷婷,走進一個落魄書生的家園:事炊縫補,相偎取暖,為之以幽蘭之息拂然入夢,安然于悠遠的時光家園,任風吹草長,任寒來暑往,只為等待那段善緣。那只被書生放生的白狐懂得: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再。
我只希望牽著蒲翁的青布衣衫,我愿成為蒲翁舊紙箋上暗夜徘徊的落魄書生和暗香浮動的月色媚娘……身處聊齋,冥冥中,我聽到蒲翁喃喃自語:“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