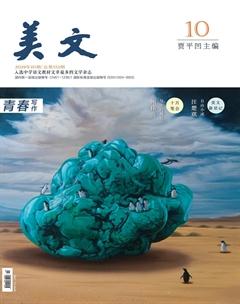桐城派的一篇清新小文
陳楠
清代的中國文壇熱鬧得不像話,歷朝歷代曾經興盛過的文體,到了清代都復蘇了,又攀上了另一個高峰,散文當然也不例外。除了備受推崇的“乾嘉三大家”,清代散文界還有更加有分量的一個流派——桐城派。姚鼐就是桐城派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說起桐城派,其散文風格形成得早,名稱得來的晚,清末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苞、劉大櫆、姚鼐善為古文辭后,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桐城也被譽為“文都”。
曾國藩是個很客觀的人,他按時間順序說明了桐城派的發展。其實桐城派第一個重要人物是戴名世,接下來才是方苞。戴名世他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戴名世身涉清初三大文字獄的“南山案”,最終被斬首,與其交好的方苞因為給《南山集》作過序,也頗受牽連,被下獄判處死刑。可是方苞幼時聰穎,在二十二歲初中秀才之時就進京入國子監,眾人對其古文評價甚高,被稱為“歐韓復出”“北宋后無此作”,當時的文學大家、理學大家、飽學之士甚至高官都對他推崇有加,李光地也認可其文品,給了他很多提攜和幫助。康熙帝賞識方苞的才華,李光地拼命為其周旋,方苞在刑部大牢關了一年有余就被放了出來,還因禍得福被康熙召進了南書房,以后三十年仕途順利。方苞的名篇《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堪稱經典。可是方苞作文講究“義法”,對作文有諸多限制,說穿了“義”就是倫常禮法,“法”就是對遣詞用句的規范,在這樣才華橫溢的人的嚴格要求下,桐城派古文顯得拘束了。
劉大櫆,上承方苞,下啟姚鼐,對清代散文貢獻非常大。科舉不利的劉大櫆二十九歲出游京師,五十四歲仍舊名落孫山。在京城許多年沒有功名的劉大櫆一直以做門客為生,雖然連挑剔的方苞都為其文章喝彩,可他終究沒有得到與名聲相稱的地位。京城無可留戀處,劉大櫆回鄉講學,弟子如云,從學者以詩名聞世者很多。劉大櫆的為文主張很有意思,他有一個“神氣音節”說,把形式分成音節和字句,音節、字句和神氣的關系是手段與主題、表現與被表現的關系,這是難得的對形式和內容關系的正確理解。劉大櫆還主張文章不可一味泥古,拋棄道學家的視角,更多地從文學家的視角去欣賞,這是對方苞理論主張的補充和超越。
姚鼐就是劉大櫆晚年的得意門生,姚鼐的伯父姚范,也是當時的文章大家,與劉大櫆交好,所以姚鼐少時師從劉大櫆。雖然后人認為姚鼐的文章更為厚重,可姚鼐對劉大櫆的尊重始終如一。桐城派古文到姚鼐才達到了真正的高峰,姚鼐沒有方苞的狂傲,也不似劉大櫆科場失意,他三十出頭得中進士,仕途順利,累遷至刑部郎中、記名御史。再被推薦修《四庫全書》一年有余,告老還鄉,在各館任講席,悉心教授,培養了大批弟子,壯大了桐城派的隊伍。姚鼐為人淡泊名利、專心向學,所得束脩皆資助貧苦,家無余才。姚鼐八十五歲時感覺時日無多,作遺書,當中寫道身后之事:“人生必死,吾年八十有五,死何憾哉!吾棺不得過七十金,綿不得過十六斤,凡親友來助喪事者,便飯而已。不得用鼓樂,諸事如此。汝兄弟不得以財帛之事而生芥蒂……”足見其品格。
在戴名世的引領之下,經過方苞的發展和劉大櫆的升華,到了姚鼐,他提出了“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并舉的觀點,對方劉二人的理論加以綜合,再進一步提升,達到了全新的高度。姚鼐的考據簡潔清晰,很有價值,但讀起來還是枯燥了些,不如他寫的這些鮮活小品更能體現其神韻。《登泰山記》是當之無愧的名篇,文章氣勢恢弘壯大,筆力強勁卻又旖旎多變,頗得山水丹青之妙。而這一篇《游媚筆泉記》短小清新,頗有性靈的味道。姚鼐淡泊名利、為人周正,在性靈這一方面卻又與性靈派大家袁枚相交甚厚,袁枚去世,他不顧家人弟子好友的阻攔,堅持為袁枚寫了墓志,極力為袁枚辯解,不愿世人以俗眼待之。
來看看這篇清雋小品吧,文章層次清晰,先寫山水,桐城西北龍眠山的山勢與源出于此的龍溪水勢。接著寫沿途所見,一行人循龍溪行,正值陽春三月,宿雨初睛,沿龍溪十余里,水聲響亮,樹石沿溪散布,溪下有潭,有如出浴駿馬一般的大石,攀大石上,可“俯視溶云,鳥飛若墜”。后一行人循崖游覽,又見奇石, “連石若重樓,冀乎臨干溪右”,并討論這是否是北宋畫家、龍眠隱士李公麟的“垂云泮”。奇石又與奇樹相伴,樹生石縫,有能蔭數十人之大,淙淙水聲中,忽又“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又“南有泉”,這才點到了正題:媚筆泉——“泉漫石上為圓池,乃引墜溪內”。曲曲折折,飽覽山光水色終達泉邊。結尾收轉,先寫左學沖老人筑室于媚筆泉水池畔,室未筑成就邀人入飲頗有雅興。至傍晚,天氣陰沉,天籟之音起,“山風卒起,振肅巖壁,榛莽、群泉、磯石交鳴”,于是游客“悚焉”,興盡而返。
媚筆泉,從名字看應有嫵媚山色、潺潺水流,文中卻也提到如此。作者筆調清新,如水般纖敏柔細、曲折回環,將山形水勢、沿途風光娓娓道來。然而此文有溪泉也有山石,山石常是高聳險峻的。一路走來,陰柔之美與陽剛之態巧妙結合,中又點染前朝幾位名士的痕跡,交代同游左老丈的雅興。讓人感覺似乎有讀柳文之靈透,而文末交代伯父同游,囑托他作記,又有唐代古文之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