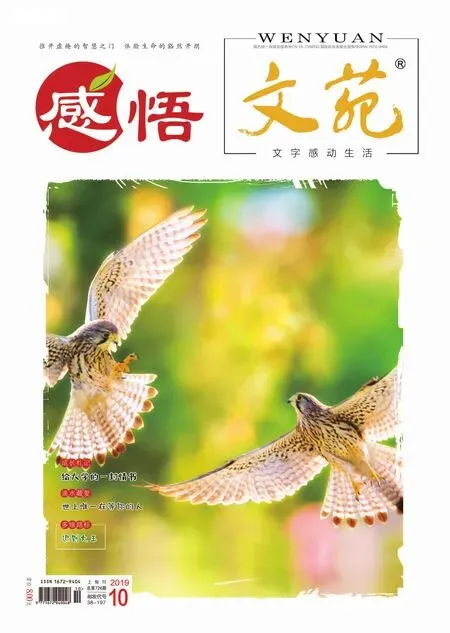日本大學的學伴制度
文/綠島
綠島,日本沖繩大學教授。

本世紀以來,教育國際化已成為眾多國家面臨的共同課題,日本也不例外。在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一些國家出現了學伴制度。所謂學伴,日文叫“チューター”,英文叫“Tutor”,原意是家庭教師、導師或一對一的教授。隨著教育的國際化,其含義有所延伸,現指本國學生與留學生在學習上平等互助、互幫互學的伙伴制度。
學伴制度能幫助留學生盡快提高語言水平和生活能力,了解當地文化、適應當地環境等。從2000年起,為了幫助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提高日語水平,促進本國學生接觸多元文化、勤工儉學,沖繩大學建立了學伴制度。對此,有留學經歷的我深以為然。
當年我作為“老三屆”大學生赴日本游學時,還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日語教育,起初在東京一所大學的比較文化研究所進修。初來乍到,無論學習還是生活都特別“懵圈”,東南西北都找不著,住處離公交車站特別遠,也沒有任何代步工具,出行極不方便。那時候特別期待能與當地學生交往,盡快融入環境,但大學當時沒有這樣的制度。我住在外國人教師館所在的校區,沒有學生住校宿舍。一到假期,偌大的校區空無一人,每日只能與野鵪鶉、野鴿子、野斑鳩為伴,想找個日本學生學日語,難度很大。如今留學生在日本享受到的待遇,令人羨慕不已。
歸納起來,日本大學的學伴制度具有需求自愿、校方助力、責任自負幾個特點。
需求自愿
剛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時,人們在語言、交通、購物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遇到障礙。留學生往往獨自一人前往留學目的地,從下飛機到前往學校,再到找到房子安定下來,都需要外界的幫助,學習上更是如此。因此,“特殊關照”就成為初次留學人員的共同待遇。
學伴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留學生在學習所在國的語言和文化時,的確需要當地學生“關照”。這是大多數留學生共同的需求。從本質上講,學伴是大學生之間在互相學習語言文化的需求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義工服務形式,或者是一種互助互學的形式,因此需要留學生自愿提出申請,本土學生自愿參與,校方沒有主動為留學生安排學伴的義務。
如何滿足需求或提供條件是另一個問題。日本大學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囿于規模和條件的限制,各大學幫助留學生的方式不盡相同。比如,我所在的學校不一定會有人到機場或車站為留學生提供接機接站導引。而且,日本很多大學沒有學生宿舍,留學生只能租借民居,一切都需要親力親為。由此就產生了矛盾:一是留學生主觀上需要幫助,二是環境條件的客觀限制。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成為越來越多的學校面臨的課題。
校方助力
學校通常利用每年入學典禮后留學生集中開會的時間,介紹本校有關留學生的注意事項,其中包括學伴募集。如果留學生向學校主管國際交流的部門提出尋找學伴的愿望,校方會推薦愿意做學伴的本校學生,安排雙方會面,并根據學生的需求在初次見面時協助溝通。
安排學伴的出發點可以是幫助國際學生適應新環境,也可以是促進學生之間的跨文化交流,還可以是增加收入。根據我在歐洲的經歷,一般而言,發達國家針對高學歷學生(碩士、博士或訪問學者)項目發獎學金是為了吸引高端人才,而本科留學生的學伴項目部分以自費為主,尤其是自負盈虧的私立大學。因此,“付費學伴”對一些學校而言是重要的經營項目。
為學伴的“供需雙方”牽線搭橋后,學校往往讓學生自行交流,不過多介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的女兒在美國留學,據她介紹,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高校也有類似項目。
提供學伴服務,學校要注意處理民間交往的分寸,引導本土學生和國際學生平等交流。校方最好的辦法就是采取自助交往形式,在管理上做到既合理公平又不失體面,讓民間交往回歸民間,使得本國學生和留學生之間既能互動交往,又可平等自在。
日本、美國和歐洲國家沒有統一的學伴模式。據我在德國游學的經歷,歐洲一些國家的學校基本不提供這樣的有組織服務,比如德國和法國。哪怕國際學生的需求再迫切,也只能自己在公共留言板上留言招募學伴。
責任自負
在國外,學伴事務通常由學生團體負責,校方參與較少。大多數學伴項目采取“義工”招募或民間互助的形式,多半是無償的。校方在提供具體幫助時,往往不采取行政手段,比如頒發文件、指派學生參與等。
無論在日本、美國還是歐洲國家,學伴制度大同小異,都是學生之間自發組織的互助勸學。學伴制度在學習之外的部分是人際交往,多是成年人之間的同性或異性交往,建立在自我約束、自我規范、自我負責的前提上。
在日本,學伴制度很少引發情感問題。學伴活動大多發生在公共學習場所,比如教室或自習室等。若雙方產生感情糾葛,校方一概不予負責。學生需要就醫就去醫院,需要找警察就去當番(派出所),需要自己負責的就自我消化。對于教學以外的問題采取責任自負原則,可以避免所謂的“制度后遺癥”。
處理人際關系,需要講求尊重和互惠。學伴制度,無論對校方還是學生而言,背后都沒有復雜的利益或情感,自由又寬松。當然,校方有義務給予愿意參與學伴活動的學生們必要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