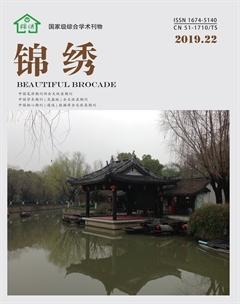毒品代購行為認定
饒炳基 黃山鐘
摘 要:代購毒品,一般是指吸毒者與毒品賣家聯系后委托代購者前去購買僅用于吸食的毒品,或者雖未聯系但委托代購者到其指定的毒品賣家處購買僅用于吸食的毒品,且代購者未從中牟利的行為。本文通過對各個有關毒品代購的會議紀要和規定進行分析,對毒品代購行為展開分析。
關鍵詞:毒品;代購;紀要
2001年《南寧會議紀要》規定: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僅代買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的最低標準,構成犯罪的,托購者、代購者均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由于《南寧會議紀要》對代購毒品行為與販賣毒品行為的界定不夠明確,給司法機關在實務中的認定帶來了較大的困難,也讓許多僅實施了代購行為的行為人可能被認定為販賣毒品,從而受到更為嚴重的刑罰。為了明確界定二者之間的界限,《大連會議紀要》在該規定的基礎增加了兩條:代購者從中牟利,變相加價販賣毒品的,對代購者應以販賣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居間介紹、代購代賣的,無論是否牟利,都應以相關毒品犯罪論處。前款是對非法持有毒品罪與販賣毒品罪作出了具體區分,統一了實踐中關于二者的分析。而后一條的規定,僅概括性的表述了居間介紹、代購代賣毒品的行為構成了犯罪,但并未明確表述構成何罪。實踐中犯罪情形和種類紛繁復雜,不同場所不同情況下既有可能構成運輸毒品罪,也有可能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這為實踐中司法機關對行為人罪名的認定帶來了困難。也導致各地對類似案件的處理產生差異。實踐中發生爭議較大的是在運輸中代購者被抓獲該如何定罪的問題。《南寧會議紀要》規定:如果代購毒品的行為人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抓獲,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是為了實施其他毒品犯罪行為的,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論處;《大連會議紀要》對此作出了調整:由原來的只定非法持有毒品罪改為按照實際的毒品犯罪行為定罪處罰。這一規定從本質上來看并沒有具體表明如何認定運輸毒品罪。從《大連會議紀要》的起草過程來看,該規定的本意是,當吸毒者運輸毒品數量大,明顯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時,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而不再像《南寧會議紀要》規定的那樣一律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
為此,《武漢會議紀要》對此作出了專門規定:在沒有證據證明吸毒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情況下,對其購買、運輸、存儲毒品的行為,直接以數量較大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同時,對吸毒者運輸毒品的行為,直接以數量較大標準作為區分非法持有毒品罪與運輸毒品罪的界限。《武漢會議紀要》的修改,明確了運輸毒品罪與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界限,為實踐中司法機關認定罪名提供了裁量標準的。同時,這也降低了運輸毒品罪的入罪門檻。《武漢會議紀要》之前,對運輸毒品罪的認定數量標準是刑法規定的數量較大基礎上再上升一個層次,而修改之后認定數量標準下降,即將會有更多的運輸代購毒品行為納入運輸毒品罪的范疇,加重了對行為人的處罰。
從《大連會議紀要》的規定來看,行為人是否從中牟利是區分代購毒品行為和販賣毒品行為最本質的標準。為了進一步明確何為“牟利”行為,在前兩大會議紀要的基礎上,《武漢會議紀要》作出了更加具體的規定:行為人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開銷之外收取“介紹費”、“勞務費”,或者以販賣毒品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為酬勞的,應視為從中牟利,屬于變相加價販賣毒品,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同時,《武漢會議紀要》中對于代購毒品作出了部分修改:行為人為吸食者代購毒品,在運輸過程中被抓獲的,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運輸毒品罪的共犯論處。
從三大會議紀要的規定與趨勢來看,代購者是否從中牟利是區分純代購行為與販賣毒品犯罪的關鍵點,這讓販賣毒品罪的認定更加嚴格。但是,2018年3月22日浙江省高院發布的《關于辦理毒品案件中代購毒品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后簡稱《紀要》)似乎與三大紀要的趨勢有所背離。根據《紀要》第一條規定:行為人向吸毒者收取毒資并給付毒品的,應當認定為販賣毒品的行為。確屬為吸毒者代購毒品且并未從中牟利構成其他犯罪的,也應依法定罪處罰。同時,第四條規定:行為人為吸毒者代購并運輸毒品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運輸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對于代購毒品中的居間介紹行為,僅起到為不以販賣為目的的吸毒者介紹販毒者,但與販毒者不存在聯系、合謀的作用的行為人不應被認定為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犯或與購毒者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僅能對其處行政處罰。從本條規定所使用的措辭來看,行為人向吸毒者收取毒資并給付毒品的行為一律都構成犯罪,若行為人從中牟利則為販賣毒品罪,未從中牟利滿足犯罪構成要件則構成運輸毒品罪或是非法持有毒品罪,這是從根本上取消了無罪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