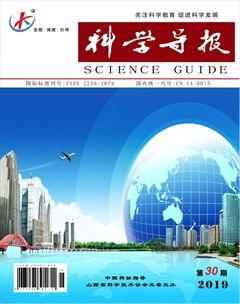淺談潘玉良的自畫像
摘要:現如今,很多人提起潘玉良,就會不自覺的把她與“妓妾”聯系起來,或者用“傳奇”等字眼去解讀她。其實,她只是終身不愛風塵,卻被風塵所誤;她只是從人世的黑暗底層掙扎出來的新女性。在漫長的蛻變中,她一直對人、女人、自己的身體做著不厭其煩的觀察、感知和認識,她都能真實的記錄下辯證的思考。她的自我成長和覺醒,是通過那一系列自畫像完成的。
關鍵詞:潘玉良;自畫像
自畫像不僅是藝術家的繪畫技巧和對現實的呈現與表達,更是藝術家的情緒、處境的內心獨白。在潘玉良第二次赴法學習之后,其藝術作品趨于成熟,這與她的出身和國內生活的坎坷經歷有著直接的關系。
一、憂郁之像
人生的苦難和漂泊的哀愁,像不散的陰霾纏繞著潘玉良的人生,從幼年成為孤兒到少年被賣。好不容易被丈夫潘贊化從青樓救出,并一路篤學成為國內最高藝術學府的教授,只因為曾經的不潔身世,又遭到世俗詆毀,被迫之下,去國離鄉,一生都沒回國。潘玉良嘗遍世間幾乎所有的苦楚,閱盡人性的卑污。致使她只能對著畫布上已經異化的自己,以此來訴說自己的難言之痛。所她畫出的,全是隱忍的思念、憂郁和哀愁。畫面上常以高貴的紫色、火熱的紅色和金色的黃色來釋放自己的情緒。畫布上的她常常眉頭緊鎖,雙唇緊閉,一雙憂傷的、憤懣的眼睛游離于畫外,與觀者四目相對。那種觀望和審視的情態令人心痛。
二、期許之像
潘玉良的諸多的照片與其自畫像相比,反差極大,其本人五短身材,頗為壯碩,衣著潦草,皮膚粗糲,短發蓬亂而不事打理,臉寬且長,眉毛高挑,鼻子扁塌,厚唇緊閉,凜然不可侵犯,魁悍如男相。真實版的潘玉良與嬌柔嫵媚絕緣,性情豪放,大嗓潑辣,能喝酒,能劃拳。其丈夫潘贊化在1955年的家書中也評價道:“你一生不講究裝飾,更有男性的作風。少年騎馬射箭,都是好手。”
就是這樣一個不修邊幅的、性格大大咧咧的人,自知沒有天生麗質的外貌,更沒有后天良好的養成環境,所以需要自己付出全部的心智、精力才能攻克高深的藝術專業,便無閑暇之心去裝扮自己,一心撲向創作,一心奔向向往的藝術殿堂。但是她終究不甘,明明是女子身,她的內心開始涌現出女性的百媚千紅,她開始自畫像的創作,讓心中所幻想的女性美投射到她早期的自畫像中。這些自畫像往往用色豐富,筆觸明快。畫中的女子一律身材高挑,皮膚白皙、妝容精致、姿態優雅;頭發被精心盤飾,穿著的衣服極具古典韻味的中式繡花旗袍;纖手執扇或者書籍,身體旁邊往往被鮮花包圍著。潘玉良把自己刻畫成一位周身散發著令人過目不忘的東方氣質的女性形象。然而,真實的潘玉良與其自畫像相差甚遠,與其說是失真的粉飾,不如說是她在用繪畫重塑他人期許中的自己。
三、覺醒之像
飽嘗了人性之惡的潘玉良,在歷經滄桑后忽然悟出一個道理:“藝術史最高的境界和唯一的出路,只有藝術史肯定人、祝福人。”回到法國后,她收起悲傷,決心主宰和謀劃自己,將剩下的生命全身心投入在繪畫里,以此在支撐風雨飄搖的人生。她結合在法國研習的油畫、在意大利修學的雕塑和本身的中國水墨畫的基礎,借鑒了印象主義以及野獸派等眾多西方繪畫流派的風格和韻味,逐漸探索出屬于自己的藝術風格——“合中西于一治”。功夫不負有心人,在1945年前后,潘玉良以優異的成績當選為中國留法藝術學會的會長。此后,她的藝術生涯進入了全盛時期。藝術事業上的成就,讓潘玉良一直苦苦追尋的自我價值,忽然得到了社會評判標準的肯定,她原本自卑自憐的情緒得到了拯救,自我的身份價值逐漸得到實現。盡管在異國他鄉可她的生活依然艱辛,她卻堅持不談戀愛、不入法國籍、不和任何畫廊機構簽約。她對自己的性別和話語有了更深一層的覺醒,開始建立起完全獨立的私語空間。如1940年創作的《紅色自畫像》中潘玉良站在窗前,身體呈現“S”型,整個人的重心放在畫面的左手邊,人物右肘倚靠在窗邊,她的眼神斜視著觀者,滿臉不屑的樣子。這與同年創作的《自畫像》相比,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此時此刻的潘玉良已經不再刻意的美化自我,而是將真實的自我直接呈現在畫布上。只是人物臉上依然充滿著憂愁。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女性不得搖于窗前”的保守年代,“窗”意味著開放性的空間,這打破了常被描繪在封閉空間中國女性肖像表現的慣例。由此,也可以看出潘玉良對傳統女性壓抑的身體,精神反抗的意識。
潘玉良后期的自畫像更具有表現的意味,她不僅直面了真實的自己,甚至夸張地畫出了自己的衰老與丑陋。潘玉良用近景特寫的方式,對自己的表情和神態都作了重點的刻畫,背景沒有任何的裝飾物趨于平面化,強調的是潘玉良對自我的表達。畫面上,人物眉目上挑,臉上的皺紋被清晰的刻畫,人物的目光直視觀者,眼神中帶著冷冽和審視的意味。由此,從潘玉良后期的自畫像來看,她不再去附庸男人眼中所理想的樣子,而是以強烈的語言,描繪著自己應該有的樣子。此時,在她心中,兩性的傳統關系已經徹底的瓦解了,女性不再是一味地順從、溫柔、優雅、嫵媚和膽怯的,而是可以擁有智慧、反叛、懷疑、審慎和嚴肅的表達。由此可見,潘玉良終于擺脫了男性藝術審美秩序和審美體系里符號化的女性形象,獲得了獨立存在的意義。潘玉良的的畫已經有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融合了中西方的藝術文化,通過塑造線來表現造型,并且她十分善用中國畫中特有的線條來勾畫人物,描繪的線條也極其流暢。她的自畫像個性張揚,有自己獨特的色彩,沒有一絲女性的嬌柔和嫵媚,反倒是一身的男子氣概,眉宇間透著她對社會、對人生的憤懣和哀怨,并且深刻揭示了舊社會中女性的生存狀態。潘玉良在中西合璧的道路上開辟了新路,賦予了自畫像獨特的東方情調,她以自畫像的形式開拓了民國女性美術的新局面,做出了驕人的成績,并為今后女性在藝術創作與探索上帶來了啟迪與杰出貢獻。
四、總結
藝術對于潘玉良而言是愉悅也是慰藉,無論人生遭遇怎樣的坎坷經歷,她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以自強不息的堅韌和毅力開掘自我的天賦,也煉就了面對苦難的豁達。潘玉良為人隨和、開朗、豪爽,卻并不因此削弱骨子里的倔強和堅持,耐苦并不言苦,這是女性的一種自愛,也是弱者的一種堅韌,這樣的堅韌和自愛潛移默化,是她一生的自我定位。她的要強引領她用實際行動去突破當時以男性為主體的藝術領域。實際上,藝術對她來說是一種自我救贖和樹立自我尊嚴的方式和途徑,特殊的生活經歷和處境,使得潘玉良的畫面充滿自憐、自愛、自強的氣息,那是她對自我生命的嘆息和獨自承擔。民國新女性畫家在繪畫上進行不懈的探索,對女性繪畫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她以自身的視角對西方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她把自身的經歷納入到自己的創作中,通過畫面去表達女性自我的審美感受。在潘玉良身上我們看到了她為爭奪藝術話語權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秉承著對藝術執著,挖掘自身對事物特征的感知力,在藝術探究上做出驕人的成績,同時給當今的女性畫家的創作帶來了啟迪作用。
參考文獻:
[1] 李超.《中國現代油畫史》[M].上海出版社.2007年第12月第一版
[2] 陶詠白.《中國女性繪畫史》[M].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
[3] 《畫魂——潘玉良傳》[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年
作者簡介:
司佳(1996.2)女,漢族,籍貫:河南商丘,廣西藝術學院美術學院,18級在讀研究生,專業:現代插圖研究
(作者單位:廣西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