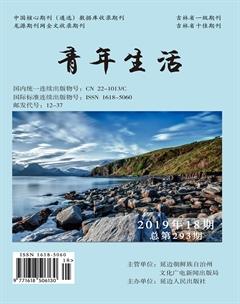吳讓之藝術初探
張涵碩
摘要:吳讓之生于江蘇揚州,最終成了皖派的代表人物,甚至是提到這兩個字首先想到的便是他。鄧頑伯也就是鄧石如在他的這一生中起到了又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吳讓之交友甚廣,早年間與現在書法人耳熟能詳的幾位清末大家有著不同形式的交際,這些交友形式中對于他金石印章的傳播也是起到了十分積極地作用,甚至在他的一些文獻資料中搜集到的極具“吳氏”印風的巔峰之作也是產生于其間。
關鍵詞:吳讓之;鄧石如;皖派;
吳讓之篆刻伊始
晚清時期的書法篆刻金石藝術層出不窮,“印壇”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影響面及其廣。吳讓之的金石藝術打破了原有的“浙派”老大的局面,打開了“皖派”新格局。與此同時他的印風也為后世書家所學習,受他影響的書家不勝枚舉。以至于晚晴印壇之所以可以名留史冊,就是因為他的出現。直至今日,吳熙載的篆刻印風仍然受到印學愛好者的大力推崇。那么這樣一位影響著晚清和近現代印壇的書家他的篆刻又是從哪里起始的呢。
吳讓之印風與鄧石如
吳熙載篆刻作品以秦漢璽印為基礎,又兼以鄧氏書刻,具有十分鮮明的特點,自成一家。很多時候吳熙載的作品可以和鄧頑伯相媲美,這和浙派大多數作品整體風貌相近但并不相同。但事實正是他的高超技藝的冰山一角。學習鄧氏的同時刻兼學別樣,不受其習氣影響,這是當時很多書家做不到的。真正做到了青從蘭出勝之于蘭。他的作品第一次做到了文字字勢的屈伸仰俯,筆畫間的頓挫提按,翻轉處的用筆的快慢,筆畫間的呼應,沒有一點不恰到好處。
如果鄧氏的陰文印風是在漢代碑額以書入印的摸索階段,那么吳熙載的陰文印就已經是印書合二為一的典范。整體風貌俊潔端正,文字富于變化,精彩靈動,混圓潔凈。筆畫交代的清楚明了,律動感強烈,在白文印的基礎上極富有書寫性,并將富有意趣的一些字緊密而又不失協調的展現于印面之上。吳熙載的篆刻在鄧氏的基礎上,在刀工刀法上做了大的調動。眾所周知,金石篆刻里字的取法是篆刻的本質所在,長達數十年的臨摹漢印,專注學習鄧石如,將鄧體印由書出的創作原則爛熟于心,在創作的印章中講書法書寫的意趣最大化的表現出來,開拓出了新的意境。他把自己對于小篆書法的獨到的剛健飄逸貫穿在印面之上,書刀結合,透過刀鋒見筆鋒,天然渾成。他熟練的刀法展現在它對于沖刀的熟練掌握,用刀方法與印文相結合。在金石學中刀法是相當重要的一門語言,是書家表達自己情感抒發自己胸中意氣的一種手段。吳讓之就是這樣一位善于學習集大成的篆刻家。他從不默守陳規,以古為師的同時,將鄧派對于金石學的“以書入印,印從書出”藝術思考踵事增華。
趙之謙與吳讓之
眾所周知近年來無論是投展還是平時學習都脫離不了趙之謙書法,他在晚清書壇也占有很高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這位書壇匠人和吳讓之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吳讓之和趙之謙在書藝交流上有著很多聯系,趙之謙曾托好友魏錫曾把自己創作的數方印章帶給吳讓之點評,“息心靜氣,乃是渾厚。近人能此者,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這短短數十字是這幾方印章中的邊框,大多說人看到類似的話會覺得很不舒服,會以為是恭維但吳讓之卻不以為然在回信中提到“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贊一辭耶”。
讓之對趙之謙的篆刻作品有著很高的評價,回信中說的若干句話也是想表達說,以碑入印的人常常有,但是鄧石如已經運用的爐火純青,但是到了你這里卻已經超越了他。不但評價高,吳熙載在炎熱的夏天也為這位未曾謀面的好友攜刻了“鑒古堂”、“趙之謙”等白文四印,這四方印遙相呼應,疏密做的是淋漓盡致,輕松地把他自己樸茂靈動、平易質樸的創作風格展現給這位“學生”,同時這樣幾方印石最終也成為吳讓之篆刻藝術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
但趙之謙在同一年就改了對吳讓之的評價,趙之謙在《書揚州吳讓之印稿》長篇文章里寫道:“讓之于印宗鄧氏,而歸于漢人,年力久,手指皆實,謹守師法,不敢逾越,于印為能品。”是的,趙之謙這時候開始說了,吳讓之的作品完全遵守他老師的方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刻印的水平只能是能品,能品之外還有妙品、神品、逸品呢!說白話呢,意思就是說吳讓之的水平也還可以,從唯一人到能品罷了,這評價降了不少格。
總結
吳讓之篆刻使書印合一綻放出了別樣的光彩,讓書寫性最大限度的在方寸間展開來。臨摹其作品時就很容易將鄧式的爽快流美,同時又兼有許多有趣的變化。特別是在對與線條整體的把控對于印石上尖與圓粗與細,使作品更加有虛實相生的變換效果和生發的趣味性。缶翁評價其篆刻藝術曰:“讓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漢印璽探討極深,故刀法圓轉,無纖曼之氣,氣象駿邁,質而不滯。學習吳讓之書法藝術的人這樣評價他:學完白不若取徑于讓翁。”
參考文獻
張 瀛.印從書出”的得與失-鄧石如、吳讓之篆刻研究.阜陽師范學院美術學院,2010(28):151-153.
( 清) 魏錫曾. 吳讓之印存·跋[A]/ /韓天衡. 歷代印學論文選: 下冊[C].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