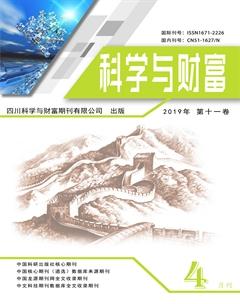“全面二孩”政策對女性勞動權益的影響
2013年全國人大通過了《關于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決議》,“單獨二孩”的政策正式啟動。2015年,中共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十三五”規劃,“二孩政策”全面放開。這兩個政策不僅標志著我國終結了長達30余年的“一孩政策”。
生育政策的變化踐行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從宏觀上來看,二孩政策的實行能有效的拉動市場消費,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延長人口紅利周期,達到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的目的。從微觀上來看,能夠滿足家庭的生育愿望,降低獨生子女家庭的失獨風險。同時,隨著這一政策的實施,打破了既有的女性勞動權益保護模式,也打破了女性職工與企業間平衡。
一、“二孩政策”對女性勞動權益影響的總體認知
勞動就業權是勞動權利的最重要的部門,也是公民享有權益的具體體現,就業權行使直接影響到勞動者的生存權。我國在《憲法》以及《勞動法》中都明確提出,保障女性享有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權利。而勞動力市場往往是買方市場,在實際求職以及工作過程中,一方面企業作為支付報酬的買方,當然希望員工為企業創造利潤。企業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得不考慮女性職工懷孕和生育所帶來的時間成本、金錢成本。在招聘中往往拒絕錄用女性職工或者未婚、未育女性職工。新的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得女性職工有二次生育的可能,這就意味著企業將面臨生育成本的二次疊加,在無形之中再一次抬高了女性的就業門檻。另一方面,企業在執行女性職工的生育政策時也很無助。《勞動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產假。1988年頒布施行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八條規定:女性產假為90天,但是在2012年新頒布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七條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假期。這就使得《勞動法》和《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在生育政策上不一致,客觀上給企業帶來了不便。
二、“二孩政策”對女性勞動權益的負面影響
(一)“全面二孩”政策對于女性求職的影響
1、顯性的影響
201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規定,符合生育條件的女性職工在生育方面將享受更多的產假。緊接著多省市制定了相關的生育條例。以江蘇為例,2016年3月30日江蘇省人大常委會修訂的《省計生條例》中明確規定,自2016年1月1日起,符合條件的生育夫妻,女方在享受國家規定產假的基礎上,延長三十天。雖然對于生育二孩的女性來說是重大利好消息,但對企業來講,無疑是增加了其勞動成本,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經濟呈下行趨勢,這一規定將會是企業負擔進一步加重。2015年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在北京等大中型城市針對女大學生求職的調研報告顯示,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普遍受到就業歧視,平均每個受訪者受到17次性別歧視。
2、隱性的影響
隨著我國法律法規的進一步完善,企業考慮到違法女職工保護的法律成本,以身試法的現象逐步減少,但這并不意味著就業歧視有所緩解。更多的企業把隱性的歧視作為又一個門檻,比如在招聘面試環節增加關于生育二孩的面試題,在入職培訓時反復強調單位可能會在轉正和職務晉升上可能會區別對待。在實際工作中,會刻意的加重女職工的工作負擔,逼迫其自己主動辭職等等。
(二)“全面二孩”政策對女性工作的影響
1、生育型職業中斷
從現實情況來看,女性在生育后一般面臨兩條路徑:一是重新進入職場,這屬于生育型職業中斷 :二是徹底退出職場。而就目前中國的社會現狀來看,絕大多數的女性會在生育后重返職場。對于女性職工來說,如果是生育型職業中斷周期長,則失去生育前的職業地位的可能性就大,并且會引起向下的職業流動。因此女性職工生育后重返職場的時間點是其職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具體到我國來說,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可能使得已婚已育的女性職工就業形勢變得不明朗。例如,在原計劃生育的背景下,以企業來說,青睞于已育的女性,因為已育的女性職工不需要再由企業承擔生育成本,但在新的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已育的女性職工存在再一次生育的可能,企業也將再一次考量雇用女性職工的成本與風險。由生育所引起的職業中斷將會導致女性職工在一系列的崗位上被剔除,最終會降低其長期以來獲得的社會、經濟地位。
2、呈向下的職業流動
職業流動本身是個人在企業中由初入職地位向現職地位的遞進過程。從流動的頻率來看,女性本身就低于男性,就流動方向而言,女性在生育后將明顯的呈現出向下流動的趨勢。一般來說,大多數產后的女性職工都希望繼續從事產前所從事工作。如果女性職工不能從事原工作,那么孩子將會極大的影響她們的選擇。尤其是在現今的社會,我國現在大中城市的職業女性普遍晚婚晚育,再加上接受了優生優育的理念,使得很多女性都會為了生育而去主動選擇舒適但待遇不高的工作。
三、保護女性職工勞動權益的對策與建議
(一)重新構建生育成本的分擔方式
我國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企業承擔了大部分的女性職工生育成本,同時期的國家政策則成為一種“虛”的存在。雖然企業承擔了大部分的生育成本,但企業卻通過降低女性職工收入的方式將部分剩余成本轉嫁給了女性職工本人。無論是生育成本由企業承擔還是由個人承擔都是顯失公平的。生育成本應當社會化,由政府來承擔生育成本。一方面生育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不能讓家庭來單獨承擔,可以通過稅收的減免、發放育兒津貼等方式減輕家庭的撫養壓力。以美國為例,根據“所得收入賦稅返還金法案”(EITC)的規定,生育一個孩子每年減稅3000美元,2個以上的孩子每年減稅5000美元。另一方面設置專有照料假,對于家有幼兒的、父母均在職的家庭允許其一方暫離工作崗位以照顧子女,還要保證假期結束后可以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
(二)制定“挽留性”政策
二孩政策的實行不僅應該考慮到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還應該考慮到女性職工育后就業問題。除了應該保障女性職工享受該有的生育假期之外,還應當幫助其如何留在職場。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關的“挽留性政策”。該政策的目的是在于促進女性職工的就業,減輕其照顧家庭的壓力。一是要繼續發揮法定生育假期的作用,保障女性職工在生育假期內的工作保留問題,另一方面還要制定相關的記錄機制,即個體在生育假期后的工作、職務、薪資水平的保值,以達到抑制職業中斷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同時對于處于撫育期的兒童配以兒童托管服務,政府一方面可以采取專項補貼的方式來讓女性職工購買兒童托管服務,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第三方購買,轉而免費提供給女性職工。政府的這一行為使得這一部分生育成本不會直接轉嫁給企業,而是由政府、社會、企業共同承擔,這樣既能降低女性就業成本,又可以讓政府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三)完善反就業歧視的法律法規
如果女性職工的就業權得不到合法有效的保障,那么她們將難以進入勞動力市場。針對這一問題,現行的法律法規都過于原則化,所以無論是出臺《反就業歧視法》還是修改現行的《就業促進法》等法律法規都要增加可操作性。一方面是要采用列舉的方式明確就業歧視的范圍和判斷標準 ,如果招聘崗位在設定時明確要求男性,需要說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則構成就業歧視。另一方面,明確就業歧視需要承擔賠償責任,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原則,求職者只需要證明用人單位存在性別歧視,而由用人單位證明不予錄用的理由存在正當性。最后禁止用人單位在招聘中詢問婚育信息或者設置孕檢等隱性歧視行為。
(四)推動勞動監察與公益訴訟并舉
勞動爭議仲裁是以勞動合同或者事實勞動關系為前提,這就使得在應聘過程中就遭受歧視的部分女性的合法權益得不到維護。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傳統的監察模式偏重解決個案,這就難以完全解決女性職工就業歧視的問題。公益訴訟本身就是為社會弱勢群體服務,維護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工具。女性作為社會弱勢群體也正是公益訴訟的服務對象。同時公益訴訟可以達到女性表達訴求、解決糾紛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公益訴訟能夠引起廣泛的公眾討論。在實際操作中,國家可以以勞動監察部門、婦聯等組織規定為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的機關。這樣既可以利用勞動監察相關權力又能夠發揮婦聯的功能,更好的保障女性職工的權益。
四、結語
女性職工的勞動權益,不僅關乎女生的就業權和生存權,更關乎著社會的穩定、家庭的和諧。我們應該在依法治國的道路上,通過個人、單位、國家的共同努力,推動全社會形成保障婦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制度共識。
參考文獻:
[1]謝慧蓉.淺析全面二胎原因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J].新經濟,2016(1).
[2]江蘇省計生條例
[3]侯建斌.全面二孩或加劇女性就業歧視——委員建議盡快制定反就業歧視法[N].法制日報,2016-3-15:009.
[4]任虹陽. “單獨二孩”政策對女性權利的影響研究[D].廣東財經大學,2015(4).
[5]李芬.工作母親的職業新困境及其化解——以單獨二孩政策為背景.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7月第17卷第4期.
作者簡介:
周勇,男,漢族,江蘇南京,大學,單位: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究方向:勞動關系、勞動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