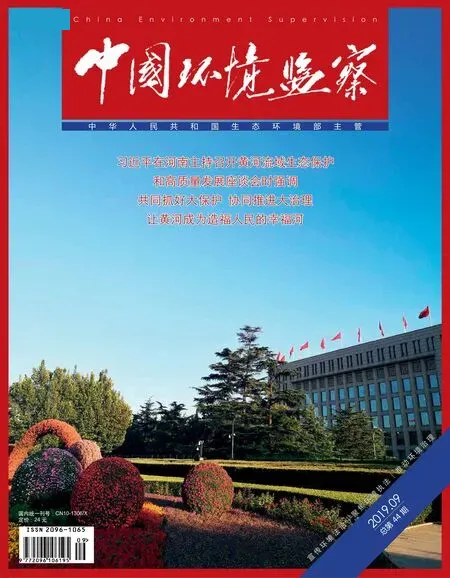垂改后,生態環境分局能否以自己名義實施行政處罰?
文|賀 震
目前,省以下生態環境機構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已全面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結合新一輪機構調整,原市縣環境保護局更名為生態環境局。全國大多市縣局已完成掛牌,部分縣(市、區)級分局(以下簡稱縣局)作為設區市局(以下簡稱市局)的派出機構已完成人員關系劃轉、檔案、資料交接,完全按照新的管理模式運行。
那么,縣局由原來的當地政府部門調整為市局派出機構后,是否具備行政主體資格?能否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行政處罰等具體行政行為?
這是垂改后,實際工作中一個繞不過去的必答題。由此還涉及衍生的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如何操作等問題。
筆者認為,以現行的法律法規規章審視,市局是轄區內對生態環境違法行為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縣局作為市局的派出機構,只有經法律、法規授權方能以自己名義實施行政處罰。即除有法律授權外,縣局無權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處罰。
垂改后,縣級生態環境分局性質發生改變
看一個行政機構有沒有行政主體資格,包括能否以自己名義作出行政處罰等具體行政行為,首先要弄清這個行政機構的性質。因為對不同性質的行政機構,法律的規定是不同的。
2015年10月下旬,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指出:“市(地)級環保局實行以省級環保廳(局)為主的雙重管理體制,縣級環保局不再單設而是作為市(地)級環保局的派出機構。”
201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中辦發﹝2016﹞63號)規定,“調整市縣環保機構管理體制。市級環保局實行以省級環保廳(局)為主的雙重管理,仍為市級政府工作部門。”“縣級環保局調整為市級環保局的派出分局,由市級環保局直接管理。”
由此看出,垂改后,市局作為市級政府工作部門的性質沒有變化。而縣局調整為市局的派出機構(分局)后,其性質已發生變化,已不是駐在地縣級政府的工作機構,而成為駐在地縣級行政區域的工作機構。
我國現行生態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從層級上看,包括生態環境部、省(自治區、直轄市)生態環境廳(局)、設區市生態環境局、縣(市、區)生態環境分局。其中,生態環境部、省(自治區、直轄市)生態環境廳(局)是同級政府組成部門,設區市生態環境局是政府工作部門,都屬于法律規定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范疇,而垂改后的縣級分局已被排除在這個范疇之外。有些省在垂改中,雖然駐在縣級行政區域的生態環境機構名稱仍稱“局”,而不是“分局”,但其性質已然是“分局”。對此是沒有爭議的。

派出機構是否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取決于法律法規是否授權
行政主體,是指享有行政權,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國家行政職權并能獨立承擔因此產生的相應法律責任的組織。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權,即獨立的擁有并行使行政權力;二是名,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對外采取行政行為;三是責,承擔由其采取的行政活動而產生的法律責任。
派出機構一般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但也非一概而論,例外的情況就是法律法規規章有授權。
派出機構是否具有行政主體的資格,不在于其是否有派出機構的名義。不同派出機構的行政主體資格并不相同,其差別就在于現行法律法規是否對其授權。即法律、法規規定某個派出機構有一定的行政職權,可以以自己名義對外行使職權的,那么它就享有授權范圍內的行政主體資格,可以在授權范圍內以自己的名義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包括行政處罰)、參加復議或者訴訟,并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在沒有法律法規授權的情況下,派出機構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包括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行政處罰權。超越授權范圍的行政行為,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作出,需要以委派其的行政機構的名義作出。
現試舉幾例,分別看一看現有不同派出機構的行政主體資格情況。
公安部門:《公安機關組織管理條例》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在本級人民政府領導下,負責本行政區域的公安工作,是本行政區域公安工作的領導、指揮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治安管理處罰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決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罰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決定。”據此,市轄區公安分局既是上級公安機關的派出機構,同時又是本級政府的工作部門,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處罰。我們生活中接觸最多的公安機關是派出所,其擁有的“警告、500元以下的罰款”行政處罰權,同樣來自于法律的授權。關于鐵路、交通、民航、森林公安機關和海關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的治安管理處罰權問題,公安部印發的《公安機關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解釋》的通知(公通字〔2006〕12號)規定:“根據有關法律,鐵路、交通、民航、森林公安機關依法負責其管轄范圍內的治安管理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第6條賦予了海關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對阻礙海關緝私警察依法執行職務的治安案件的查處權。為有效維護社會治安,縣級以上鐵路、交通、民航、森林公安機關對其管轄的治安案件,可以依法作出治安管理處罰決定,鐵路、交通、民航、森林公安派出所可以作出警告、500元以下罰款的治安管理處罰決定;海關系統相當于縣級以上公安機關的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可以依法查處阻礙緝私警察依法執行職務的治安案件,并依法作出治安管理處罰決定。”
自然資源部門:《國務院關于做好省級以下國土資源管理體制改革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發〔2004〕12號)規定: 市(州、盟)、縣(市、旗)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垂直管理后,仍“是同級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門”;“市轄區國土資源主管部門的機構編制上收到市人民政府管理,改為國土資源管理分局,為市國土資源主管部門的派出機構。”據此規定,縣(市)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垂直管理后仍然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處罰。而市轄區的國土資源部門則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不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處罰。
稅務部門的派出機構(稅務所):法律對輕微處罰也進行了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本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罰款額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稅務所決定。”
市場監督管理:1995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關于大中城市工商行政管理體制調整后工商行政管理分局執法權限問題的請示》,作出的《關于大中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分局執法權限問題的復函》(國辦函〔1995〕59號)規定,“區(縣)工商行政管理局改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分局后,不改變其依照有關法律、法規享有的行政管理職權,可以其名義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可見,按國家行政區劃設立的工商分局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工商行政管理所條例》第八條規定:“工商所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區、縣工商局的具體行政行為,但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工商所可以以自己的名義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一)對個體工商戶違法行為的處罰;(二)對集市貿易中違法行為的處罰;(三)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工商所以自己的名義作出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
可見,以上這些垂直管理的派出機構中哪些機構、哪些處罰項目可以以自己的名義作出,法律授權非常清晰。
縣局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處罰,缺乏法律依據
現行《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中,在規定涉及環保部門(生態環境部門)的行政主體時,使用的稱謂只有兩種:“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污染防治、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最新的一部法律,這部法律共有23個法條29處在規定行政主體時,使用的稱謂全是“地方人民政府生態環境主管部門”。
從以上六部法律在規定可能包含縣一級行政主體時的表述可以得出,垂管后,縣(市、區)生態環境分局不是政府部門,因此也就不再享有上述法律規定的行政處罰權。
有的現行相關法律法規規章疑似授權,但并未明確授權。
現行的《環境影響評價法》《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環境行政處罰辦法》三部法律法規規章明確行政主體時,在稱謂上比上述六部法律的表述少了“人民政府”四個字。似乎,縣局在上述三部法律法規規章中得到了相應授權,可以依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規定的有關違法行為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行政命令、行政處罰。但仔細分析,并非如此。

其一,縣局是市局的派出工作機構,是市局的一個部分,不屬于“縣級以上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縣級以上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 “縣級以上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范疇。
其二,現行《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系由環境保護部于2009年12月30日由部務會通過,于2010年3月1日起施行的。而省以下環保垂改是2015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部署的,環保部的部門規章不可能穿越時空為幾年后才出現的縣局授權。因此,《環境行政處罰辦法》中的“縣級以上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應視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縮略語,屬于文字表述的不規范情形。
綜上分析,在現有法律框架下,設區市所屬的縣局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處罰。
實踐與建議
探索試行用市局編號印章制作相關執法文書。
縣局作為環境管理的第一線機構,日常執法監管是其主業,大量的執法文書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制作,而要報由市局,以市局的名義制作和行使職權,確實不方便,提高了執法成本、降低了執法效率。但若是在沒有現行法律授權的情況下,縣局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處罰,則屬于違法行政,行政相對人若提起復議,復議機關通常都會予以撤銷。若行政機關予以維持,而行政相對人提起訴訟,復議機關將和縣局一道成為被告,縣局和復議機關必然敗訴,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無疑要被撤銷。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一碼歸一碼。法律判斷與情理判斷,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由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不能以縣局以市局名義實施行政處罰不方便、成本高、效率低為由,而“霸王硬上弓”,讓縣局違背現行法律實施行政處罰。
為解決這一問題,一些設區市生態環境局探索為委派的一個個縣局對應刻制本級名義的編號印章,市局名義的編號印章由相應的縣級分局保管使用。用編號印章的形式可以看作是行政機關對行政處罰權的委托,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不失為一個權宜之計,在修改現行法律對縣局行政主體資格授權之前,似可以推而廣之。
《行政處罰法》第十八條規定:“行政機關依照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規定,可以在其法定權限內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條件的組織實施行政處罰。行政機關不得委托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實施行政處罰。委托行政機關對受委托的組織實施行政處罰的行為應當負責監督,并對該行為的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受委托組織在委托范圍內,以委托行政機關名義實施行政處罰;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實施行政處罰。”第十九條規定:“受委托組織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務的事業組織;(二)具有熟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業務的工作人員;(三)對違法行為需要進行技術檢查或者技術鑒定的,應當有條件組織進行相應的技術檢查或者技術鑒定。”必須注意到,縣局用市局名義的編號章實施行政處罰,市局承擔對此印章使用產生的法律責任。因此,市局絕不能“大撒把”,必須加強對縣局執法、處罰過程和法律適應的強力監管。
加快推進現行法律法規的修改進程。
2018年2月28日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提出“推進機構編制法定化”,并明確指出“機構編制法定化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要保障。要依法管理各類組織機構,加快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五個法定化”是中央針對現實中包括派出機構在內的各種黨和國家機構設置過程中缺乏嚴謹的法律論證、未嚴格履行法定程序、機構職能權限設定存在不合法、不合理等現象提出的改革總體方向。
2018年12月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綜合行政執法改革的指導意見》(中辦發〔2018〕64號),部署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明確提出“減少執法層級,推動執法力量下沉,提高監管執法效能。”“除直轄市外,縣(市、區、旗)執法隊伍在整合相關部門人員后,隨同級生態環境部門并上收到設區的市,由設區的市生態環境局統一管理、統一指揮。縣級生態環境分局一般實行‘局隊合一’體制,地方可根據實際情況探索具體落實形式,壓實縣級生態環境分局履行行政執法職責和加強執法隊伍建設的責任,改變重審批輕監管的行政管理方式,把更多行政資源從事前審批轉到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上來。實行‘局隊合一’后,縣級生態環境部門要強化行政執法職能,將人員編制向執法崗位傾斜,同時通過完善內部執法流程,解決一線執法效率問題。”
現行涉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大多是本輪生態環境機構改革之前制定的,從現實看,改革后的生態環境機構(不僅僅是縣級生態環境分局)確實與之有某些不相適應之處。可以預見,下一步,現行涉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將適應生態環境機構改革的推進,作出修改。對縣級生態環境分局行政主體資格是否予以授權、是全面授權(與改革之前一樣)還是部分授權,建議修法時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和縝密的論證,以保證修改后的法律接地氣、好執行。
借鑒其他垂直管理機構法律授權的經驗。筆者認為,借鑒公安、稅務、工商機構授權經驗,對縣級生態環境分局進行部分授權比較適宜,輕微行政處罰、部分行政命令(如100萬元以下的罰款、非民生領域企業的限產停產整改等)建議授權縣級生態環境分局以自己的名義作出,重大行政處罰、重大行政命令應由委派機關(市局)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