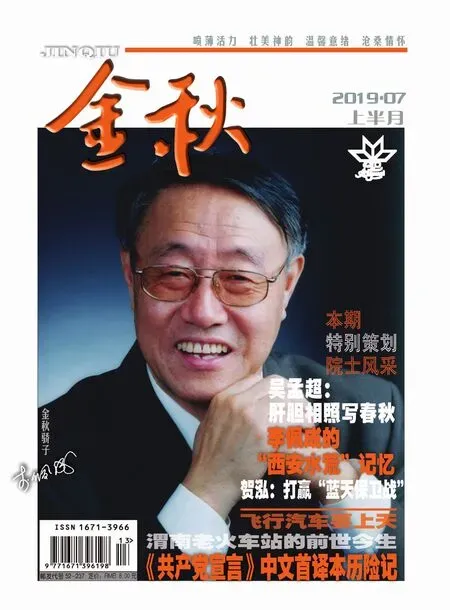兒女的人生航燈
文/王曉莉
我們的父親王建才1936年農歷七月七日出生。他在16歲時喪父,便幫著奶奶和太爺爺勇敢地挑起了撫養小叔小姑的重擔。父親17歲在農械廠當學徒,用微薄的工資供養小叔小姑們上學并贍養生病的奶奶和年邁的太爺爺。小姑15歲時渾身的淋巴結腫大經常高燒不退,多次治療不見好轉,最后醫院放棄治療,讓家人把小姑領回家順其自然。看到奶奶總是偷偷地掉淚,父親便千方百計到處找醫生、尋偏方,硬是從死神手里把小姑拉了回來。

父親和母親戴榮琴結婚后,就多了一個贍養、照顧奶奶和太爺爺以及小叔小姑的得力幫手。記得我們年幼時,奶奶肺氣腫經常發作且行動困難,需要經常住院治療,當父親上班不在家時,都是母親用她矮小的身軀背起奶奶上下樓去看病。她自己也是個嚴重的心臟病患者,但她常常不顧自己的病痛,像親生女兒一樣照顧著奶奶的晚年。在父母親無微不至的孝敬照顧下,奶奶和太爺爺都得以高壽而安詳地離開人世;小叔小姑們也都得到了父母親真誠的關愛與幫扶。
父母親在對親人關愛的同時,對家鄉父老也相當關注。記得很多年前,父親的老家煙王村一村人的吃水都是用村北頭的老水井,打上來的水很渾濁,于是父親帶著村里的鄉親到處爭取財政支持,終于打下了村里的第一孔機井。機井給莊稼和鄉親們帶來了方便,也給一村人帶來了祥和。老家村里的鄉親父老,不管是來西安看病還是有事相求,父母親都會熱情相迎、真誠款待。無論風雨時還是黑夜里,隨時走進父母親在西安的家門,老家村里的鄉親都能吃到一碗熱乎乎的酸湯面。我們記得最清的是村里的六大,患有嚴重腎病在西安治療,父親幫著聯系醫院找大夫,母親天天做好營養豐富的飯菜送到醫院,為了照顧好六大六媽,年幼的我們都多次到醫院送過飯。
父母一生養育了5個兒女,這5個兒女都是他倆攥在手心里的寶貝。記得1976年大地震,西安也余震不斷非常危險,母親把5個孩子轉移到廠里的防空洞,她自己則全然不顧危險天天回到樓房的家里做好一大鍋香噴噴的飯菜,然后一步步端到防空洞里,看到兒女們吃的有滋有味,她總是一臉的幸福和滿足。1995年4月,在母親離開我們前的最后一個月,她的冠心病已經非常嚴重,但她卻隱瞞病情,當時正好遇到她的兒媳生孩子,她便把醫生開的住院證偷偷地藏了起來,一邊照顧坐月子的兒媳和剛出生的小孫女,一邊照顧一家人的生活,每天乘著公交車往返于五路口和北郊。記得她走的那天,從早上6點到半夜12點,整整一天,她就像個上了發條的陀螺,沒有片刻的停歇,最后終于累倒在床上,再也沒有醒過來。母親太累了,剛剛60歲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子欲孝而親不待,這種遺憾真讓人撕心裂肺啊……母親走后,父親加倍地關愛我們,每到假期周末,他和我們相聚在一起,感受大家庭濃濃的親情,享受幸福的生活。在他臨走前的最后一個下午,他還打電話牽掛著兒女的健康,在他心里兒女永遠是他的小樹苗,離不開他的保護和澆灌。

父親的后半生傾力奉獻給了老齡事業,像頭老黃牛那樣任勞任怨,在每一個工作崗位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尤其是在省老齡委工作的11年,得到了省上領導和同事們的高度認可。他走后,他單位的領導傷心地對我說:“沒有你爸的貢獻就沒有今天的老齡委和老年大學,你爸爸是我省老齡工作和老年大學的奠基人之一”。父親生前常對我說,老年事業是一個積福行善的事業,不但要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獻在老齡工作中,而且希望將這個接力棒傳遞到兒女的手中。他認為要傾盡全力關心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的老干部,以親情化的服務讓老干部安度晚年。
父親一生孝順父母、關愛親友、樂觀豁達,一直保持著一種積極向上的心態和良善處世為人的素質。從西安到咸陽老家煙王村,有60多公里的路途,他在70歲、75歲和80歲時3次騎著自行車往返于家鄉和西安。在他81歲離世前的最后一個下午,他還拖著已經疲憊不堪的身軀給奶奶和太爺爺上了最后一次墳,燒了最后一次紙錢,盡了最后一次孝。
雙親慈孝樹典范,仁愛持世惠子孫。載酒公過風亦醉,澆花人去水猶香。父母親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們如同航燈,永遠照亮著兒女們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