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劉 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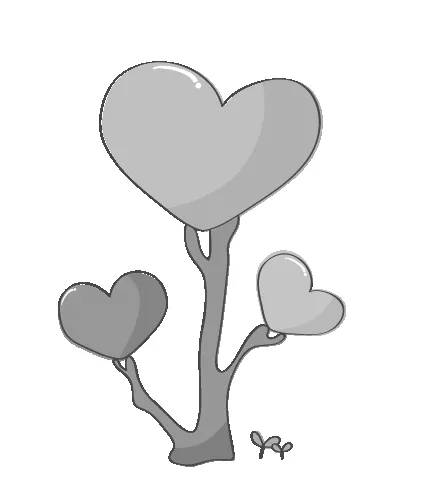

我是站在醫(yī)院的走廊里,把這篇《潛伏在女兒朋友圈里的時光》發(fā)給木木的,大約過了半小時,微信彈出木木的消息,她驚訝又欣喜地說:“這篇文章是你媽媽寫的嗎?”“《親愛的多云小姐,我愛你》那篇是你之前發(fā)在雜志上的那篇嗎?”“厲害厲害,驚到我了。”
那是一個月夜,媽媽剛剛寫完這篇文章時,興致勃勃地要讀給我們聽。她雙手捧著稿子,神采飛揚地站在電視機前,像戲劇里的花旦,唱念做打,好不熱鬧。我的頭枕在爸爸肉肉的肚子上,我們吵吵鬧鬧,故意不配合,把媽媽“氣”得不行,轉眼間,笑聲就溢滿了整間屋子。
通過文字讓更多人聽到她的心聲,是媽媽一直以來的心愿。她年輕時是一個文青,在校刊上發(fā)表過不少古體詩,可早年的困苦生活,讓她畢業(yè)后不得不一頭鉆進金融行業(yè)。所以后來無論我就讀中文專業(yè)還是熬夜寫稿,媽媽都全力支持著我。
隨著我收到的樣刊越來越多,媽媽心底的文學夢也漸漸蘇醒。她熬了半個多月,像個兢兢業(yè)業(yè)的鐵匠,小心翼翼地燒料、鍛打、定型、淬火,終于完成了初稿,于是便有了上一幕的故事。
可就在接到稿件錄用通知前一個星期,爸爸查出了惡性甲狀腺乳頭狀癌,腫瘤隨時都可能發(fā)生轉移。媽媽每天都忙著排隊繳費、取檢查報告、來回喊護士、蹲在地上搓洗爸爸換下的衣服……不過短短幾天,她臉上的皺紋深了許多,多天沒有洗的頭發(fā),亂糟糟地堆在頭上,像秋日下的稻草。
為了爸爸能夠得到更好的救治,媽媽連夜買票帶我們到上海。爸爸需要立刻做手術,可是每一家醫(yī)院看病的人都很多很多,醫(yī)生給我們的答復都是等待,可是哪里等得起呢?多一秒都是奢侈的。我們在一周內連續(xù)換了三家醫(yī)院,卻依然沒有著落。
除去在醫(yī)院的時間,我們都擠在醫(yī)院門口又臟又亂的小賓館內。和爸爸在一起時,媽媽堅強得厲害,她的黑眼圈像兩把大鐵鎖重重地墜在雙眼下方,把眼底的心事鎖得死死的,讓人讀不出一絲情緒。可一當爸爸遠離她的視線,她立刻就蹲在地上,一次又一次哭到崩潰。
深夜,我透過廁所那扇小小的排氣扇,瞥見遠處連綿不絕的暗黃街燈像一把大火,把夜晚燒成了灰燼。上海很大很大,而我們只是這浩瀚海洋中,一座無人問津的孤島。
第十天,依然沒有等來一點消息。晚飯后,我們走了很長很長的路。我是一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尤其是面對陌生的大城市。可是父母的存在,給了我昂首闊步的勇氣。因為我知道,此刻的我,必須扮演一個大人的角色,自信地帶他們穿過一個又一個擁擠的地鐵口、疾馳的馬路和沒有街燈的深巷子。
眼前這個曾經重達170斤的男人,如今孱弱得像一棵枯萎的梅樹。過馬路時,爸爸習慣性地握緊我和媽媽的手,我們就這樣,穿過一個又一個車水馬龍的路口,無比踏實的幸福充滿心間。
多年來,我一直不顧一切地往前沖,去外地讀大學、讀研、計劃留學,我是遠航的船只,只有一眼望不到頭的海水和怎么也靠不了岸的碼頭,卻從未回頭看看,身后那焦急的目光。可今晚,我突然意識到,愛他們,是我做過最有意義的事。
父親,無花果,只有在墜落地面的瞬間,甘甜才會涌滿身體,如同我們持續(xù)病痛與苦難的一生。秋天要走了,時日無多。我必須在冬天來臨前,讓一切悲傷都塵埃落定。決不能讓它們被冰雪凍住,融化在第二年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