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的眼淚
李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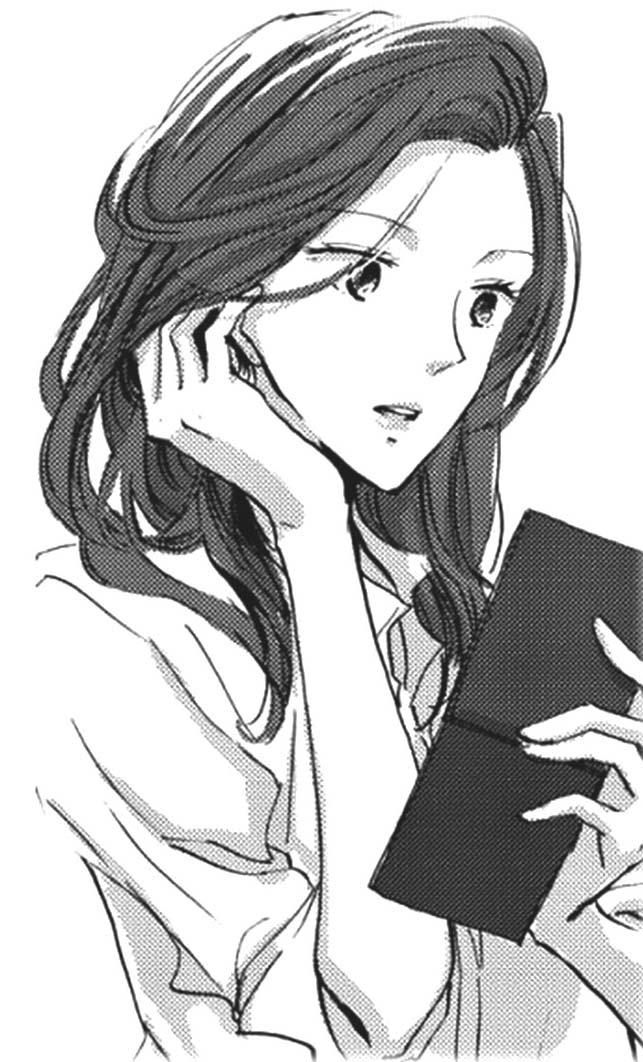
1.再見
初冬,尋常的大霧天氣。窗邊相對而坐著兩個人,他們都撐著,堅持著,誰也不先示弱,誰也不先交出底牌,似乎這個時候誰讓出一步,就是輸了全盤。
6年,足以讓兩個曾經耳鬢廝磨的戀人變得謹慎而客氣。
“杜小曼。”他提名帶姓地說,“真的不回你的澳大利亞了?多好的地方啊。”
“再好,也是別人的,老頭死了,我一個人怎么呆得下去。”她往咖啡里放一塊糖,優雅攪動。
“喜新厭舊,還是老毛病。”他輕笑。
她低頭不語,心中五味雜陳。她恨他的虛偽,他是男人,為什么不能直接點,單刀直入地問她還愛不愛他,還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可是她不是也假裝著超脫,只字不問他的情感狀況嗎?
她再也不可能像6年前那樣,使勁地揪住他的耳朵大叫:“方夕,快點說你愛我,快說!”
她早已沒有那樣的資格。
那年,18歲的杜小曼從農村來到這個城市,在一家報社做前臺接待員,方夕是這家報社的保安,平時總在杜小曼身前身后晃。有時候他故意向她借一支筆,弄斷了,再做出很愧疚的樣子說:“實在不好意思,不小心弄壞了,我又不知道哪里有賣的,算了,請你吃飯吧。”
杜小曼其實早就對他有心,于是晚上下班后就樂呵呵地跟著方夕去吃路邊攤。
從春天到秋天,路邊攤吃了十幾回,露天電影看了幾十場,廣場溜達了一百次,方夕終于在長久的醞釀之后拉起杜小曼的手,把一條漂亮的手鏈纏在她的腕上。
他們終于確定了男女朋友關系。
6年后再見時,杜小曼腳蹬一雙及膝米色長靴,方夕看著,不由心生感慨。這雙長靴,怎么也得幾千塊吧,可是當初他們為了一雙廉價短靴,費了多少波折。
那時候,他們去夜市閑逛,杜小曼看上一雙白色短靴,三十塊。
“太貴了,你說呢?”她拉拉方夕的衣角說。
“二十塊吧。”方夕砍價。
“不行。”攤主斬釘截鐵。
“那算了。”杜小曼拉著方夕戀戀不舍地走了。走了,她心里卻放不下,一再地提起那雙鞋,一會兒說,“三十塊,真貴啊。”一會兒又說,“不過真的很好看。”
方夕心里明白,就讓杜小曼等著,他跑回去買,結果價錢就漲了,他狠狠心,花三十五元的高價把那雙鞋買了下來。拿回去給杜小曼,她又氣又喜,當寶貝一樣抱在懷里。
那晚,他們一時高興,錯過了最后一班公車。因為已經浪費了錢,就更加舍不得打車,于是走路回去,走了整整兩個小時,卻不倦不累。
那年的平安夜,他們在郊區的玫瑰園里拉回五百枝玫瑰,站在人流如潮的廣場上賣。
杜小曼戴著圣誕帽,手里拿了幾根閃亮的魔棒,美得像下凡的仙女。方夕嗚里哇啦地吆喝,她便不停地把花拿給那些青年男女,一邊遞過去,一邊說些祝福的話:“祝你們幸福,美滿,甜蜜。”
很多女孩子看到她后,情不自禁地贊嘆:“你好漂亮!”
又看方夕一眼:“哇,多般配的一對!”
花賣得好極了,杜小曼興奮得滿臉通紅,她暗暗算著,這一晚上,大概會有一千多塊的收入。
他們把花全部賣完,沒有舍得給自己留一枝,匆忙趕回杜小曼的單身宿舍,把收來的零錢倒在床上,一張一張地數:“哈哈,居然賺了兩千塊!”
杜小曼高興得抱住方夕親了十幾下,當然,方夕回敬了她幾十下。
從此,他們愛得更加徹底。
2.父母反對
那年春節后,他們租一間平房,住在了一起。
那是很簡陋的一個房子,小小的兩間,沒什么家具。可是杜小曼卻很滿足。每天下了班,她可以跟方夕一起回到他們共同的家。和相愛的人長相廝守,還有比這更令人愉快的嗎?
杜小曼用花花綠綠的棉布把床邊圍起來,又在墻上貼滿漂亮海報,再弄張玻璃小圓桌,房間就溫馨得像個家了。方夕對杜小曼的布置十分滿意,一個勁地說:“好老婆啊好老婆。”
可是,方夕的媽卻并不這樣認為。方夕和杜小曼同居4個月后,杜小曼終于被帶去見公婆。
本來以為不會有任何問題,沒想到,婆婆堅決地打擊了他們。當她得知杜小曼家在農村,自幼沒有雙親時,臉上便有越來越濃的烏云。
她偷偷把兒子拉到小臥室,嚴正聲明:“不行不行,這姑娘家里太窮不說,又從小沒人管,肯定是個野孩子,娶她我可不踏實。”
杜小曼在門口,聽得清清楚楚。她愣了,驚得忘了躲藏。
方夕媽媽抬頭,一眼看到她,臉上烏云更濃:“你聽到了更好,這就是我的態度,你還是識相點,走吧。”
對于任何一對熱戀的情侶來說,家人的堅決反對都是巨大的陰影。方夕臉上的陽光被遮住了,杜小曼心里的溫暖被遮住了。
雖然還是以往那樣的生活,卻平添了暗暗的心事。
“別擔心,”方夕安慰杜小曼,“我會說服我媽的,她那么疼我,一定不會為難我們。”
可是,在方夕說這話的第二天,他媽媽就來戳穿他的承諾了。
方夕媽媽從老家趕來,霸道地坐在杜小曼精心布置的小屋里,對杜小曼道:“都跟我兒子住在一起了,你也太不檢點了吧,果然不是好人家的閨女。我不是說了我不同意嘛,還賴在我兒子這里干什么,快走吧走吧……”
方夕使勁地拉媽媽,卻阻止不了她氣勢洶洶的咒罵。
當晚,杜小曼收拾東西回了以前的宿舍。因為沒有爹娘,她自幼受了多少屈辱,沒想到,如今還要從頭來過。
方夕給了她一個虧欠的眼神,沒有敢當著兇惡的媽媽對她說一句話。杜小曼知道,方夕其實是很懼怕自己的母親的。
忍著不哭忍著不哭,眼睛還是紅紅的,像熟透的櫻桃。
她一個人躺在久未回去的宿舍,忽覺人生蒼涼。那一夜,噩夢連連。
3.抑郁
第二天,杜小曼腫著一雙眼睛等方夕上班。可是左等右盼,方夕一整天都沒有出現。
臨下班時,主管叫她去。杜小曼想,一定是自己上班狀態不好,得罪了領導,去時,心里滿是絕望。
沒想到,主管的態度倒是一反往常,她客氣地讓杜小曼坐在自己旁邊,神秘地說“:我們剛剛病退的一位老領導劉總,不知道你認不認識,62歲了,想去澳大利亞休養,老伴剛過世,他希望能找個人在身邊伺候著,人家對你有印象,點名要問問你愿不愿意。”
杜小曼傻傻地看著主管:“去澳大利亞做保姆嗎?待遇怎么樣?”
主管微笑:“也不只是做保姆,劉總孤身一人,想與你一起生活。當然,名譽上可以是保姆,不過……劉總家資無數,你如果陪他安度這幾年,以后也是享不完的富貴……”
杜小曼明白了,這就是給人當小老婆啊,她本能地要反對,張開嘴,卻把拒絕的話咽了回去。
“我得想想。”她說。
那天,方夕剛來上班,就見杜小曼被一個男人接走了。方夕在同事們模糊不清的評論里,漸漸明白了真相。
他血沖上腦,拔腿向外追去。那奔馳已經緩緩開出大門,方夕在后面瘋狂追趕,卻是越追越遠。
杜小曼坐在車里,看著方夕狂奔而來,口中還不停呼喊著。他在喊什么,她完全聽不到,但她知道,在他那樣撕心裂肺的呼喊里,他們的愛情,已經轉身走了。
她的眼淚嘩啦啦地洶涌而出,他的身形漸漸模糊在車窗外面的世界里。
一個月以后,杜小曼降落在地球的另一端。
澳大利亞的生活,仿佛是另外一個世界。世外桃源般的別墅里,杜小曼搖身一變,成了女主人。老劉病入膏肓,卻對她寵愛有加。白天需牽手散步,晚上要共枕而眠。
他教她簡單的英文,告訴她那些時尚品牌,改變她衣著的品位,提醒她用昂貴的化妝品。
不到一年的時間,杜小曼就成了另一番模樣。
她常常對著鏡子里貴婦人一樣的自己發呆。這樣的生活,曾經是她的夢想,唯一不符合理想的,就是枕邊人不是方夕。
可是,這太重要了。她想,如果讓她在方夕和榮華富貴之間選擇,她會選擇她的方夕,一定會。可是,方夕在她和媽媽之間,會選擇她嗎?即便選擇了她,他們會幸福嗎?
杜小曼每天被這些問題折磨,越想越迷茫,越迷茫越忍不住去想。
杜小曼開始抑郁,越來越嚴重,她漸漸厭惡老劉,拒絕與他相處,不為他做任何事。
在幾次劇烈爭吵之后,老劉請來當地知名的華人心理醫生,為她治療。
杜小曼開始吃藥,一把一把地吞下那些昂貴的抗抑郁藥物,卻仍不見好轉。醫生知道她是心病,私底下告訴她:“這樣下去,你可能毀了自己,重度抑郁癥患者的出路,極大可能是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在國內有什么心愿未了,不如好好與老劉聊一次,讓他放你一條生路。”
4.回來
杜小曼回來了,老劉寬容了她的毀約。幾經輾轉,杜小曼終于打聽到方夕的下落——他在一家婚禮公司做司儀,因言語幽默,反應靈敏,外形帥氣,在當地已是小有名氣。
杜小曼去公司找他,卻得知他正在主持婚禮,杜小曼去參加了那場陌生的婚禮。于是,幾年以后,杜小曼終于又見到了方夕。
他還是那么俊朗,眼睛里閃動著光彩。他喜氣洋洋地站在大紅喜布前,爽朗地說著喜慶的祝福話,講著幽默的小段子。嘉賓們被他逗得前仰后合,捧腹不止。
杜小曼難以相信。幾年后,方夕已經從當年那個窘迫的保安,蛻變成出色的婚禮司儀。如今,他們都不再是當年貧賤的兩個人。可是,那些不貧賤的感情,還在不在呢?
一直到杜小曼站到方夕面前,他才定睛看她,才終于認出她來。
他們在咖啡店里坐了很久,也僵持了很久。終于,方夕接了通電話,一個年輕女人的聲音從話筒里泄露出來,她問他晚上回不回去吃飯。
“不了,你自己吃吧。”他說。沒有稱呼,沒有寒暄,可見是多么熟悉的關系。
杜小曼終于明白方夕與她保持距離的原因,她試探著問:“剛才那個……”
“我媽的保姆。她身體不好,需要24小時陪護。”
“你,有沒有女朋友?”她心中喜悅。
他輕輕搖頭:“沒有。”
“那么,是不是,厭舊了?”她試探著問。
他半晌沒有說話。
“確切地說,是恨舊。”方夕的眼睛忽然開始泛紅,“當年你就那么走了,你可知道我的心情?在一起那么久,我都不知道你是那樣無情的人。當我眼睜睜看著你坐著老頭子的車漸漸遠去的時候,我想我一輩子不會原諒你。”
她的眼淚傾瀉而出。他終于握住她的手:“小曼,我曾經發誓不原諒你,可是,當你坐在我面前,我才知道拒絕你是多么艱難。
“小曼,我早已知道你要回來。老頭子沒有死。他讓你的心理醫生聯絡我,告訴我你的一切,希望我好好待你。
“小曼,我其實想好了要冷淡你,要讓你嘗到我當年的苦,可是,我沒有做到。”
他聲音哽咽,說不下去,而她已經在對面,哭出聲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