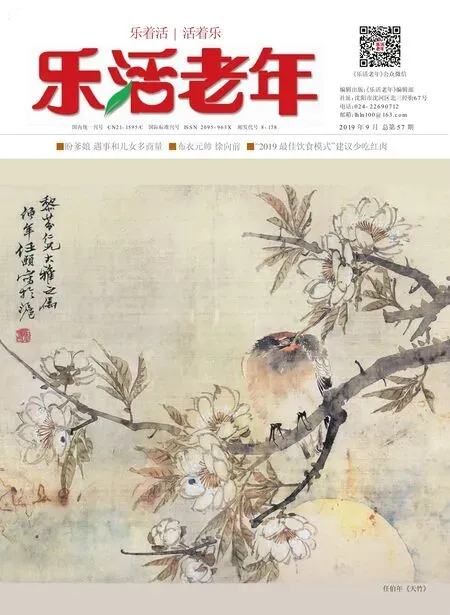培養我們的意象
文/胡中惠

客居蓉城,謁杜甫草堂,訪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處,突然覺得,這里就應當是花間詞誕生的地方,就應當是楹聯肇始的地方。鳥鳴山幽,水綠風和,杜甫的詩句,陸游的詞句,斷斷續續從心底奔涌出來。他們的人,他們的詩,與這里是那樣地契合,盡管一個是河南人,一個是江浙人。由此我又想,我們東北人學習傳統詩詞,只在鑒賞層面流連怎么都行,但寫作起來,確乎有許多“隔”的地方。我們所接觸的教材中的意象,不是中原就是江南甚至大部都是江南的,屬于我們的意象在哪里?幾乎沒有。沈延毅先生生前十分喜歡元好問,當時我在心中即驟起疑團:沈老可謂腹笥豐贍之人,唐宋那么些大家皆可學,為什么卻獨鐘元好問呢?來四川小住我明白了,這正是沈延毅先生的超拔之處。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被尊為“北方文雄”,他的作品中不獨中原的意象,更有一些我們東北的東西涵泳其中。沈老向他學習,可謂獨具慧眼。
沒有理由懷疑古人詩詞中意象的采擷,人家本來就是中原人或南方人,熟悉的景物得心應手,不寫這些寫什么?還有,江南佳麗地風物確實美,也確實出詩,人家的“春江花月夜”,人家的“杏花春雨”,人家的“一江春水”,我們真沒有。今天我們學習傳統詩詞寫作,以古為徒是不二選擇,不學習李白難道還要學習李逵?不學習陸游難道還要學習陸賈?可是,如此這般大咧咧地學下去寫下去,永遠要拾人牙慧,永遠要走在人家的后面,因為在意象的表現上沒有或者說少有自己的東西。人家溫婉我們也溫婉,結果是不太溫婉,因為人家是生來的溫婉,我們是改裝的溫婉。
太像別人就沒有了自己。一些祖籍在東北,出生在東北或者生活在東北的先賢已經意識到這些并做了不少的嘗試,遠的如納蘭性德、僧函可,近的如作家蕭軍、書法家沈延毅等。他們的這些探索可能是下意識的,零散而凋敝,能夠流傳的作品不是很多。當下詩壇也有人認識到這一點,惜乎沒有形成規模。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向畫界學習。很多畫家很早就打出關東畫派的旗幟,據說盧志學先生的白樺林還走進了人民大會堂。因為他們知道,偌多的風花雪月固然好,但不完全屬于我們,只有努力尋找屬于自己的意象,才能創作出與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來。白山黑水自粗豪,瑞雪青松也多嬌。這里的山,這里的水,這里的人,多寫寫沒有什么不好,也許人家最喜歡讀我們的作品就是這些。
順便說一點,“意象”一詞于新詩寫作不陌生,于傳統詩詞寫作好像出鏡率不高。將百度詞條摘錄如下,以備參考。“意象”一詞是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古人以為意是內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體的物象;意源于內心并借助于象來表達,象其實是意的寄托物。中國傳統詩論實指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藝術處理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