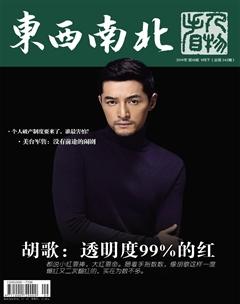文在寅困局:一個“高人氣總統”怎樣走向內外交困
王昱

面對來自日本愈演愈烈的經濟制裁,近期,日本和韓國先后將對方從本國的貿易“白色清單”中移出。8月12日,韓國總統文在寅表示,在應對日本的相關貿易限制舉措方面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靜地思考對策,做好長期打算。
當天在總統府青瓦臺召開的幕僚會議上,文在寅表示,很快就是紀念1945年8月15日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光復節了,在這個時候,韓國更應毅然決然地應對日方的貿易限制措施。他同時強調,在應對方面不能感情用事。
文在寅說:“過去我們曾飽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如今又面臨日本的經濟報復。經濟報復措施本身就不正當,采取該措施的原因還涉及歷史問題,這就更不應當了。這就是為什么在光復節來臨之際,我們要更加堅決。不過,面對日本的經濟報復我們不能感情用事,我們要堅決,還要保持冷靜,思考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對策。”
文在寅說,如果韓日兩國人民能基于成熟的公民意識,以熱愛民主人權、和平的態度進行溝通,增進友誼,韓日關系的未來將更加光明。
雖然說,日韓兩國的貿易戰到頭來對兩國來說都是有傷害的,但很明顯,韓國總統文在寅所面對的壓力要比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大得多,現在韓國還遭到了美國的“落井下石”。一方面是國內經濟持續低迷,一方面是日本的“絕不退讓”。面臨內憂外患,韓國的形勢大變,我們不禁要問,曾經在韓國民意頗為高漲的總統文在寅,如今面臨的困局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他還能“撐多久”?
激進派封死了退路
7月1日,日本產經省宣布,對日本向韓國出口的三類產品實施出口許可管理。這三類產品都是生產半導體的必需材料,而半導體又是韓國第一大產業。不難想象,此舉給韓國帶來多大的震撼效果。時間進入8月,日本又繼續宣布,將韓國從貿易“白名單國家”中剔除出來。這個白名單囊括世界上主要的發達國家,亞洲只有韓國一個。日本將韓國“拉黑”,表明他們已不把韓國視為“自己人”,將來在雙邊貿易中會增加審批流程,日韓貿易將雪上加霜。
雖然面對日本接二連三的制裁,韓國文在寅政府擺出了“絕不退讓”的態度,但此情此景,還是不免讓很多密切關注東亞局勢的人想起了其前任樸槿惠當年的窘境。
2013年,樸槿惠走馬上任,由于其父樸正熙被韓國左翼定為在日據時代賣國求榮的“韓奸”,所以樸槿惠在上臺初期對待日本的態度相當冷淡。在歷史問題上,樸槿惠也數次親自探望日據時代的韓籍慰安婦,甚至主導慰安婦檔案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一時間,樸槿惠似乎將以韓國歷史上最“反日”的總統名留史冊。
然而,到2015年底,樸槿惠政府的對日政策卻突然180度大轉向。在綜合考慮日韓經濟彼此之間的高度依賴以及美國的強力施壓后,樸槿惠最終與安倍簽訂了《日韓慰安婦協議》。協議規定,日韓兩國“永久且不可逆地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和解”。雖然在該協議中,日本就慰安婦問題進行了“歷史性的道歉”,也提供了金錢方面的補償,但韓國民意并不買賬,很多“慰安婦維權者”翻出樸槿惠競選時對他們的保證,認為自己受到了樸槿惠的欺騙。他們認定《日韓慰安婦協議》無效,不斷起訴,就連原本已逐漸平息的勞工問題也大起波瀾。樸槿惠的民意也在此后開始走下坡路。起于韓國左翼的文在寅正是在這一時期打出“徹查《日韓慰安婦協議》”等口號,依靠激進的左翼觀點急速積累了人氣,加之樸槿惠此時又鬧出“閨蜜門”,使得文在寅最終獲取了總統的寶座。
依靠左翼上位的文在寅在上臺后不出意外地將政策推向了極端:對內,他嚴厲清算前任總統樸槿惠,并對另一右翼前任總統李明博也展開了調查,試圖將韓國國內右翼保守勢力一網打盡;對外,則徹底否定了樸槿惠時代對日外交成果。

文在寅和樸槿惠探望日據時代的韓籍慰安婦
只不過,文在寅的這種做法也封死了他對日外交的后路。有日媒當時就評論稱:“即便首相(安倍)愿意與文在寅政府重談,即便能達成令文在寅滿意的協議,這份協議也不可能讓所有韓國人滿意。”而只要有更激進的左翼對新協議不滿,韓國新一輪“反賣國賊”運動就將像掀翻樸槿惠一樣把文在寅掀翻。這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長江后浪推前浪”的游戲。
推翻協議擋住了未來
行文至此,可能讀者會有疑問,日韓的歷史問題糾紛究竟為何如此難解呢?
與大多數二戰時期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不同,由于戰前《日韓合并條約》的存在,按照國際法,日本對韓國的戰爭賠償主要是日本政府對韓國個人的賠償:殖民時期,日本強征了相當多朝鮮(韓國)勞工和慰安婦,戰后的日本政府對這一罪行無法推脫,勞工補償也就成了日韓建交談判的主要議題。
其實,最好的補償方式是將賠償款支付給具有請求權的個體民眾,畢竟,此事嚴格說來是韓國受害者群體與日本政府的恩怨。日本人最開始也是這樣提的,然而,當時主政韓國的樸正熙堅持要求由韓國政府代理勞工請求權,一次性接受日方的補償。而在日方看來,這個提案確實省去了日本政府與韓國民間個體博弈的麻煩,日方也樂于接受。最終,日韓在1965年簽訂《日韓請求權協定》,日方向韓國政府無償支付3億美元,以及有償經濟援助2億美元,共計5億美元,一次性了結日韓之間所有“民事請求權”。
可別小看這5億美元。當時韓國百廢待興,全國GDP也只有31億美元,政府一年財政總預算也只有3.5億美元。日本經濟當時已經崛起,但外匯儲備也只有18億美元。可以想見,如果這筆錢真的能在當時經由韓國政府發放給受害者,應當是一筆能夠告慰受害者的賠款。
然而,熱衷于工業化的樸正熙并沒有這么做,而是將賠償款幾乎全數用于了扶持三星等韓國大企業,韓國的工業由此迎來了騰飛期,一舉奠定了經濟繁榮的基礎。至于這筆錢中又有多少被韓國當時腐敗的軍政府私分了,這是一筆無法查清的糊涂賬,我們只知道在戰爭中受害的勞工和慰安婦,成為被拋棄的人,他們幾乎沒有拿到任何政府的賠償。
于是,憤怒的韓國民眾開始提起訴訟。但有意思的是,他們不狀告本國政府,而是狀告日本政府。這種訴訟請求其實也是被逼無奈,因為面對蠻不講理的樸正熙軍政府,如果韓國民間組織敢直接將矛頭指向軍政府,勢必遭遇殘酷鎮壓,所以受害者維權群體只能以這種“曲線救國”的形式存在。
由于《日韓請求權協定》明文在前,本來這樣的訴訟在日韓兩國都會被駁回。不過,韓國軍政府為了誘導民意對外,長期對這種訴訟采取默許的態度。但這自作聰明的一手,最終還是被韓國軍政府玩脫了——上世紀80年代末,韓國戰爭受害者維權群體與韓國左翼合流,最終成為掀翻軍政府的民意浪潮中的一部分,也讓戰爭受害者與韓國左翼牢牢綁定在一起。從此,一個令人糾結的矛盾出現了:找日本政府要本國政府欠的賬,從“權宜之計”變為民粹主義的政治正確。
所以你可以想見日本人的心聲:該賠的我們都已經賠了,你們還想怎么樣?但在韓國政府連續換過幾輪之后,日本人也意識到光靠《日韓請求權協定》實在難以說服韓國。考慮到《日韓請求權協定》確實對慰安婦問題語焉不詳,安倍政府才最終與樸槿惠政府簽訂了《日韓慰安婦協議》。
今天回頭來看,《日韓慰安婦協議》體現了日韓解決歷史問題最可行的思路:雙方都心知肚明地各退一步。日本再次道歉,為當年的圖省事埋個單。而韓國政府也為自己挪用賠款的行為負個責,同日本一起出資,建立基金共同補償當年虧欠的戰爭受害者。
但受制于其支持者的政治觀點,文在寅政府上臺后,對這個還算說得過去的協議搞了個奇葩操作:韓國一方面沒有直接否認《日韓慰安婦協議》的效力;另一方面卻又解散了賠償基金,讓日本的賠償程序無法進行,導致《日韓慰安婦協議》名存實亡。不僅如此,韓國最高法院還在去年史無前例地判決民間勞工團體對日索賠勝訴,這就連作為兩國建交基礎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也一腳踢翻了。這種把既往條約當廢紙的行為,當然要惹得原本就對韓國敵意滿滿的安倍政府掀桌子不干。
“太極推手”打到了盡頭
將國內問題轉換成國際問題,既將民眾的怒氣引向了國外,又賺取了一波基于民粹主義的支持。從日韓此輪糾紛當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在寅及其所代表的韓國左翼政客的一種執政思路。這手借力打力的“文氏太極推手”一度令其在執政初期博取了高人氣,但最近一段時間卻顯現了副作用——不僅是日本人,連美國人都開始找文在寅的茬。
7月23日,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訪問韓國,原本韓方期待博爾頓此訪可以調解日韓之間的貿易爭端,但據韓媒報道,訪問期間,博爾頓突然獅子大開口,要求韓國2020年將防務分攤費增至50億美元(約合5.9萬億韓元)。而今年3月,韓美剛剛商定的韓方軍費分攤額僅為1萬億韓元。
不到半年時間,美國人要的“保護費”突然漲了近5倍。不可否認,特朗普對駐韓美軍軍費分配早有不滿是主要原因。但文在寅上臺后風起云涌的韓國左翼反美運動恐怕也讓美國人在要價時更加不愿意留情面。自今年4月份以來,韓國首爾等城市就接連爆發左翼團體主導的“驅除駐韓美軍”的游行,與文在寅同屬韓國共同民主黨的政客甚至在集會上聲稱“朝韓統一之后,駐韓美軍應立刻撤出”等言論,雖然韓國政府一再表示這類言論“不代表政府立場”。但這種消息傳到原本就對軍費問題不滿的特朗普耳中之后,其會作何感想可想而知。
也許文在寅政府這么做有其苦衷,面對特朗普漲軍費的要求,共同民主黨黨內一直有激進左翼要求政府更加強硬地予以回擊,此時默許民眾上街抗議美軍,或許既能讓民眾“出氣”,又能在談判中對美方施壓——但這樣做的結果無疑是徹底敗了與美方的交情,導致美國人在日韓糾紛這個節骨眼上不僅不愿意幫忙,反倒要來添亂。

內有左翼民意的逼迫,外有美日“盟友”的為難,眼下的文在寅進退維谷,似乎也只能依著慣性說一些迎合其擁躉的漂亮話自我麻醉。這不,8月5日,文在寅發表電視講話,表示:“現在韓國不僅要戰勝日本此番經濟打壓,還需要有更廣闊的視角和非凡的決心,去趕超日本經濟。”至于“趕超日本”的方式,則是“如果朝韓能夠通過經濟合作,實現半島經濟和平發展,我們就能很快追上日本”。
是啊,如果朝韓能夠一直和諧相處、精誠合作,攜手趕超日本也不是沒有可能,但在局勢風云變幻的朝鮮半島,有哪一個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敢把國計民生押注在這么不確定的事情上呢?等這樣的宏圖遠景實現,又要花上多少年的時間?
(鐘玉棠薦自《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