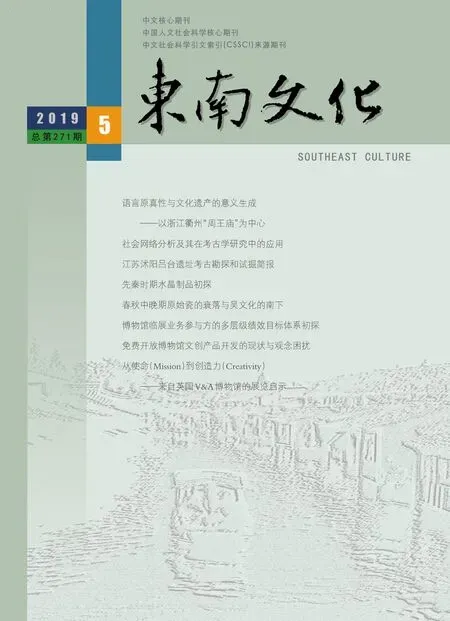社會網絡分析及其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
陸青玉 欒豐實 王 芬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
內容提要: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目前正處于繁榮期,在我國的考古學研究中具有巨大的應用潛力。它以抽象的節點和連線構成的網絡來模擬古代各種社會關系,尤其注重對物質文化交流、社會結構的時空變化等相關問題的探討,為全面解讀古代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同時,在靜態的網絡數據與動態的歷史事實之間的對接等方面,我們目前的研究還需要注意一些問題。
考古學研究的材料較為零碎,研究的目的則是借助一定的方法,將這些看似雜亂無章,實則反映著古代社會的實物材料按照一定的邏輯聯系起來,力求較完整、合理地呈現古代社會的某些片段。這其中,具有科學理論指導的串聯方法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對古代社會的研究中,現實或虛擬空間中人與人的關系、各種事物間的關聯以及它們在不同時空關系中的演變,都可以用點和線構成的網絡進行簡化或抽象地表示。這也反映了一個理念,即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但是決定整個世界形態的卻是它們之間的關聯。
國內考古學研究中,對物質關聯性的探討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通過類型學、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來分析器物、人群以及文化等各層面的聯系;二是從聚落考古角度,從聚落組成單位的界定、聚落布局和內部結構、聚落空間分布及其相互關系、聚落形態的歷史變遷研究等幾方面展開[1]。其中,除了聚落考古學中對聚落組成單位的界定外,以上兩個方面的探討均可以采用一種更直觀,更具跨區域、跨文化和歷時性比較的方法,這就是歐美考古學界較為流行的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這種方法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為闡釋古代社會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途徑,但目前此種方法在國內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還較少。本文從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的發展史、內容和方法、考古應用及存在的問題等幾個方面進行闡述,以期引起學界同仁對此方法的關注。
一、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發展簡史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簡稱SNA,被視為關系性研究,著重于探討社會參與者(社會實體或網絡節點)之間的聯系。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來源并不單一,它是不同學科相互融合的產物,受到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綜合影響[2]。其中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為網絡分析建模提供了重要支撐,利用圖形理論來直觀地描述實體間的聯系,則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對社會網絡分析的貢獻。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的發展歷程可以被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30—70年代形成并走向成熟。20世紀30年代,隨著人們對實體間聯系的代數化、圖形化和可視化的追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莫雷諾(Jacob Moreno)開創了“社會計量學”理論,并采用點和線構成的二維社會關系圖來描述抽象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3],這對社會網絡分析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隨之人類學家也開始接受這種可視化研究方法,并把它用在血緣和交換關系等問題的探討上[4]。哈佛大學的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人際關系學、六度分割理論之后,在70年代將矩陣理論應用于社會網絡分析,同時培養了一批對當代社會網絡分析具有重要影響的學生,推動了此研究的成熟化、系統化和國際化進程[5]。正如美國的弗里曼(Linton C.Freeman)所述[6],社會網絡分析的主要內涵,如重視節點之間的聯系、對分析資料的數據轉換、模型的應用等,在該時期得到了充分討論。但整體而言,該方法還處于初成階段,考古學相關的應用案例較少,在對網絡結構的闡述和解讀上還顯不足。
第二階段,即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發展期。本期出現了成熟的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和典型研究案例,其顯著特征是網絡分析和圖形理論在考古學地理空間分析中得以應用。如威廉姆斯(Irwin-Williams)將美國西南部查科(Chaco)地區的紀念碑視為網絡節點,將量化網絡空間分析技術和可視化的社會網絡結構相結合,提出節點間的人群互動可以基于人工制品的來源地進行分析[7]。島嶼考古學家通過網絡分析中的鄰近點分析技術,結合可視化網絡圖形來探討沿海地區古代社會的空間分布網絡[8]。尤其是美國佩里格林(Peter Peregrine)對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卡霍基亞(Cahokia)中心聚落演變過程的考察[9],將遺址周邊的主要水系視為一個網絡,河流交匯處和河流源頭為網絡節點,河流本身為網絡邊界,進而通過對三個中心度[10]的度量,對河流網以及節點所代表的中心聚落進行了系統的分析。這項研究不同于之前單純或主要對圖形進行主觀解釋的做法,而是將圖形理論和規范的量化分析技術相結合,為此后系統的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樹立了模板。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繁榮期。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復雜數據的分析技術得到飛躍式發展,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研究迎來了大繁榮,產生了一系列多維度的應用案例。如對古代貿易和交流路線[11]、人群流動[12]、文化邊界和文化傳播[13]、古代政治集中化和國家起源[14]等問題的研究。具體研究方法也得到完善和拓展,如以網絡中心度、網絡密度等常規分析為基礎,動態空間分析[15]、重疊網絡概念的應用[16]、凝聚子群分析[17]等新方法不斷出現,極大提升了社會網絡分析對考古學材料的多角度解讀能力。此外,隨著計算機技術和GIS技術的不斷發展與融合,以及跨區域性等宏觀課題的引領,目前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開始廣泛用于大型數據集的分析[18],從而有力拓展了人們對古代社會的認識能力。
總之,在以上三個發展階段中,第一階段以初步的圖形理論分析為主、多學科的應用使其理論框架逐漸成熟,但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有限;第二階段在初步的圖形理論分析的基礎上,融合了一系列定量化的分析方法,推動了考古學網絡分析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第三階段則在考古學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課題規模方面出現突破。因為該方法極具延伸性,在未來的考古學研究中已經表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
二、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的內容和方法
1.社會網絡分析的元素構成
社會網絡分析集中于對社會單元(社會參與者)或節點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它由一系列相互連接的節點構成,這些節點代表著特定的社會實體,它們構成了網絡分析的最小單位。節點的選擇基于分析者的研究目的和興趣,可以是某類特定器物或組合、特定意識形態的表達、單個遺址或遺址群、國家,或者是生產、流通過程的特定環節。網絡節點的類型可以是同類的,也可以包含不同類型。包含不同類節點的網絡稱為多元網絡模型,典型的多元網絡模型是隸屬型網絡,它的一類節點代表社會實體,另一類則代表實體間的組織或相應的事件[19]。
社會網絡的另一構成元素是聯系。社會網絡分析關注的是節點間的聯系而非孤立的節點,對網絡聯系的系統梳理,是深入理解網絡節點代表的社會實體真實含義的基礎[20]。網絡聯系在網絡中表現為節點之間的連線,稱為網絡連接或網絡邊界。節點間的連接所代表的含義各不相同,常見的有道路、河流、遺址中共出的器物、遺物表現出的共同風格等。連接的權重可以表示為連接的數值屬性,如共出器物所占的比例、遺址間的距離等。當然,還存在著二進制的連接權重,其中“1”和“0”分別代表兩節點間連接的有和無。此外,連接還可細分為有向和無向連接,有向連接指示著社會實體的流動方向。表現在網絡中的抽象化聯系在現實社會中無處不在,它影響人們的決定,并且通過這些聯系,信息和物品才得以傳播和發展。網絡中的聯系形成了結構化的社會環境,決定著社會群體的功能[21]。
出于對“網絡概念的直觀感受”[22],社會網絡分析通常采用節點—連接構成的可視化網絡圖來直觀地表達特定的網絡結構。以圖一這個隨機生成的網絡結構圖為例,各個圓圈分別代表一個節點,圓圈之間的連線表示網絡的連接,帶箭頭的連接為有向連接,指示著物品或信息的流動方向。網絡分析軟件根據節點和連接的權重、連接的方向性等原始數據,借助特定算法構建出初步的網絡結構,并自動計算出網絡的密度、直徑或中心度等屬性。如圖一中九個節點的標簽中,第一個數字代表節點編號;第二個數字代表節點的入度,即指向該節點的有向連接數;第三個數字代表節點的出度,即從該節點散發出的有向連接數;第四個數字代表該節點的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即與該節點相連的所有連接的總數。如果我們將此網絡視為一個區域某類產品的交流網,圖中九個節點分別代表九個不同的遺址,各個節點的大小和顏色深淺根據各自節點的度中心性而變,那么根據網絡整體結構和連接的方向性,從圖中就能很直觀地看出此類產品在這些遺址間的流通狀況。如326號遺址只是單純地為330號遺址供應此類產品;327號遺址同時為兩個遺址供應此類產品;332和335號遺址之間的產品供求關系不清楚,但兩者都從328號遺址獲得此類產品;328號遺址顯然是一個此類產品的生產中心,它同時為其他三個遺址供應此類產品;334號遺址則是此類產品的重要消費中心,吸收了來自周邊三個不同遺址供應的此類產品;333號遺址的度中心性雖然不高,但其位于兩個小網絡的中間地帶,起著連接通道的作用,關系著整個交流網的完整性,區位優勢極強。
當然,以上產品交流網如果結合GIS技術,將遺址置于實際的地理空間中,再進一步結合遺址的最優路徑、坡度、高程和緩沖區等空間分析方法,則能在更深層次上對遺址間的產品交流問題進行解讀。另外,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的屬性也不限于上文所講的中心度,有時還涉及到網絡密度、直徑等;分析的考古學問題也不限于古代產品交流,還涉及到人群的遷移、社會權力的變革等問題。因此,由節點和連接抽象出的社會關系網絡,能為我們直觀地解讀古代社會不同層面的問題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
2.社會網絡分析的一般步驟
英國的科勒(Anna Collar)等人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的一般過程[23]。首先,過去那些有趣的現象應該被識別,如個體或聚落間的經濟關系;其次,形成對這一社會現象的一個抽象概念,如商品的流動;最后,把這個抽象概念轉換成實際的網絡數據,如交換雙方形成的一對節點以及物品流通的路徑。這是所有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推理過程的三個基本環節,但在具體操作中,又可細分為七個步驟(圖二)。當然這個分析框架并非通用的,其中很多步驟需要多次重復,有的則可以省略。整個分析過程中,花費時間最多的階段在于數據收集、預處理和對分析結果的解釋。
首先是數據集的建立,這是社會網絡分析的基礎。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需要有問題導向性,在收集數據之前必須首先明確將要研究的問題。在問題引導下收集數據同樣不易,通常表現在很難判斷哪些數據對網絡分析最有用,并且很多研究會在分析過程中由于數據的局限性而走入死胡同。但有兩種策略可以引導我們找到合適的分析數據。一種是探索性驅動的策略,即分析者選擇一個預先存在的數據集,它包含一組預先定義的類別,分析者通過對這個數據集的多角度探索,找到可能產生的任何有意思的結論。如在對墓地進行社會網絡分析時,可以從墓葬空間布局、墓葬規格、隨葬品類型、不同類型隨葬品的數量、人骨高矮和健康狀況等角度來收集數據,進而通過對同期墓葬的比較來考察墓主的財富、身份和地位的差異,或通過對不同期墓葬的比較考察社會群體身份的變化,或通過對人骨的各種體質人類學屬性歸納來解讀當時不同階層人們的體質差異,或從不同屬性墓葬的空間分布特征來識別族群分化和不同族群成員的內部構成問題。雖然在進行墓地分析時,限于材料參差不齊,所得結論往往是有限的,但此方法總能在對墓主、器物和社會等因素系統把握的基礎上,還原出反映古代社會關系的某些片段。比如,是否存在著不同階層間墓地的空間分布差異、是否存在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人群之間體質和健康的差異、是否大規格陶器及墓葬面積比小型陶器及墓坑深度更能體現社會身份的尊貴性等,這顯示出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解讀考古學問題中的潛力。另一種尋找數據的策略叫假設性驅動,即對未知的世界有個先入為主的假設,并根據假設的結論來選擇所需要的數據,進而驗證結論。如為了討論魯北地區龍山文化白陶的生產和流通問題,筆者根據該區域素面鬲的空間分布特征,假定同樣存在一條東西向的白陶流通之路,進而從桐林[24]、前埠[25]、丁公[26]等遺址采集同時期的白陶標本并進行巖相學分析,最終發現龍山文化時期存在桐林和丁公兩個城址之間存在一類白陶的交流網[27]。可見這種策略引導下收集數據的方法,目的性更強,最終的分析結果無論是否支持原假設,也都同樣具有其現實意義。
數據收集完成以后,要對不同的數據進行預處理。這個過程會根據研究案例的不同而作出相應的調整,如有些時候需要去除那些數值較高或較低的部分,有時候需要對連續性、階段性數據或表示有無的數據進行編碼,如使用二進制數據“1”和“0”分別表示物品的有無,還有的則需要根據使用的分析軟件的要求對數據格式進行轉換,如把列表型數據轉換成矩陣式等。
接下來的數據導入、數據分析、可視化和結果的解釋是一脈相承的環節,且這些步驟有時需要重復操作。社會網絡分析常用的軟件包括Pajek[28]、UCINET[29]、Cytoscape[30]等,不同的軟件需要不同的數據格式、導入方式和分析方法。另外,分析的內容與研究的問題有關,并直接關系到對結果的解釋,這兩步是整個網絡分析過程的重點。如對節點度中心性的分析,即基于節點在網絡中的位置及其與其他節點的連接數來度量節點在獲取資源和傳播資源的能力,節點的度中心性反映著網絡節點所代表的遺址或其他對象在整個網絡中的重要性[31]。而鄰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則是指一個節點與網絡中其他節點的緊密程度,表示為節點與網絡中其他節點的測地線距離之和的倒數。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中,鄰近中心度較高的遺址通常也是那些比較重要或突出的遺址,因為“它們可以比其他節點經過更少的路徑去分享或獲取資源”[32]。網絡密度則是對網絡的整體特征而言,即網絡中實際存在的連接數與此網絡可能存在的所有連接數的比值,網絡密度始終處在0到1之間,較高的網絡密度意味著節點間的連接較多,溝通渠道多元化,便于資源、信息的互動[33],通常也意味著較高的社會發展水平。局部集聚系數是度量一個節點的鄰居之間也互為鄰居的程度[34]。考古學研究中,一個高集聚系數的節點喪失,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巨變甚至癱瘓。如將史前中國各文化區的農作物類型視為社會復雜化網絡的一類節點,中原地區混作農業的各類作物集聚系數較低,某類作物的生產受損,則會激起整個農業系統的互補自救;而長江下游稻作農業的集聚系數較高,一旦水稻生產受到自然災害等因素的沖擊,則會危及到該區域整個社會系統的運轉。這也反映出社會網絡分析的一個原則,即結構關系通常要比孤立的節點屬性更為重要[35]。此外,中間中心度[36]、特征向量中心度[37]、最短路徑和雙模網絡[38]等,也常被用于考古學物質文化交流、權力變動等相關問題的研究。而與GIS技術結合,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還可以進行社會空間變換的動態分析[39]。
總之,把事物和事物之間的聯系抽象成一系列節點和連線,借助于相應的分析軟件,按照研究目的賦予節點和連線特定的屬性,從而編織出抽象的社會網絡,通過對網絡節點、連接、局部網絡、網絡整體、特定時段或歷時性的網絡分析,能為解讀古代社會提供新的視角和觀點。
三、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考古學應用
如第一節所述,當前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領域日漸廣泛,特別是針對那些分析手段多樣、分析角度多元、跨時空的大型研究課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對美國西南部前西班牙時期(1200BC—1450BC)社會網絡的時空變化分析[40]。該區域這個時期最大的特點是人口遷徙和集聚現象引發了大規模的人口變化。為重塑當時社會網絡的變遷過程,研究者從700余個遺址收集了約430萬陶片,從140余個遺址收集了4800余件黑曜巖制品,采用社會網絡分析和GIS技術相結合的方法,以陶器組的相似系數以及黑曜巖的成分聚類為網絡連接的權重,以典型遺址為網絡節點,通過對節點度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度、網絡密度等特征屬性的度量,結合GIS的最優路徑等空間分析技術,再以年代特征明顯的陶器為時間尺度,根據以往研究成果推測遺址人口,最終界定出以50年為間隔期,該區域社會網絡密度和定居中心的時空變化。結果表明,美國西南部聚落間長期存在著跨250余千米的長距離聯系,且這種聯系在歷經區域人口減少、遷移和聚落融合的過程中始終存在,社會聯系的距離長短并不總是與空間距離的遠近相關;此外,這個研究還揭示出該區域南北兩類不同的文化網絡的發展和崩潰過程,其中小型化和分散化的聚落表現出更強的穩定性。這個研究課題也說明了社會網絡分析技術對大型數據集的駕馭能力,為今后區域性、歷時性的社會宏觀研究提供了范例。
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主要以古代物質遺存為媒介,其中關于人工制品的傳播研究在社會網絡分析中所占比重最大。這些研究往往通過對陶器[41]、石器[42]等人工制品在區域內或區域間時空分布的比較分析,進而探討社會經濟組織、政治結構和人群的空間分布問題。以中美洲瑪雅文化為例[43],傳統觀點認為,該地區古代手工業制品為本地生產,并且受到社會精英階層的嚴格控制,且這種經濟模式長期處于穩定狀態。但考古學家借助可視化的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瑪雅文化分布區900BC—1520AD年間242個遺址的黑曜巖制品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他們首先評估了前西班牙時期幾個重要城市和政治中心在古代貿易網絡中的地位,根據其是否處于網絡中心判斷其所在區域經濟是否受到集中控制。接著結合地理空間數據,分析了黑曜巖的流動究竟是受到成本最低的預期決定,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流通過程中呈現周期性的增、減波動。最后作者通過對各時期黑曜巖分布網絡的密度、規模(網絡直徑和平均直徑)和層次結構變化的研究,探討了各區域黑曜巖分配系統的整合方式,以及特定地點或政治中心對黑曜巖分配網絡進行控制的程度。結果發現,古代中美洲的經濟既不是自上而下由精英控制,也沒有在長時期內保持穩定的狀態,因此并不符合人們對此區域前工業化階段手工業經濟的傳統認識。由此,他們針對之前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提出的前現代農業經濟的靜態模型,提出了古代中美洲瑪雅文化動態經濟的反例,豐富了人們對瑪雅文化社會經濟形態的認識,同時也讓人們認識到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解讀古代社會經濟形態方面的巨大潛力。
除了以上案例,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還被廣泛應用于文化邊界和文化傳播[44]、聚落(國家或政體)的形成[45]、自然災害對沿海互動網絡的影響[46]等問題的研究。但總體來看,這些都是基于不同時段內空間和物質這兩根主線展開論述。其中空間分析通常借助于GIS技術對不同的距離進行測量,通過對網絡節點的各種中心度、連接強度、最短路徑等屬性的度量,進而探討區域交流的最優路徑以及相應聚落在特定社會網絡中的地位等問題。對于物質網絡的分析,要將相應器物的存在與否、數量、密度、相似性等因素轉換為相應的權重,從而探討物質流動方向、形式和路徑等問題。其中物質網絡分析的一個重要的假設是,分析對象的高度相似性意味著更大可能地共享社會關系。總之,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是個功能強大的分析工具,可以用于驗證傳統數據分析的假設,還提供了社會活動參與者和他們族群之間交互的模型,幫助研究者明確地指明各種社會關系,以及如何度量各種關系在不同的材料、社會、空間和時間維度上的體現。它可以用于從游獵采集社會到帝國階段的不同社會尺度、從單一定居點到宏觀大區域的不同空間尺度、從某一時間段到數個世紀的時間尺度的動態分析。能讓研究者走出瑣碎的考古材料,從抽象的框架中系統地思考和解讀古代世界。
四、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需要注意的問題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潛力巨大,因而在近二十年來計算機技術發展的推動下,迅速成為歐美考古學界廣泛應用的分析方法。但是這種方法在中國考古學研究案例中幾乎仍是空白。在評估其發展潛力的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這種方法在運用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首先,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是一種方法而非理論,每個社會網絡結構都提供了很多可能性的理論視角,且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中會有不同的形成原因,我們不能僵化地用唯一的視角去看待某個社會網絡,進而限制此方法的功能發揮。
其次,我們必須謹慎進行小樣本數據的網絡分析。由于網絡分析所揭示的是數據的結構,是對古代社會或物質、空間關系的抽象表達,它畢竟不是過去事實的完整體現,因此,基于統計數據的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同其他學科或其他領域的常規性抽樣分析一樣,分析結果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樣本容量的影響。
此外,多學科合作是考古學研究發展的必由之路,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同樣如此。除基本的網絡分析需要計算機科學、統計學和數學知識外,社會網絡的空間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GIS平臺提供數據和技術上的支持。此外,社會學、地理學和人類學等學科,也都為全方位解讀社會網絡提供了獨到的見解,如中心—邊緣理論的應用等。另外,考古資料的多元性本身就匯集了類別各異的數據集,從而引導著多學科的學者進行多角度的解讀。
總之,在審慎的基礎上,我們必須承認,網絡思維是一種強大的研究視角,它可以讓我們在面對考古數據時迸發出豐富多樣的解讀方法。面對中國豐富多彩的考古材料,考古學社會網絡分析在今后的考古學研究中,必定能作出其應有的貢獻。
[1]欒豐實:《聚落考古學》,《欒豐實考古文集》(二),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472—486頁。
[2]Tom Brughmans.The Roots and Shoots of Archaeological Network Analysis:A Citation Analysis and Review of the Archaeological Use of Formal Network Methods.Berliner Beitr?ge Zum Vorderen Orient,2014,29:18-41.
[3]a.Jacob L.Moreno.Who Shall Survive?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Interrelations.Washington: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mpany,1934.b.Stephen P.Borgatti,Ajay Mehra,Daniel J.Brass&Giuseppe Labianca.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Science,2009,323(5916):892-895.
[4]Barnes J.Anderson.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Social Networks,1954,vii(1):233-252.
[5]〔美〕林頓·C·弗里曼著,張文宏、劉軍、王衛東譯:《社會網絡分析發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9—119頁。
[6]Linton C.Freeman.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Vancouver:Empirical Press,2004:3.
[7]Cynthia Irwin-Williams.A Network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Prehistoric Trade.In:TK Earle,J Ericson(eds),Exchange Systems in Prehistory.New York:Academic.1977:141-151.
[8]John Terrell.Human Biogeography in the Solomon Islands.Fieldiana.Anthropology,1977,68(1):1-47.
[9]Peter Peregrine.A Graph-Theoretic Approach to the Evolution of Cahokia.American Antiquity,1991,56(1):66-75.
[10]Linton C.Freeman.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Social Networks,1979,1(3):215-239.
[11]Jenkins David.A Network Analysis of Inka Roads,Administrative Centers,and Storage Facilities.Ethnohistory,2001,48(4):655-687.
[12]Barbara J.Mills,Jeffery J.Clark&Matthew A.Peeples.Migration,Skil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Pre-Hispanic Southwest.Economic Anthropology,2016,3(2):203-215.
[13]Bentley R.Alexander,Stephen J.Shennan.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Stochastic Network Growth.American Antiquity,2003,68(3):459-485.
[14]Fulminante Francesca.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the Emergence of Central Places:A Case Study From Central Italy(Latium Vetus).BABESCH,2012,87(1):1-27.
[15]Barbara J.Mills,Jeffery J.Clark&Matthew A.Peeples,et al.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Late Pre-Hispanic US Southwest.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3,110(15):5785-5790.
[16]Jessica L.Munson,Martha J.Macri.Sociopolitical Network Interactions:A Case Study of the Classic Maya.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009,28(4):424-438.
[17]Borck Lewis,Barbara J.Mills,Mattew A.Peeples&Jeffery J.Clark.Are Social Networks Survival Networks?An Example from the Late Pre-Hispanic US Southwest.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Theory,2015,22(1):33-57.
[18]同[15]。
[19]Stephen P.Borgatti,Daniel S.Halgin.Analyzing Affiliation Networks.In:John Scott,Peter J.Carrington(eds),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11:417-433.
[20]Tom Brughmans.Thinking Through Networks:A Review of Formal Network Methods in Archaeolog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Theory,2013,20(4):623-662.
[21]Stanley Wasserman,Katherine Faust.Social Network Analysis:Methods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9.
[22]Wouter De Nooy,Andrej Mrvar&Viadimir Batagelj.Explorator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ith Paje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4.
[23]Anna Collar,Fiona Coward,Tom Brughmans&Barbara J.Mills.Networks in Archaeology:Phenomena,Abstrac-tion,Representa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Theory,2015,22(1):1-32.
[24]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臨淄桐林遺址聚落形態研究考古報告》,《海岱考古》第5輯,科學出版社2012年。
[25]燕生東、魏成敏、黨浩等:《桓臺西南部龍山、晚商時期的聚落》,《東方考古》第2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
[26]欒豐實、方輝、許宏:《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27]陸青玉:《魯北地區龍山文化時期陶器流通問題的社會網絡分析》,待刊。
[28]Wouter De Nooy,Andrej Mrvar&Viadimir Batagelj.Exploratory Network Analysis with Pajek.Psychometrika,2011,71(3):605.
[29]梁辰、徐健:《社會網絡可視化的技術方法與工具研究》,《數據分析與知識發現》2012年第5期。
[30]Michael E.Smoot,Keiichiro Ono,Johannes Ruscheinski,Peng-Liang Wang&Trey Ideker.Cytoscape 2.8:New Features for Data Integration and Network Visualization.Bioinformatics,2011,27(3):431-432.
[31]Gjesfjeld Erik.Network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Hunter-Gatherers:Methodological Problem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Theory,2015,22(1):182-205.
[32]同[23]。
[33]同[7]。
[34]Duncan J.Watts,Steven H.Strogatz.Collective Dynamics of‘Small-World’Networks.Nature,1998,393(6684):440-442.
[35]Knoke David,Yang Song.Social Network Analysis: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2nd ed.).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2008:4.
[36]同[10]。
[37]Barbara J.Mills,John M.Roberts&Jeffery J.Clark et al.The Dynamics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Late Prehispanic U.S.southwest.In:Carl Knappett(eds),Network Analysis in Archaeology:New Approaches in Regional Network Analy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85-206.
[38]Graham Shawn,Weingart Scott.The Equifinality of Archaeological Networks:An Agent-Based Exploratory Lab Approach.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2015,22(1):248-274.
[39]同[15]。
[40]同[15]。
[41]同[31]。
[42]Briggs Buchanan,Marcus J.Hamilton,Kilby J.David&Joseph A.Gingerich.Lithic networks reveal early regionalization in late Pleistocene North Americ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6,65:114-121.
[43]Mark Golitko,Gary M.Feinman.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Pre-Hispanic Mesoamerican Obsidian 900 BCAD 1520: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Theory,2015,22(1):206-247.
[44]Terrell,John Edward.Language and Material Culture on the Sepik Coast of Papua New Guinea: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Simulate,Graph,Identify,and Analyze Soci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Between Communities.The Journal of Island&Coastal Archaeology,2010,5(1):3-32.
[45]Koji Mizoguchi.Nodes and Edges:A Network Approach to Hierarchis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Japan.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009,28(1):14-26.
[46]Carl Knappett,Ray River&Tim Evans.The Theran Eruption and Minoan Palatial Collapse:New Interpretations Gained from Modelling the Maritime Network.Antiquity,2011,85(329):1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