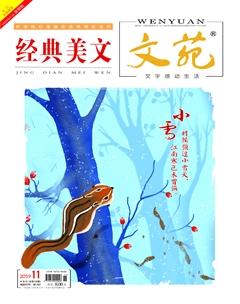巨嬰,方鴻漸的真實面目
陳思呈
巨嬰需要一個人來幫他負責任,這個人首先當然是父母;成年之后父母力不從心,那么這個臆想中可以“替自己負責”的人,其實就是全世界。仿佛全世界都應該為他的錯誤掩耳盜鈴,不然的話就任性或自憐,其實都是賭氣。
看《圍城》,無意注意到一個以前沒注意過的細節。方鴻漸在三閭大學開始他的教書生涯,常感到囧,講課時仿佛衣料尺寸不夠硬要做成稱身的衣服,課堂氣氛又悶,學生時不時缺課。種種沮喪時,他突然感慨了起來——回國后這一年來,他與他父親疏遠得多,在從前,他會一五一十稟告父親方遯翁的。只是現在他想象得出其回信不外是紀念周上對學生說的話,自己在教職員席里也旁聽膩了,用不著千里迢迢去招來。
這細節真叫人詫異,其時方鴻漸已經28歲,去歐洲留學四年回來,三閭大學教了快一年的書,是一個回鄉消息要被登當地報紙、回鄉后要在本地中學演講的人物。這時候遇事還想著“在從前,會一五一十稟告”,真不知道讓人要稱贊他的乖順,還是奉他為巨嬰。
其實方鴻漸對父親的態度甚為矛盾。一方面他清楚父親的見識,這個前清舉人、小縣鄉紳方遯翁,很可能是“最愛說教的家長聯盟”組織的重要成員,平生名言是“贈人以車,不如贈人以言”。對方鴻漸的婚事,他所贈的言是“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初見兒媳婦孫柔嘉,所贈之言則是“家無主,掃帚倒豎”,意思是柔嘉要在家里管家才是,不要外出做事,這建議成為日后小夫妻諸多爭吵的根源。
方遯翁還自信“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古訓,桌面上錄著《鏡花緣》中的奇方,給他懷了孕的三兒媳婦開的方子是:豆腐皮一張,醬油麻油沖湯吞服,因為豆腐皮是滑的,麻油也是滑的,在胎里的孩子胞衣滑了,容易下地。
方鴻漸對父親很了解,自然談不上信服。比如他父親聽說他失戀了,誤以為是與蘇小姐,方鴻漸也不敢糾正父親的誤會,唯恐他會大筆一揮,直接向唐小姐替兒子求婚,方遯翁是會鬧這種笑話的。
但同時,對這樣的父親,他有事卻總要一五一十地稟告,方家逃難住在上海租界時,住周家的鴻漸,隔一兩天就到父母處請安。這一方面是我們傳統文化倫理的影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另一方面,也許因為方鴻漸需要一個“父親”的角色來作為他稟告的對象。這個父親借現實中的父親為實體,事實上只是借了一個名分。或者這么說,巨嬰都需要一個父親,遇事可以一五一十地稟告。
方鴻漸其人,甚有巨嬰人格的影子。他看似玩世不恭,其實與其說玩世,勿寧說胡涂。例如制作假學歷這事,當時他的想法是:“父親和丈人希望自己是個博士,做兒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們失望嗎?買張文憑去哄他們,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反正自己將來找事時,履歷上決不開這個學位。”
確實他自己從沒有主動提過這個學位,但不提不等于沒做過,污點已經形成。待到蘇小姐知道這件事之后,他——“把丈人和假博士的來由用春秋筆法敘述一下,買假文憑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認干親戚是自己的隨和同隨俗——”這些解釋,有一種自以為老練的笨拙,一種掩耳盜鈴的天真,一個老實人干的丑事,總像枚沉默的炸彈在那里,不知何時會被引爆。方鴻漸的情商不足以從容地解除后顧之憂,后來他因此如何自取其辱,也不需多說了。
而他與蘇小姐的曖昧就更冤了。蘇小姐需要他的愛意,這是蘇小姐的需要,方鴻漸卻沒有能力去抵抗這樣的要求。愛上唐小姐之后,方鴻漸更覺得應該與蘇小姐疏遠,書上說,他迫于蘇小姐的“恩威并重”,還時不時往蘇家走動——“他只等機會向她聲明并不愛她,恨自己沒有快刀斬亂麻的勇氣。”其實根本不是因為蘇小姐的恩威并重,而是方鴻漸沒有力量去面對與別人情面上的破裂。
在這么“拖一天算一天”的麻痹中,他獲得一種心理舒適區。人在做蠢事的時候,未必不知道后果,都是出于軟弱假裝不知道。方鴻漸也一樣,他去蘇小姐家一次,回來就后悔一次。但是,他對自己的生活有一種鄉愿式的、“維穩勝于一切”的心理,“好比睡不著的人,顧不得安眠藥片的害處,先要圖眼前的舒服”。
在圣·埃克蘇佩里的小說《小王子》中,小王子離開他的星球,訪問了幾顆星球,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其中有一個酒鬼,令我印象最深。酒鬼默默地坐著,面前放著一堆空酒瓶和滿酒瓶。
“你在干什么?”“喝酒。”
“為什么喝酒?”“為了忘卻。”
“忘卻什么呢?”“羞愧。”
“羞愧什么呢?”“羞愧喝酒。”
方鴻漸從開假學歷到與蘇小姐曖昧,到最后失去真愛唐小姐,都有點像一個廣義的酒鬼。在生活中帶著酒精給予的醉意,麻木地往前走著,抱著沒理由的樂觀,相信他的拖延和逃避能使事情變好,能使壞事情不被命運發現。
然而方鴻漸不僅有糊涂的軟弱,還有任性之后的強硬。在三閭大學混不下去,沒接到高松年的聘書時,他惱羞成怒,只想發封信去發泄怒罵,倒是孫柔嘉比他成熟得多,阻止他說這么干全無必要。他內心良善厚道,卻易讓人看不上,比如劉東方的太太就認為姓方的小子挺無能的,孫柔嘉的姑姑也認為自己的侄女兒配錯了人。但以方鴻漸的抗挫能力,對此只有鬧翻,有點像小孩子對不滿意的局面一陣攪渾。他的自卑心理像戰時物價一樣高漲,以至于賭氣說要養條狗,說那樣就算世界上還有件東西比我低,要討我的好。
這樣的無能和賭氣,都是巨嬰人格的典型。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說,中國人認為接受他制他律是好的,一個人人格有問題時,也往往不是從這個人本身去追尋這種毛病的根源,而是回到教育者身上去,如: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孫隆基此說很有道理。同時,也因為接受他律是好的,他也需要為一個人去“事事一五一十地稟告”,這并非一種忠實,更是一種自我暗示,一種他制他律的暗示。
方鴻漸與蘇小姐曖昧也好,氣呼呼想寫信責罵校長高松年也好,歸根到底都是同一種性質,只是一個軟弱的老實人不斷地逃避對自我負責。
摘自騰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