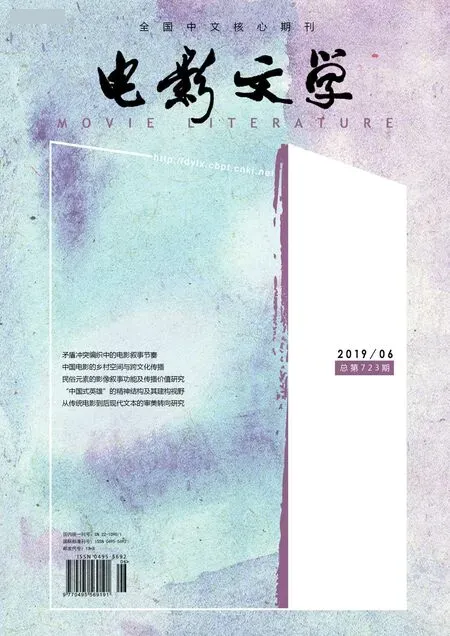“中國式英雄”的精神結構及其建構視野
曹丙燕 徐國杰 (山東科技大學 文法學院,山東 青島 266590)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旋律電影一直在尋求政治話語與大眾審美、市場資本的融合機制,近幾年一系列既叫座又叫好的電影不斷推出,并持續刷新票房和藝術的新紀錄,如《智取威虎山》(2014)、《戰狼》(2015)、《湄公河行動》(2016)、《戰狼2》(2017)、《紅海行動》(2018)等(1)學術界對這類電影的命名并不統一,有“主旋律電影”“新主流電影”“新主旋律電影”等不同稱謂,本文重在探討主旋律電影英雄人物精神內涵上的傳承與流變,因此依然采用“主旋律電影”這一名稱。,這足以證明主旋律電影正在建構符合主流價值觀念、大眾審美和市場規律的敘事模式,正在形成自己獨特的美學特征。因此,這些電影的成功遠不止票房和口碑,而是具有“事件電影”(event movie)的意義,“所謂‘事件電影’并不是就影片的表現題材而言,而是指影片上映后所引起的一系列文化現象以及造成的社會影響”[1],如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問題、文化自信問題、國家形象的建構問題等。其中,不容忽視的是影片建構了具有鮮明中國文化內涵的能指符號——“中國式英雄”。任何命名都是在他者的參照下才能彰顯獨特內涵,筆者之所以把影片中的人物稱之為“中國式英雄”,是因為他們不同于以往主旋律電影中的“戰斗英雄”“革命英雄”“民族英雄”;不同于香港武俠片中的“江湖英雄”;也不同于好萊塢影片中的個人主義“超級英雄”。這些英雄既極具個性化又有時代和民族特色,既有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又具人本精神和普世情懷,表現出更加博大的格局和更加深厚的人文關懷。《戰狼2》《紅海行動》等電影引起的轟動效應,預示著代表中國文化符碼的“中國式英雄”正在悄然生成并在當今世界文化格局獲得了一席之地。
一、英雄形象的轉型及“中國式英雄”的誕生
樹立國家與民族形象,表現政治訴求,展現國家價值觀,一直是主旋律電影區別于其他類型電影的內在特質,而民族精神、時代精神、愛國主義等主流價值觀則主要借助影片中的英雄模范形象來表達和傳播。因此,英雄形象塑造的成敗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主旋律電影價值使命的完成與否。
20世紀90年代初,主旋律電影《焦裕祿》《毛澤東的故事》《周恩來》等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優秀共產黨人和革命領袖形象,主旋律電影取得了輝煌成就。但由于好萊塢電影中的個人主義超級英雄形象的沖擊,主旋律電影因過分注重英雄人物的道德完美和集體精神,個性扁平,越來越難引發觀眾情感共鳴。例如電影《蔣筑英》(1992)講述了光學家蔣筑英為祖國科研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故事,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獲得了第13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最佳故事片提名、最佳男主角提名等多個獎項,豆瓣評分7.3分。然而,這樣一部思想性強、藝術水準高的電影在全國看片會上只被訂了53個拷貝。這一巨大反差不得不讓人反思主旋律影片該如何講好英雄故事?主旋律電影不像商業電影那樣追求票房和利潤,但作為大眾藝術,不贏得觀眾就無法完成傳播主流價值觀念的使命。于是,承載著主流價值觀念傳播重負的主旋律電影,開始了自我轉型的探索,塑造符合大眾心理需求的英雄形象。其中,“建國三部曲”——《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是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市場化轉型的一種成功模式。

表1 “建國三部曲”的投資與票房情況
注:截至2018年12月1日
資料來源:http://www.cbooo.cn ;https://movie.douban.com
這三部具有“獻禮”性質的影片在兼顧國家價值觀念和藝術性的同時,充分考量了受眾心理,在人物塑造上大膽融合商業電影熱點元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對“豪華全明星陣容”的起用,以《建軍大業》為例,電影時長133分鐘,有54位明星亮相,平均兩分半鐘就會出現一個明星,強烈吸引了青年觀影群體。更重要的是 “建國三部曲”對歷史人物的塑造視角更加平民化、日常化,對諸多身處政壇高位的歷史偉人進行多層次塑造,改變了以往的神化書寫和審美定式。《建國大業》由一個孩子的視角,描繪了淮海戰役勝利之夜領袖們把酒當歌慶祝勝利的場景:一向儒雅的周總理衣衫不整,朗聲高唱《國際歌》;毛主席喝到半醉,歪倒在一旁大笑。概念認知中莊嚴偉岸的領袖形象走下神壇,卻增加了感染力和親和力。不過在肯定三部影片成功轉型的同時,也不得不指出從《建國大業》到《建軍大業》投資額增加了6倍,而票房變化卻不大,市場效應明顯下滑。可見,僅靠明星陣容、敘事細節上的平民化處理,這種淺層次的商業元素借鑒很容易導致觀眾的審美疲勞。
近幾年,《智取威虎山》《戰狼》《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等電影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實現了從精神內涵到敘述手段的真正轉型。《智取威虎山》將紅色經典做出了適應新時代觀眾審美心理的新解讀,將俠義精神融注革命精神重塑了楊子榮等戰斗力驚人、智勇雙全的英雄形象;《湄公河行動》選擇“國際緝毒”這一現實社會熱點題材,塑造了高剛、方新武等中國緝毒警察形象;《戰狼》系列中的冷鋒既是一名具有超強戰斗素質的特種兵,也是俠肝義膽、重情重義的男子漢,還是常常意氣用事、不守紀律的“刺頭”;《紅海行動》中的“蛟龍”突擊隊,八名隊員個個軍事素質過硬,他們團結協作,為了營救同胞、維護世界和平舍生忘死,成功塑造了新時代“中國軍人”的群像。這些全新的英雄形象與正在崛起的大國形象契合,點燃了觀眾的愛國熱情,使主旋律電影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票房神話(見表2)。

表2 2014年以來幾部代表性主旋律電影的投資與票房情況
注:截至2018年12月1日
資料來源:http://www.cbooo.cn ;https://movie.douban.com
尤其是《戰狼2》不僅創造了中國電影票房的新紀錄,也是唯一進入全球電影票房前100的非英語影片。另外, “第34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提名”中,《紅海行動》幾乎包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等所有獎項提名,一舉領跑百花獎榜單。由此可見,《戰狼2》《紅海行動》等影片中的英雄形象符合中國觀眾普遍的審美心理和價值理想,他們的能力與智慧、情懷與擔當契合了人們對新時代“中國式英雄”的想象。
二、“中國式英雄”的精神結構
毋庸諱言,《戰狼2》《紅海行動》這些影片在英雄人物塑造上的成功,與其在美學與敘事策略上對香港警匪片和好萊塢英雄片的借鑒分不開,但是在精神內涵上卻具有鮮明中國文化特色和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特色;與以往主旋律電影中的英雄相比,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超越性,成為具有鮮明標志的“中國式英雄”,筆者認為“中國式英雄”的精神內涵表現在三個層面:
(一)基礎層面:“個性化”英雄
在我國的傳統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領域,一直強調集體意志高于個人意志,個人主義總是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話語而處于他者化狀態,投射在英雄形象塑造上,主旋律電影中的英雄人物總是集體意志的體現,缺少個性化意識和個人情感表達。綜觀近幾年幾部成功的主旋律電影,盡管敘述視角不同,但片中英雄都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人的個體意志被充分尊重。
《智取威虎山》《戰狼》系列等影片大膽突破,一改群體化的敘述視角,塑造了類似好萊塢超級英雄的個人化英雄形象。以《戰狼2》為例,冷鋒是整部影片的中心人物,他出場不久便被軍隊開除,影片以這種方式讓他與集體保持了距離,彰顯個人意志。他的身上有軍人的擔當精神,有過硬的軍事素質,有高度的人道主義情懷,又不乏幽默感。但是與以往神性化英雄不同,影片塑造人物的著力點不是完美而是個性化,除了對英雄超能力和愛國精神的凸顯,影片還通過諸多場景和細節刻畫了他意氣用事、桀驁不馴的一面,對拆遷的惡勢力以惡制惡;對敵人輕蔑地“豎中指”;就連到非洲的目的也完全是個人的,為未婚妻龍小云復仇。這些缺憾不但沒有降低冷鋒的英雄魅力,反而使他的英雄氣與世俗性融為一體——有血性、講義氣、有擔當,拉近了觀眾與英雄的距離。
《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敘事視角是群體性的,影片中的主角英雄不是哪一個具體的人,而是由多人組成的行動隊,但這絕不意味著傳統英雄群像式刻畫的簡單回歸。以《紅海行動》為例,片中的英雄是八人組成的“蛟龍”突擊隊,戰斗中以集體為基本作戰單位的對抗是其顯著表征。但個體英雄并沒有被“蛟龍”的整體形象淹沒。首先,蛟龍小隊的每一個隊員所肩負的職責是不同的,隊長楊銳,副隊長兼爆破手徐宏,觀察員李懂,通信兵莊羽,狙擊手羅星、顧順,醫護兵陸琛以及機槍手張天德和佟莉,每個隊員都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次,影片在群體性敘事中對每個相對獨立的個體也進行了個性化塑造,隊長楊瑞外冷內熱、思慮周全,為穩定軍心,向隊友隱瞞羅星的傷情;與恐怖分子搶奪黃餅,彰顯了他的人道主義情懷。觀察員李懂技術過硬,但是抗壓能力差,最初面對戰事心態不穩,在戰火考驗下迅速成長,關鍵時刻一槍擊斃恐怖分子扭轉了戰局;狙擊手顧順心高氣傲,外冷內熱,極具人道主義情懷,當他發現敵人的狙擊手不過是一個孩子時,略偏槍口,僅擦傷了他的臉而不忍心將其擊斃……這類精妙細膩的形象刻畫,使得每個個體都獲得了鮮活的個性化自我。
綜上所述,個人主義視角并非好萊塢英雄的專屬。“事實上,個人英雄主義在影片中的適當安放不僅可以作為傳播不同價值觀的載體……還能夠作為主流價值的代言得以在敘事中發揮作用。”[2]群體性視角也不意味著英雄形象的概念化與符號化,尤其是在家國同構的故事中,集體的形象通過生動的個體才得以具象化呈現。銀幕上的英雄只有具備了強烈的個性辨識度才能被觀眾記住,只有符合立體化的人性書寫才有感召力,這是“中國式英雄”生成的基礎。
(二)核心層面:個人情感與國家意志的融合
在以往的主旋律電影中,為了凸顯英雄的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精神,總是將其置于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個人倫理與民族大義的矛盾沖突中,最終通過個人的奉獻與犧牲完成英雄人物的道德升華。這樣的敘事模式,讓觀眾對英雄人物的高尚人格產生崇敬之情的同時,也因其趨于神性的完美而產生距離。《戰狼2》《紅海行動》等影片,也一次次將英雄人物置于生死考驗中,但是突破性在于個人情感與集體意志、國家使命不是二元對立,而是高度融合,這使得英雄作為自由個體的自我生命價值和作為集體使命的家國擔當有了統一性。
與《湄公河行動》中的方新武相似,《戰狼2》中冷鋒遠赴非洲目的也是為未婚妻龍小云報仇。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暴動,喚起了他作為軍人的使命感,主動承擔起撤僑的任務,由此也實現了冷鋒從爭強斗勇的莽漢式個人英雄向有家國情懷和人道主義精神的中國式英雄的轉換。在斗爭過程中,冷鋒發現對手竟是殺害未婚妻的兇手,所以冷鋒與雇傭軍“老爹”的對決,既是國家意志與國家力量的顯現,也是個人情感意志的驅動。在《紅海行動》中,“蛟龍”突擊隊本來的營救目標只是鄧梅,而記者夏楠極力說服隊長楊銳搶奪黃餅,以避免恐怖分子制造更大災難。為此,夏楠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交換人質鄧梅,冒死與突擊隊員并肩作戰。夏楠在影片中對蛟龍突擊隊行動的升級與國家形象的升華起了重要推動作用,但是影片并沒有把夏楠塑造成一個符號化的人物。她的犧牲精神與斗爭勇氣,不是凌空高蹈的理念,而是源于丈夫和孩子死于恐怖襲擊的慘痛經歷。
這些情節設置具有類型化的特點,但正是由于肯定了個人情感和倫理,才沒有把英雄人物架空,成為國家意志的傳聲筒。同時也由于個人情感與國家意志的高度融合,才在敘事上順利實現個人意志向國家意志的升華,為個性化的英雄賦予愛國主義的精神特質,這也是“中國式英雄”與好萊塢超級英雄的區別。當然,好萊塢超級英雄最終也實現了個體向群體歸屬,但是兩者之間需要一個媒介,這個媒介往往由超級英雄的“道德父親”扮演。“道德父親傾向于社會利益,是超級英雄價值理念的引導者,是超級英雄頭上的緊箍咒。特別是在道德父親去世之后,他的形象便永遠地烙在了英雄的心中,他的教誨升華為不可改變的定律。”[3]而且超級英雄扮演的始終是群體利益的保護者,而不是群體中的一員,這也是兩者重要的區別。在被普遍認為好萊塢色彩濃厚的《戰狼2》里,影片用了大量意象和細節凸顯冷鋒的民族大義和愛國精神,冷鋒與“老爹”的對決明顯處于弱勢,因“老爹”撕掉了冷鋒臂上的徽章“I FIGHT FOR CHINA”,冷鋒瞬間被激怒,急中生智,反敗為勝;冷鋒帶著僑胞通過交戰區時,以臂為旗桿,讓中國國旗高高揚起,交戰雙方看到五星紅旗,立即停止射擊。這些細節告訴我們,超級英雄之所以戰無不勝是因為他背后站著一個強大、正義的國家。無論是《戰狼》系列中的個體英雄,還是《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中的群體英雄,最終都是正在崛起的、有國際擔當的中國國家形象的象征。
(三)拓展層面:英雄的人道主義與普世情懷
最近幾年主旋律影片中的“中國式英雄”之所以是“中國”式英雄,還因為英雄的舞臺和參照系發生了變化,《戰狼》的故事發生在中國邊境;《湄公河行動》在泰緬邊境的金三角;《戰狼2》《紅海行動》都發生在非洲,他們的英雄行為較之以前已經超越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這些國家主義價值觀,體現出英雄跨越國界和種族的人道主義與普世情懷,體現出崛起的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上的責任擔當。
《紅海行動》中,“蛟龍”突擊隊這一英雄群像的塑造是通過三個層面的營救任務逐級開拓其精神內涵的:第一項任務,保護中國商船和被圍困的中國僑民,體現出中國政府對公民權益的捍衛。第二項任務,營救人質鄧梅,此時“蛟龍”突擊隊保護的是個體的人,體現了國家對公民個體生命的尊重和個人權益的捍衛。與以往的主旋律影片相比,這是一個重要突破,因為我們每個人——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都有可能會成為那個需要救助的“鄧梅”,而我們的國家不會拋棄每一個公民,這樣的人本精神,大大點燃了觀眾的愛國熱情。第三項任務,與恐怖分子搶奪黃餅,已遠遠超越了保家衛國的范疇,表現出超越國家民族界限的普世情懷。在《戰狼2》中這種普世情懷落到了冷鋒身上,冷鋒帶著救援飛機來到華人工廠,管理者老林把中國員工和非洲員工分開,要求只帶中國員工離開,這原本是符合救援任務要求的。但是在戰爭和死亡面前,冷鋒扮演的不僅是中國僑民的保護者,而是不分國籍和種族的全人類的保護者,他的一聲“婦女兒童上飛機”,體現出對人類平等的生命尊嚴捍衛和普世的人道主義情懷。也正是在保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這些中國式英雄成為“超級”英雄,因為他們不僅是中國的英雄,也是人類的英雄。
上述三個層面的精神內涵,也是“中國式”英雄敘事展開的三個層次,具有超強能力的“個性化英雄”——具有愛國精神的“國家英雄”——具有普世情懷的“超級英雄”。以《戰狼2》《紅海行動》為代表的影片,正是在這三個層面實現了對以往主旋律電影中革命英雄形象的升級,也使這些英雄形象成為能夠走向國際銀幕上的中國文化符號。
三、“中國式英雄”建構的美學視野
根據電影產業的標準化和復制性特點,《戰狼2》《紅海行動》等影片的巨大成功,將會引發一大波的“英雄熱”。近20年來,類型化已經成為電影普遍的敘事策略,緝毒、撤僑、災難、革命、戰爭等宏大題材,出奇制勝的情節,驚心動魄的打斗場面,充滿溫情的細節,都會成為英雄電影的敘事要素被復制生產,在這些敘事模板中注入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思想,英雄片成為一種類型電影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我們早就遭遇過簡單復制帶來惡性后果,例如那些空洞的武俠大片,雷人的抗日神劇。《戰狼2》《紅海行動》等影片在電影市場的成功并不能說明主旋律電影已經建構起成熟的美學范式,這些影片是主旋律電影成功開拓的代表作,還沒達到敘事美學的成熟。就主旋律電影多年的轉型探索來看,轉型一直側重于對好萊塢電影、中國香港警匪及武俠電影的視聽元素、敘事模式層面的學習和借鑒,電影畢竟是以內容為王的產業,除了可復制的故事情節、可模仿的視聽要素與敘事模式,成熟的敘事美學還需要具有包容和共識性的精神內核的建構,這是“中國式英雄”建構最核心的東西。
主旋律電影是中國獨特的電影類型,但是以電影的方式弘揚國家和民族文化的“主旋律”并不是中國電影獨有的現象,每個國家都在電影中融注了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好萊塢超級英雄正是美國個人主義、樂觀精神及普世價值的集中反映,并通過“超人”“蜘蛛俠”“鋼鐵俠”這些廣受歡迎的形象把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傳遞到全世界。我國發展主旋律的電影口號提出于1987年,特指“弘揚民族精神的、體現時代精神的現實題材和表現黨和軍隊光榮業績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4]這一命名對電影題材及思想性的規定具有很強的國家意識形態色彩,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電影市場狀態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文化進入全方位轉型,電影創作呈現兩種傾向:一方面,以文化反思和現實批判為主的藝術電影表現出強烈地對政治話語的排斥;另一方面,電影迎來娛樂化高潮,一些影片出現了明顯的庸俗化傾向。在這樣的背景下,主旋律電影“以國家的名義,強調了社會主義電影文化的特征,其規范的意識形態很明顯,目的正在于以社會主義體制的身份意識重新確立秩序,規定電影格局”。[5]如今30多年已經過去了,時代語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電影與政治、市場的關系重新組合,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越來越多的電影走出國門,豐富著世界銀幕。在這樣的情境下,“ ‘大片’可能是中國電影‘走出去’的一種重要形式和策略。或者說,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和文化大國,唯有創作出能為世界廣泛接受的大片,我們的民族電影工業才可能在未來真正屹立于世界電影工業之林中”。[6]文化語境和電影使命的改變,要求主旋律電影的思想內涵和價值體系做出相應調整,讓它更能體現當代中國的精神和氣度,更易于觀眾認同和接受,有更強的包容性和共識度。這些內涵上的變化映射到英雄人物塑造上,它的潛在觀眾既包括國內觀眾也包括海外觀眾,這就要求中國式英雄形象的建構應當具有更加開放的、國際化的美學視野。在其精神內涵上要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等特質,突出本民族的個性化表達,也要具有人本精神和普世情懷;在敘事上,既不能為了傳達國家意志而壓制了英雄個體的自我表達,也不能為了迎合觀影需求而一味模仿西方,喪失獨立話語的闡述。可以說,“中國式英雄”美學視野建構是這一文化符號能否立足世界銀屏、獲得價值認同的核心和基礎。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對世界經濟與文化的參與度越來越高,通過電影鮮活的鏡像聚焦表現中國式生活方式、行為習慣、審美特質和人文關懷,讓世界了解中國,實現多民族文化平等且良性的互動,是中國電影的使命。中國的崛起不僅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勞使本國人民安樂幸福,也擔當著維護世界和平、構建人類共同命運的責任,“中國式英雄”要把這樣的國家形象傳遞到全世界,在遵循電影產業規律的同時,使中國主旋律電影在國際視域中獲得更為廣泛的傳播空間和更多的話語權,打造具有鮮明辨識度的“中國式英雄”,讓世界看到“中國式英雄”,這不僅是主旋律電影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電影產業走向成熟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