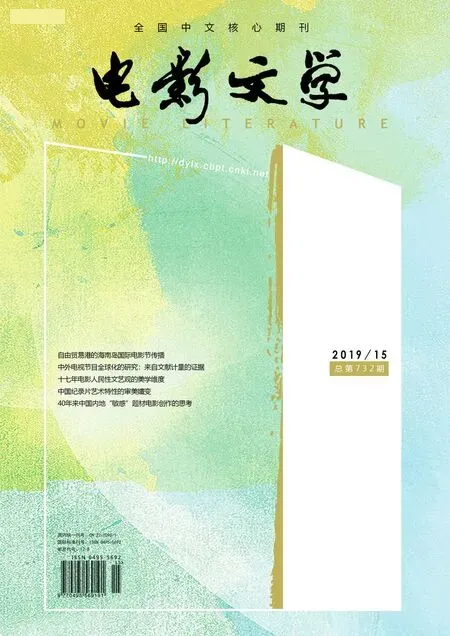消費語境下新聞改編電影的表演觀念
張雅楠(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00)
中國電影的發展進程中,向來不乏現實題材的創作身影。其中,由新聞事件改編的影片自出現便深受觀眾青睞。1921年中國第一部改于新聞事件“上海洋場惡少閻瑞生謀財害命案”的電影《閻瑞生》在上海播出,且在上映首日就獲得1300塊大洋,可以說《閻瑞生》是一部成功的商業片。此類影片也是第六代導演創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因他們側重邊緣化敘事和個人化表達,影片不僅難以通過審查,也遭到主流市場疏離。電影《可可西里》《天注定》《圖雅的婚事》《日照重慶》等都被貼上“邊緣、晦澀、小眾電影”等屬于各自的標簽。2013年中國電影市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后,新聞改編電影因自身優勢成為部分創作者在市場考量下的自覺選擇。此類影片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長,且出現像《湄公河行動》《我不是藥神》等叫座又叫好的佳作,它們也成為當前主流商業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表演觀念是指“人們關于表演藝術及其創作方法的最基本的看法”(1)陳亮.中國本土電影表演觀念研究 [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12.。實際上,銀幕最終呈現的表演觀念不僅包含演員的直觀表達,也蘊藏著導演的思想理念。本文以消費語境下新聞改編電影所具優勢為基點,結合2013年后近五年的10部新聞改編電影(表1),分析影片表演成分處于重要位置的原因,著重探討在導演的表演需求和演員的表演創作中隱匿的表演觀念。

表1 2014—2018年上映的新聞改編電影及上映日期
一、消費語境下偏重故事電影改編的市場選擇
商業化發展和市場化進程下,影片的票房高低,不僅成為資方獲利大小的參考指數,也成為一部電影成功與否的考量標準之一。依此,利益最大化也成為電影產業在市場中生存發展的基本訴求。社會新聞所具有的關注度及中低成本投入成為新聞改編電影的優勢所在,在此基礎上,投觀眾所好的故事化電影改編在具有更強可看性的同時,也使表演成分處于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
(一)節約成本,風險可控
消費語境下,“一個健康的電影市場的型構,應該是金字塔式的——少數的大制作電影位于尖端,中、小、低制作電影是基座,電影產業收入則主要來自中、小規模投資的影片”(2)饒曙光,畢曉瑜.中小成本電影的困境和策略——以現實題材影片為例[J].當代電影,2008(01):9-13.。依據饒曙光在文中(3)同①。“大制作:投資多在億元以上,期待(國內)票房通常在一億元以上。中等制作:投資和期待(國內)票房大致在1000萬~5000萬元之間。小制作:成本在400萬~1000萬元之間,期待票房(國內)往往在100萬~1000萬元之間。低成本制作:成本在150萬~300萬元左右”。對當下電影投資規模的劃分,10部電影(表2)中屬于億元以上投入的少數尖端大制作電影有3部,即《戰狼2》《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其余7部都是中低成本電影,即《我不是藥神》《親愛的》《失孤》《解救吾先生》《追兇者也》《十八洞村》《心迷宮》,這也從數量上印證了既作為電影市場塔基又作為電影產業保障的中小成本電影更具普遍性。

表2 2014—2019年新聞改編電影的票房和成本(單位:萬元)
被選取改編電影的新聞事件,多是與人民生活相關的社會事件、社會風貌和社會問題。7部電影中,有6部影片的新聞原型是發生在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故事,而改編于“吳若莆被綁案”的《解救吾先生》是備受人們關注的明星事件。這類影片的視覺表達,不需要宏大場面和酷炫特效,制作成本自然不會太高。與動輒幾億元的高投入相比,7部影片中成本投入最高的《解救吾先生》為8000萬元,《心迷宮》投入僅170萬元。此外,改編電影在上映前,早已建立相應情感鏈條的受眾也成為影片的潛在觀影群。而電影中熟悉的生活場景和很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的經歷更容易將觀眾帶入角色,產生共情。這使影片在具備一定票房號召力的同時,也擁有了一定的票房保障。
(二)偏重故事電影的改編
新聞改編電影,可從紀實片創作和故事化改編兩條路進行,盡管二者處于相互融合、相互借用的漸近線上。但7部電影無一例外都選擇故事電影改編,究其原因是消費語境的商業邏輯下,“商品的意義來源于它們在符號的制作和再制作這一延續過程中的位置”(4)[英]西莉亞·盧瑞.消費文化[M].張萍,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64.。由此,作為商品的電影也成為一種意義符號。而“屢屢刷新票房的喜劇片、不時引發熱議的青春片和都市愛情片,以及持續扎堆上映的驚悚/恐怖片不僅成為當下中國電影產業的主體力量,更凝聚著當前大眾文化的整體氣象”(5)張志秀.景觀化的中國——對消費語境下國產商業片創作現狀的觀察與思考[J].當代電影,2017(08):150-151.。與紀錄片相比,故事化改編的劇情片更具生動性、趣味性且富有人情味,而更具可看性的故事不僅更易被觀眾接受,也更容易產生多元的意義符號,發揮電影的商品價值。《我不是藥神》的改編就偏于商業片,“《我不是藥神》的整個節奏都特別清晰,起承轉合、動作、喜劇元素都特別類型化”(6)ARRI.9.0高分電影《我不是藥神》攝影指導王博學專訪[J].影視制作,2018(07):43-50.。而嚴格遵循新聞六要素“5W1H”的社會新聞,有著合理清晰的故事脈絡,也成為改編的充分條件。得以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背后,隱藏著一個或一系列曲折離奇的故事。《親愛的》中兒童田鵬(原型:彭文樂)在被拐三年內與養母李紅琴(原型:高永俠)產生濃厚感情,親生父親田文軍(原型:彭高峰)將孩子帶回家后,反而成為對孩子的“二次拐賣”。新聞價值又使改編后的電影更易上升至倫理道德、社會意識和法律層面。《親愛的》不只關注被拐兒童的心理健康,也譴責了拐賣兒童的犯罪人群,呼吁對其施以嚴厲的法律制裁。
新聞事件的故事化改編,無論是以新聞故事為原型進行戲劇性調整,或是以新聞框架為藍本填充故事內容、豐富人物語言,由真實新聞改編的影片或多或少受到事件原型的約束。此時的新聞改編電影是在有所限制的前提下,盡可能保證人物真實性和事件完整性,并圍繞原型的人物性格和人物關系塑造角色。不依靠酷炫特效的中小成本劇情片,使表演成分成為故事得以推進的重要保障。
二、消費語境下新聞改編電影中導演的表演需求
與新聞相比,電影因創作周期較長成為一種傳播很慢的媒介。經改編上映后的電影,新聞信息本身的價值已不再是賣點,取而代之的是通過影像表現新聞信息的方式。換言之,新聞依靠信息“內容”獲得關注,而電影則依靠信息“形式”賺取票房。在此“形式”的創作中,導演作為“首要作者”,規范和引領著其他創作者的表達,演員也不例外。從創作角度來說,正是導演和演員的默契合作,打通了通向銀幕角色人物的道路。實際上,銀幕角色形象也是信息“形式”的呈現方式之一,導演的美學視域和創作探究也決定了他對表演的需求。而導演的表演理念,不僅影響著演員選用,他們在影片中的視聽運用也影響演員的表演。
(一)口碑和商業并重:放棄非職業演員
新聞改編電影中的“表演成分是‘第六代’電影人的重要文化標志牌以及精神姿態”(7)厲震林.中國電影美學思潮史述1979—2015[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7:136.。早期的賈樟柯常選用非職業演員擔當主演表現邊緣人物,是因為他們純粹且直接的情緒化表演。但在消費語境的市場壓力下,導演選擇演員不能單純考慮演員對于影片整體呈現的愿景,還要顧及票房。7部電影的導演都沒有選用非職業演員飾演主要人物(表3),其中6部是明星演員+職業演員的演員陣容,而新晉導演忻鈺坤的《心迷宮》中雖無明星演員參演,卻都是職業演員。從票房成績來看,明星演員參演顯然是有一定票房號召力的。
表3 本文研究影片的導演表及主要演員表
實際上,明星策略作為電影工業的法寶之一,不只因為他們的票房吸引力,還因為明星演員銀幕外的生活形象和銀幕內的角色形象賦予電影形象顛覆的張力。形象顛覆,在電影學中指“推翻原有的經典或傳統,在原有人物的基礎上重新塑造,改變其形象和個性”(8)陳偉.明星形象顛覆與觀眾認知——以《親愛的》為例進行的互聯網觀察[J].當代電影,2015(07):111-114.。首先是外在的形象顛覆,《親愛的》中李紅琴由趙薇扮演,成名之后的趙薇多以時尚形象示人,這與影片中的農村婦女形象有極大反差。《失孤》中的尋子農民雷澤寬由天王劉德華飾演,外形俊朗的劉德華與影片中頭發花白、胡子拉碴的銀幕形象簡直天壤之別。也正是如此顛覆性的形象,在電影開拍時,天王劉德華變身邋遢農民就成為影片噱頭之一。由此,銀幕外明星生活形象和銀幕內人物角色形象的“顛覆”重構,為影片帶來話題關注度的同時,也為影片帶來巨大的戲劇張力。此外,還有內在的形象顛覆,也就是演員賦予情境的張力,即演員能不能深入角色核心,能不能理解角色經歷及其在角色人生中的心緒轉變。這并非意味著演員需要與角色有同樣的經歷,但演員自身的生活經歷、敏感性、使命感及其表演技巧的運用確實可以影響角色人物的塑造。《親愛的》中扮演李紅琴的趙薇是一位媽媽,對孩子的母愛自然能感同身受。劉德華在演藝生涯中的敬業,以及在現實生活中低調做公益的正能量化身,與《失孤》中執著善良的雷澤寬在人物品格上極其相似。《親愛的》尋子會的場景中,飾演一位失子母親的孔令美僅僅參與了一段表演,但她講述時微微顫抖的嘴唇,及在給眾人和自己鼓勁兒說完“加油”的那一瞬的笑中帶淚,所體現的正是一名職業演員的專業素養和技能。盡管《十八洞村》屬于宣教片,但仍取得10711萬元的票房成績。這也正是消費語境下導演選擇經過訓練的職業演員參演的原因。
(二)多元鏡頭語言所側重的表演
新聞通過文字闡述,電影通過視聽表達。有足夠技術支撐的多機位拍攝的今天,演員是否仍須熟悉攝影機的位置并了解其拍攝手法,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導演基于通過視覺畫面表達,而突出的視覺中心是什么始終影響著演員的運動速度和節奏,正是攝影機和演員的有機融合構成了電影的形式元素之一,并以此表現影片的視覺沖擊力和感染力。電影演員熟悉鏡頭同話劇演員熟悉舞臺一樣重要,因為影片多元的鏡頭表達對演員表演有不一樣的要求。
1.長鏡頭:充沛時間下情緒的連貫表達
長鏡頭是指在一段時間內不打斷時間的自然流程而完整再現事件發生的過程。長鏡頭給予演員充分的時間進行自然的表達,連貫的情緒流露使角色人物更具真實感。《我不是藥神》的拍法“是通條拍攝,就是一場戲從頭到尾不停機,演員一直演,導演也不會打斷演員表演”(9)ARRI.9.0高分電影《我不是藥神》攝影指導王博學專訪[J].影視制作,2018(07):43-50.。《失孤》中同樣是長鏡頭默默跟隨雷澤寬一路尋子。此外,長鏡頭也帶給演員表演一定的限制。新聞改編電影較少通過外部激烈沖突展現人物內心斗爭,而是經由長鏡頭的客觀注視引發觀眾思考。《失孤》中周天意的媽媽自殺的場面,為了沖淡情感的沖擊力,導演使用中遠景鏡頭,此時演員展現情緒就需要通過肢體動作的表演,但不能肆意妄為。《親愛的》中韓德忠情緒失控之后,通過長達40秒的固定長鏡頭呈現韓德忠的情緒,飾演韓德忠的張譯通過倚靠小賣部墻壁哭泣完成這一規定情境中的最高任務。而李紅琴在最后一場戲中,一直被丈夫欺騙,認為自己不具有生育能力,但在即將得到吉芳的撫養權時,檢查結果顯示自己已經懷孕,面對血緣與親情,導演將鏡頭漸漸拉遠,將其置于更為廣闊的環境中以顯示她的無助和無力,此時李紅琴的扮演者趙薇并未有太多瑣碎的肢體動作,只是蹲在走廊上放聲哭泣。不同于第六代導演影片中非職業演員的情緒化表演,長鏡頭下演員的情緒表演,需要集中注意力進行連貫性表達。同時,中遠景鏡頭下肢體動作表演既不能豪放夸張,也不能過于瑣碎,而是不斷接近角色人物由內而外散發的情緒和氣質。
2.特寫鏡頭:調動每一寸肌膚的心緒變遷
特寫鏡頭使演員從周圍情境中凸顯出來,可以表現人物細微的情緒變化和瞬間的心理動向,容易使觀眾在心理上受到感染。特寫鏡頭之下,細節之處會被無限放大,微相表演和眼神變化向來是特寫鏡頭所關注的,這些細微的變化更易表達角色的復雜心理,也給予演員一個良好的表演時機來證明自己的演技。《解救吾先生》在華子被捕審訊的時候,他被銬的手試圖在椅子后面掙扎以及無法伸直的雙腿,反映的是一個被捕入獄的犯人內心的不服和不適,而銀幕上無限放大的華子笑瞇瞇、無所謂的模樣凸顯了華子的癲狂和挑釁。《親愛的》中在田鵬生日宴上,一直堅信能找到孩子的韓德忠宣布妻子懷孕,親吻田鵬后離開,這時給人物一個面部特寫鏡頭,從韓德忠的眼神中,我們看到的是“心如死灰”四個字。而魯曉娟去看心理醫生這個鏡頭,通過與心理醫生對話時候的面部特寫鏡頭,我們看到魯曉娟因為丟失孩子而過度悲痛,沉著疲憊的臉,當角色面對鏡頭說話時,似乎是在和每一位觀眾訴說“‘你的孩子沒有丟……’所以你才能如此云淡風輕地跟我說話”。特寫鏡頭下演員眼神和面部表情的每一個細微變化,呈現的是角色人物復雜的心理,這也要求演員對作為表演創作素材的自身非常熟悉,甚至于對身體素材的每一個組件都了如指掌。當然,特寫鏡頭也給予演員充分發揮演技的表演時機。
3.手持鏡頭:戲劇性的情節過程表現
手持鏡頭沒有拍攝區域的限定,相對靈活的鏡頭可以隨時抓取演員的表演,此時演員的表演表現的是情節過程的發生。演員“仿佛根本沒有表演,只是一個真實生活中的人在其行為過程中被攝影機抓住了而己”(10)同①.。《親愛的》中李紅琴在公安局接受審訊的場面,此時手持搖晃鏡頭的不穩定感是為了體現李紅琴的緊張與害怕。這時演員的表演空間雖然相對充裕,但若在鏡頭搖晃的同時,演員動作幅度偏大的表演不僅不能體現一個農村婦女的“不諳世事”和緊張,反倒過猶不及,給人一種“混亂”之感。反觀趙薇的表演看似很安靜,她靠著蹲在墻角下,只在回答提問時才偷偷抬頭望向警察,不知所措、局促不安的感覺體現得恰如其分。《我不是藥神》中,作為執法者的曹斌本應嚴守法律秩序,但在面對可以拯救無數限于病魔中的鮮活生命時,在法律和道德之間,他的內心出現搖擺,此時手持鏡頭的搖晃所體現的是曹斌內心的矛盾和掙扎,最后定格在鏡子中的曹斌是為了影射他內心已經做出的決定,而我們觀察曹斌的扮演者周一圍此時也僅做出一個緩慢但不僵化的抬頭動作。盡管手持鏡頭給予演員足夠的表演空間,但此時演員既不能像特寫鏡頭中刻意關注細節又不能像長鏡頭中營造意象化的情緒,而是實實在在表現事件發生的過程和人物的心理和思維變化。手持搖晃鏡頭下,演員表演更像是以靜制動,通過為數不多的動作表達角色的心緒變化。像壓抑的雄獅將所有情感包裹在身體中,只待一觸即發的瞬間宣泄而出。
如果說,手持搖晃鏡頭下的個人戲,是角色人物情感積蓄和思維變化的戲劇表達。那么,手持跟拍鏡頭下的群戲,則是情節“實際過程”的發生。《親愛的》中田文軍、韓德忠一行人誤將黑猩猩當成被拐兒童的追趕場面,田文軍、魯曉娟被李紅琴所在農村的村民追堵的過程和他們“搶奪”孩子的一場戲,以及李紅琴在活動中被丟失孩子的家長“群毆”的場景,都是手持鏡頭拍攝的畫面。《解救吾先生》在華子與其同伙出手綁架時,導演采用手持跟拍的方式,整個畫面跟隨華子的手進行拍攝,鏡頭在吾先生和電影制片人之間來回晃動三次之后,華子已經架著吾先生離開。不難發現,群戲中的手持跟拍都伴有比較強烈的運動過程,這也要求此時群戲的演員在各司其職的情況下,肢體動作的表演應當快速、有力、準確,以便直接呈現情節發生的戲劇性效果。
(三)同期聲和方言運用:語聲表演的測金石
作為電影錄音工藝之一的同期聲,是對現場真實聲音的記錄,顯然,它比后期配音更逼真、自然。因為同期錄音在反映角色的同時,也映照出角色人物所處的環境。這也意味著對演員語聲表演能力的考量。不只是同期聲的錄音選擇,導演在影片中的方言設置于演員而言同樣是一種挑戰。
明代音韻學家陳第所言: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隨著電影形式的不斷豐富,方言運用也從紀實美學轉向形式主義的探索,其作用也從簡單地展示真實轉向戲劇性表達。影評人、編劇程青松也曾說過:“第六代導演和寧浩運用方言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追求紀實美學風格,后者是追求夸張的、戲劇性的商業效果。”(11)夏璠.方言作為電影表現形式元素的探討[J].電影評介,2010(16):27-28.消費語境下的新聞改編電影,選擇方言的目的則兼具上述效果。不只為使人物角色更加真實可信,具有日常生活的真實感,運用方言塑造的形象生動的角色能增強影片的戲劇性效果。《親愛的》中樂于教孩子方言的田文軍以及鄉下農婦李紅琴。《十八洞村》大量使用花垣縣當地的方言。在《追兇者也》中,導演巧妙地將云南方言與東北方言植入其中,因為方言在營造紀實風格環境的同時,具有得天獨厚的喜劇優勢。“如果我要拍一個發生在昆明的現代都市故事,語言的運用可能就無所謂了,用普通話也是可以的。但要拍一個發生在邊陲地區的故事,要是人物滿嘴都是字正腔圓的普通話,那肯定不是我要的感覺了”(12)曹保平,連秀鳳,唐宏峰,梅雪風,陳雨薇,田艷茹.《追兇者也》四人談[J].當代電影,2016(10):51-57.。不難發現,以方言示人的角色多為底層人物,因此,經常出現參演新聞改編電影的演員在影片開拍前特意學習某一地域方言的現象,而不少演員也將方言學習作為塑造人物的入口。
三、消費語境下新聞改編電影中演員的表演創作
大片依靠視聽奇觀吸引觀眾,中小成本電影的觀眾基礎則在于故事,由新聞事件改編的電影,故事整體走向觀眾皆有所了解,此時影片中主要人物能否獲得觀眾認同便成為關鍵。“如果我們對影片中最人性的要素‘角色’不感興趣,我們就幾乎不會對整部影片感興趣”(13)[美]約瑟夫·M.博格斯,丹尼斯·W.皮特里.看電影的藝術[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322.。正是通過演員的表演得以塑造影片中的角色人物形象,或好或壞,或遭人同情,或遭人嫉恨。誠然,如上文所言,導演對于演員的表演有規范作用,但更多的是觀念性的,而非技術層面的。因此影片創作時,演員雖然處于與導演不斷磨合的過程之中,但仍然有著一定的美學發揮空間,甚至在有些時候,表演處于中心地位。
(一)現實主義表演為基礎
新聞事件改編的電影中,觀眾處于“先知”的上帝視角,而電影中的銀幕世界又與他們熟悉的現實生活相仿,由此觀影過程中的觀眾恰如窺視器,在觀影的同時也對影片中每一個熟悉的事物評定喜惡,劃分好壞。而電影表演藝術創作又必須是生活于最真實的人的現實生活之中的(14)張輝.電影表演美學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1:103.。因而新聞事件留有的影像素材可以成為演員表演的參照標準,與新聞事件中的原型人物進行交流也使演員有機會達到“同現實的密切的血肉聯系”(15)張輝.電影表演美學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1:104.。換言之,此類影片中演員的表演是在現實邏輯之下進行的,“演員應當對于那人人都會做的日常生活的動作,做得自然、簡潔、美觀”(16)洪深.電影戲劇表演術[M].北京:生活書店,1953:195.。為了達到如此意境,演員需要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回憶和現實感覺轉移到角色人物所處的情境中,結合自身的表演創作手法最終塑造電影中的角色人物。
《我不是藥神》中,扮演呂受益的王傳君為了演好片中角色,深入白血病患者病房體驗生活,其中一位患者在每日服藥后必吃橙子,因為他覺得橙子可以補充足夠的維生素。在影片中,王傳君保留了這一習慣,只是將橙子換為橘子,更符合一個沒錢看病卻又期望通過維生素補充換取一線生機的病人形象。這是演員依據現實中的原型人物對角色形象的塑造。而扮演劉思慧的譚卓則是花費一個月的時間苦練鋼管舞,正因為通過從內到外的投入與磨煉,最終使電影中的每個人物都傳遞出清晰的生活質感。《解救吾先生》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真實的情節、演員表演、臺詞等,其實它們都來自當年央視12套社會與法頻道《天網》欄目以及北京TV《法制進行時》中的“解救吳若甫”過程的跟拍紀錄視頻以及對于犯罪嫌疑人華子及其同伙的審訊采訪紀錄視頻。在《追兇者也》開拍前,劉燁花費近三個月時間學習云南話,盡管并未足夠標準。但在一些字音的后綴上盡量靠近云南話,找到一種方言的發音韻律,并融合在故事的情境里。正是因為影片中這些演員,在遵循現實主義表演美學的基本原則——“生活、自然、真實”的前提下進行的表演創作,才得以塑造影片中感動觀眾鮮活的人物形象。而消費語境下新聞改編電影中,角色的生活根源不只來自演員自身,還有新聞原型人物的觀照。也意味著,新聞改編電影中演員塑造藝術真實的角色人物所參照的是:演員的生活真實、新聞的原型真實和劇本的假定真實“三重真實”的融合。
(二)細節表演塑造角色性格
作為電影主要表現對象的人物形象,也推動著電影故事的發展。美國著名劇作理論家羅伯特·麥基曾對人物塑造進行歸納:“人物塑造是所有可觀察到的素質的總和,是一個使人物獨一無二的綜合體: 外表特征,加上行為舉止、語言和手勢風格、性別、年齡、智商、職業、個性、態度、價值觀、住在哪兒、住得怎樣。”(17)[美]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M].周鐵東,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441.
角色的性格塑造作為角色人物的情感物化體現,包含著演員外部動作再體現的角色外部性格化和演員內部心理再體驗的角色內部性格化兩部分。電影表演創作中,性格化塑造要求演員“根據角色淘洗和挑選內外部細節,并且自然而然地吸收和運用這些細節”(18)張輝.電影表演美學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1:221.,最終達到內外形神的一致。《親愛的》開場掃過曲折陰暗的小巷交代了故事發生的空間背景,而田文軍爬梯子上去,在一團亂麻的電話線中抽抽拽拽尋找自家的那根線,并吐出嚼過的口香糖粘在找到的電話線上做標記。這一段情節簡單的幾個動作把田文軍這個人物市井小民的身份和有點小聰明的人物特點都反映出來了。關于動作,洪深認為,對于角色來說,每個動作都是有來歷有理由的,“而對于那屬于某一職業或某一特別生活狀態的人的動作,平時即須隨處隨時觀察留意,而在有表演的必要時,更須扼要地抓住幾點,仿效得純熟、可信而‘內行’!”(19)洪深.電影戲劇表演術[M].北京:生活書店,1953:196.
此外,新聞通過敘述和描寫展開新聞事件和人物,其中的對話形式只能出現于采訪中,但在改編為電影后,對話除了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溝通、表達傳遞,還可以用來塑造形象、體現個性、推動劇情。“人的聲音比冷冰冰的白紙黑字更能顯示細微的差別”(20)姚曉濛.電影美學[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82.,由此,電影演員“怎么說”與既定的劇本對白“說什么”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為說話的音量、語氣以及與之相伴的表情所傳遞的信息,相較文字本身會更豐富。不只如此,影片中方言的運用進一步深化了人物所處的環境以及人物身份和性格特點。在感情表達上,方言具有普通話無所比擬的優勢,方言中有特定的語音、句式和語法結構,甚至有其特定的詞語表達,這種表達具有其所在地域的特定含義。普通話無法實現。《親愛的》中李紅琴情急之下脫口而出的“我們怎么不能把小家伙養好了”,“小家伙”這個詞在普通話中可表達多層含義,但趙薇用蕪湖方言表達,則具有一種地方特色的獨特韻味,同時也體現出趙薇對吉芳的疼愛以及作為一個鄉下農婦在情急之下無法仔細斟酌用詞的人物性格。
正如《我不是藥神》中的黃毛、《追兇者也》中的王友全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細節表演的角色性格塑造不僅使人物更真實,也賦予角色無法被人忘記的個性,以此增強影片的戲劇化效果。
(三)偶發的即興表演打破僵化
在當前的電影創作中,高強度的拍攝易使演員陷入機械和刻板,使不少演員的表演創作套路化、模式化。尤其在新聞改編電影中,故事發展和脈絡走向觀眾都較為熟悉,此時演員不可預知的即興創作不僅可以打破預先設計帶來的表演僵化,還可以帶來出其不意的戲劇性效果。《解救吾先生》的結尾,劉燁飾演的刑警隊長與兒子通話時,即興所說:“諾一,這么早起來了,對不起,爸爸實在是太忙了。”被大家稱為影片的彩蛋。當然,這種即興創作是有一定前提的,其一是植根于劇本字里行間的理解,其二是演員的想象。盡管原型人物及素材可作為演員的參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給演員的創作帶來局限。此時,足夠豐富的想象力可以促使演員創造出劇本中潛在的內容,不失為錦上添花之舉。《解救吾先生》在華子媽媽探監的一場戲中,華子撞向玻璃是演員王千源在拍攝時的即興創作,但這一動作將一個兒子對母親的愛和悔以及哀己不爭怒己不幸體現得淋漓盡致。盡管即興創作在有些時候會產生意外的驚喜,但在拍攝中也受到電影拍攝特點的制約,比如分鏡頭拍攝。因此,在電影表演創作中,即興創作只能是偶發行為。而演員期望通過即興創作達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就必然需要在把握角色內心感受的前提下,充分掌握和了解不同鏡頭所表達的層次變化。當然,即興創作只能錦上添花,新聞改編電影中的表演創作仍需以現實主義表演為基礎,以細節表演塑造角色性格為核心,才能創造鮮活動人的銀幕角色。
四、結 語
綜合分析消費語境下2013年來近五年的新聞改編電影,為了將眾人皆知的故事表達得出乎意料,導演的表演需求潛藏:故事化改編下選用明星演員做主演的市場訴求以及影片趨于真實表達的視聽語言運用。為了塑造“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銀幕人物形象,演員的表演創作是在演員生活真實、新聞原型真實和劇本角色真實為底色的現實主義表演基礎上,經由細節表演的性格化塑造和偶發的即興創作,力求銀幕人物形象更真實的同時,也加深了戲劇性表達的效果。消費語境下,受力于商業因素的新聞改編電影,所呈現的是在真實底色下深化戲劇表達的表演觀念。這也對演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然,始終在模仿、復制、畸變中找尋著最佳分寸和配比的電影表演創作,始終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