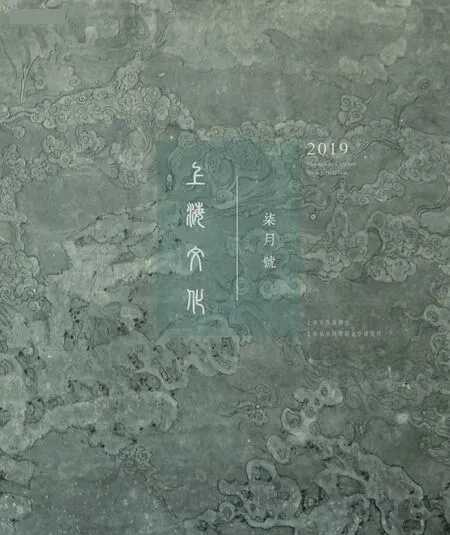四十年樽俎之間(一)
李慶西
周老師講《文心雕龍》,詮釋“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認識文學的發生和變異,是真正的文學啟蒙。
壓縮在記憶中的四十年很難還原當初的情景,抖落開來全是碎片。
1979年最清晰的記憶是饑餓感,食堂里永遠彌漫著爛菜葉子和陳化糧的餿味。可是晚上一過九點,藏起的兩塊苞米面餅子就讓人搜刮走了。中文系男生宿舍燈火通明。二班的曹詩人喊我去參加文學社活動,討論王蒙小說《夜的眼》。饑腸轆轆的意識流,代入精神的饑餓狀態。城市惺忪的燈光,黑暗中一雙雙饑渴的眼睛。民主與羊腿,魚與熊掌……
關于早年黑龍江大學的文學社團活動,我寫過一篇《社團風云》的回憶文章(見《書城》2008年7月號),記錄當時的一些情況。我們這些知青出身的77級都是揣著文學夢而來,詩與遠方卻并不只在夢里,更是現實的掙扎。系主任一再強調,中文系不培養作家(豈料如今中文系都在開辦創意寫作中心),我們文學社還是出了好幾個詩人和作家。成就最大的要算如今在美國的小說家哈金(本名金雪飛),他是英語系的,跨系加入我們文學社。寫詩的張曙光,日后成為重量級詩人。還有李龍云(已故),是專業劇作家。龍云未加入文學社,卻經常跟我們交流,大二時寫了話劇《有這樣一個小院》,在北京演出,文學社有我和張維功去觀摩。其代表作《小井胡同》至今是北京人藝保留劇目。
文學社聘請周艾若老師擔任顧問。周老師教文學理論,骨子里極富詩人氣質。由于文學,我們頻繁出入周老師家,去他那兒蹭飯。當初討論的話題早已忘得一干二凈,卻一直記得周老師家的番茄雞蛋面,還有窗邊巨大的龜背竹。傷痕文學幾乎伴隨著整個大學時代,一切皆于苦難中導出。粗頭亂服,簞食瓢飲,自有波西米亞范兒。延宕的青春開始躁動,扃閉的心靈終于從鐵屋子里奪路而出。周老師講《文心雕龍》,詮釋“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認識文學的發生和變異,是真正的文學啟蒙。
不光是社團,宿舍里八條漢子,每天都談論文學,扯開去又是飲食男女。風雨如晦,饑鳴不已,饑餓現實主義敘事不乏畫餅充饑的想象力。同屋尚剛以畫家李苦禪名字相調侃,笑我是“李苦饞”。時而亦有湊份子的宿舍聚餐,廉價紅燒貽貝罐頭+劣質白酒是標配,隔壁那屋喝酒只是路邊采幾把灰菜蘸大醬。那種白酒哈爾濱市面上都叫“工藝酒”,其實是工業配方生產的勾兌白酒,入口很嗆。畢業前尚剛同學準備報考中央工藝美院研究生,大伙戲謔地稱之“工藝酒”。那時候工藝美術史論還是冷門專業(豈料而今已成顯學),尚剛的志趣跟我不同,但我們很談得來。多年以后,他已是學科大佬,時常飛來飛去各處講學,來杭州就來我家喝酒,樽俎之間自然未能忘情四十年前的“工藝酒”。文學是性情,是酒是藥,是無邊界之國。“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我總是期盼他突然降臨。
大學畢業是1982年初,回到杭州在一家工廠做科室干事。那時大學生國家包分配,由不得個人挑肥揀瘦。系主任說的沒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大多數人分配去向果然跟文學無關。其實,文學跟哪一行都有關聯,那陣子全國人民都操心文學。
廠區廣播喇叭天天播放“妹妹找哥淚花流”,供銷科一位業務員拉我喝酒,跟我討論報告文學究竟是“報告”還是“文學”。人事科長提醒我,你們不要搞成錢守維和韓小強的關系,那是樣板戲《海港》里邊階級敵人腐蝕青年的例子。
我進廠就在人事科協助調查“經濟犯罪”案子,不曾想很快查到那個錢守維。那人報銷的餐飲發票有一大摞,不知后來怎么定性。轉過年我調到出版社,廠里來電話讓我回去領取四季度獎金,在財務科碰上錢守維,又被拉進飯館。他點了河蚌肉炒春筍,響油鱔絲(后來發現這道菜只有上海人做得好),從公文包里拿出半瓶洋河大曲,要兩個杯子。我有些不好意思,他說那些事情他都知道,不怪你。說起剛弄到一本好書,臉上掛著詭秘的笑容。一看是《十日談》,我說這書做知青時就看過。
這世界永遠是異次元。人與人并不只有階級斗爭。
你在廠里混得蠻好,做啥說走就走了?換作我,討飯也不去那種是非之地。他給我分析,文字一途如何風云莫測。老甲魚真是洞若觀火,若干年后想起那番酒后箴言,不由大為欽服。他說,王蒙是做領導的料兒,劉賓雁早晚要吃栽(杭州話栽跟頭的意思)。
每天都談論文學,扯開去又是飲食男女。風雨如晦,饑鳴不已,饑餓現實主義敘事不乏畫餅充饑的想象力
還在工廠時,我的大學畢業論文由《文學評論》作為頭條刊出,隨后又被《新華文摘》轉載。我能進入出版社,那篇論文起了關鍵作用。論文題為《關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卻是借著三國話題論證文學自身規律,那時我對《三國演義》談不上什么研究,真正研究三國敘事是許多年以后的事情。想到這一節,是因為它使我與文學界開始有了接觸。
調入浙江文藝出版社是1983年春天,第二年夏天去蘭州參加一個當代文學會議,會后轉道去了北京。那時我剛在《文學評論》發表了第二篇論文《文學的當代性及其審美思辨特點》。我給他們投稿,并不認識哪位編輯,到了北京就想去認識一下。在建國門內大街社科院大樓里找到他們的編輯部,沒想到人家對我這外省文青相當熱情,京中文化單位待人接物跟我們那兒大不一樣。聊到中午飯點,編輯部主任王信、副主任賀興安和理論組編輯王行之三人帶我去就餐。
那時候社科院大樓附近只有一家涮羊肉小館,因不便走遠就進去找了座位。我是第一次吃涮羊肉,顧不得天熱,吃得大汗淋漓。紫銅涮鍋嗤啦嗤啦地翻騰,水蒸氣里彌漫著炭火味,沒有空調的店堂整個兒籠罩在煙霧里,幾乎看不清對面人臉。王信說,倒是找對地方了,老北京人就好這一口。王行之詢問我新的寫作計劃,我說起當時評論界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文章套路,很想從審美意識角度厘清某些問題,他跟我討論了幾個要點,鼓勵我趕快寫。回去寫了《論文學批評的當代意識》一文,第二年也在他們那兒發了。餐后三位前輩搶著付賬,爭了半天結果是王信買單,王信說他工資高,他掏腰包,必須的。
那天,王行之跟我說,有個地方你應該去一下。第二天他帶我去了朝內大街166號,那是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辦公樓,當時剛剛獨立建制的三聯書店也在那樓里。老王帶我走上頂層閣樓,把我介紹給《讀書》編輯部的人,自己就走了。那天見到沈昌文、董秀玉、吳彬、趙麗雅那些讓人敬慕的出版人和編輯,也有幸窺見他們后臺運作的若干情形。《讀書》這份刊物我在大學里就每期必讀,以前覺得那是很遙遠的文化殿堂,現在我就坐在里邊喝咖啡。絕非想象中的富麗堂皇,辦公室顯得簡陋、寒傖,四周挨挨擠擠的柜櫥,桌上堆滿了稿件和校樣,地板上是一摞摞的書刊。這里跟《文學評論》風格迥異,談論的話題也不一樣,但有一點相同,就是讓造訪的陌生人一點都不感到拘束。中午編輯部請飯,帶我去了樓下的大食堂。老董讓幾個編輯分頭排隊和占座。食堂飯菜說不上如何美味,倒也吃得很開心,他們的真誠和熱情不僅是個人秉性和修養,似乎也是一種團隊傳統。
后來我就成了《讀書》的作者,再去北京沒少在他們那兒蹭飯。
德培將那些抱殘守缺的評論大腕數落一通,發出驚人的宣言:“他們那幫人撐不過三年,你們看著吧!”
1984年故事多多,去蘭州和北京之前認識了兩位上海青年評論家,程德培和吳亮。
那年7月,杭州文聯在建德舉辦李杭育小說討論會,打算請幾位省外的評論家,因為程德培寫過杭育的作品評論,他們首先想到了德培,結果德培又拽上吳亮。據說程德培以前是煙酒不沾的好青年,但會議最后那天晚上也破戒喝上了。招待所餐廳頓頓是當地出產的蘆筍,肉片蘆筍,平菇蘆筍,木耳蘆筍,清炒蘆筍乃至清湯蘆筍,從那以后見到蘆筍我就反胃。大學畢業后不再是以前餓死鬼樣,胃口是極好,口味亦與時俱進。整個國家經濟生活正迅速向好的方面發展,會議餐難道不能搞得像樣些?有人從外邊帶來一些魚干和鹵味,大家跑到招待所露臺上喝啤酒,聊著各種信息和動態。又聊創作的話題,林斤瀾的怪異,賈平凹的簡古風格,陳村的復沓敘述。會外閑聊有時比會上討論更精彩,話題轉向抨擊主流評論家們官話連篇的平庸與淺薄。德培嚷嚷啤酒沒了,操辦會務的老高馬上又搬來一箱。大家都意識到,那種以傳統現實主義為“政治正確”的評論準則絕對是一種窒礙。借著酒勁,德培將那些抱殘守缺的評論大腕數落一通,發出驚人的宣言:“他們那幫人撐不過三年,你們看著吧!”果真讓他說著了,不到兩年功夫評論界已是另一番天地。
這一年冬天,《上海文學》牽頭的“新時期文學創新座談會”在杭州舉行,杭州文聯和我所在的出版社是兩個合辦單位。后來許多參會者的回憶文章和訪談都稱之“杭州會議”,我寫過一篇《開會記》(刊于《書城》2009年10月號),也提到一些情形。記得參加會議有三十余人,有作家也有評論家,我跟大多數人是第一次見面。其中來自北京的是阿城、黃子平、季紅真、李陀、陳建功、鄭萬隆,上海是茹志鵑、李子云、周介人、徐俊西、張德林、陳村、吳亮、程德培、陳思和、許子東、蔡翔、肖元敏等,其他省市有韓少功(湖南)、南帆(福建)和魯樞元(河南);杭州市文聯是李杭育、徐孝魚、鐘高淵、高松年等,出版社僅我和黃育海二人。會議由茹志鵑、李子云和周介人輪流主持。會上討論的情況沒有記錄,因為拒絕媒體采訪,亦未作任何報道。事后阿城、韓少功、李杭育、鄭萬隆幾個寫了文章,呼吁重新認識傳統 / 民間文化的審美范式,以開拓創作視野,被認為是尋根派宣言。其實會議不只是醞釀了尋根思潮,對嶄露頭角的先鋒小說亦有足夠關注,記得有一天下午,集中討論了馬原尚未發表的《岡底斯的誘惑》。
會議租用陸軍療養院的兩幢小樓,過去是將官休養的住所,其時窳陋不堪,屋里連暖氣都沒有(那個冬天非常冷),會議餐食亦泛善可陳。杭州文聯盡地主之誼在“知味觀”請大家吃了一頓,《上海文學》又在“樓外樓”回請一次,那是當時杭州最有名的兩家飯館。“知味觀”那次,阿城談興甚濃,說話間不知喝了多少紹興花雕。那酒入口綿順,他喝的太快,像《水滸傳》說“吃得口滑”。筵席散后踉蹌奔出,扶著電線桿嘔吐。有人上去攙扶,他拽住人家說,“我告訴你,這酒有后勁,這酒坑人!”
杭州會議前一天,因會務安排我先去了上海,當晚《上海文學》宴請北京過來的那撥人,是在上海展覽館“西角亭”餐廳。我第一次走進那么氣派的餐廳,水晶吊燈晃得兩眼發愣。周介人叫我別拘束,我便大快朵頤,那兒的芥末鴨掌特別好。飯局開始前,王元化先生特意來看望大家,李子云向他逐一介紹在座的客人,像是領導接見的意思(王元化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他沒吃飯就走了。再過十年,我才有機會跟王先生共進晚餐。
1984年以后去上海的機會多了。文學的宴饗剛剛開席。走進巨鹿路675號院子,感到格外親切。上海作協機關和《收獲》、《上海文學》等著名文學刊物都在那座樓里,那是真正的作家之家。吳亮、程德培尚未調入作協,作協掌門人茹志鵑先生已是滿懷熱忱地關照他們。杭州會議之前,我收到吳亮一封信:
慶西兄:
剛剛接到茹志鵑一封信,她非常熱情地把我向江蘇人民出版社推薦了,據說他們對出我的作品表示“歡迎”,要我寄目錄去。
這樣我就有點犯難,不知如何處置。出版社情況種種我不甚了解,你的意見怎樣?我要請你為我來決定了。
南京我還沒有去信,等你的“手令”。
即頌
近好!
阿亮 [1984]11.5
吳亮信中說要等我“手令”,是因為在建德會議期間,我跟他和程德培談過約稿意向,希望能編輯出版他們的第一部評論集。只是出版社向來看重專著而輕視集子,況且領導鬧不清兩位年輕人有多少分量,說再等等看——“看他們發展情況再定”。吳亮多少有些要挾的意思:你那兒不要我就給江蘇了。因為之前跟他有約定,先跟我打招呼也算有信用。他信中附來茹先生手札,全文如下:
吳亮同志:
昨天江蘇人民出版社有同志來,我們向他推薦了你的作品,他很歡迎。可惜我們不知你的地址,否則立即就可給他,他今天已回南京。明天我也要去南京,但也無法帶去,只好你接信后自己寄了,寄:
南京 高云嶺 江蘇人民出版社文學編輯組 周行同志收即可。
祝好
茹志鵑 [1984]11.4
“新人文論”前后一共出了十七種,作者還有黃子平、陳平原、趙園、王富仁、藍棣之、劉納、季紅真、南帆、王曉明、李劼、蔡翔、殷國明等人。這是國內集中推出新時期文學批評與研究成果的第一套叢書
茹先生這封信正好是一個契機,我拿著信去找頭兒,我說不能再等了。總編看這情形,當即拍板。我馬上回復吳亮,千萬別給江蘇!從吳亮的《文學的選擇》、德培的《小說家的世界》這兩本書開始,我和黃育海形成了編纂出版“新人文論”叢書的思路。之前我們已經出了許子東的《郁達夫新論》(那是專題性著作),重印時亦納入這套書。“新人文論”前后一共出了十七種,作者還有黃子平、陳平原、趙園、王富仁、藍棣之、劉納、季紅真、南帆、王曉明、李劼、蔡翔、殷國明等人。這是國內集中推出新時期文學批評與研究成果的第一套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百家文論新著叢書”、上海文藝出版社“牛犢叢書”和“文藝探索書系”都在我們后邊才啟動。
前些日子,吳亮來我家喝酒。醉意朦朧中,說到三十五年前這樁事兒,他怎么也想不起來了。當然,如果不是留著他和茹先生這兩封信,怕是我也記不得當初的情形。從這事情上看,茹志鵑實是“新人文論”的強力推手。還有李子云、周介人,他們主持的《上海文學》是吳亮、德培最初的園地。想起前輩功德,不由感慨萬分。
1985年5月,《人民文學》在北京舉辦一個青年作者座談會,地點在廠橋的中直機關部招待所(今金臺飯店舊址)。我剛在該刊發了一個短篇,副主編崔道怡和小說組長王扶分別來信叫我去,說是王蒙也來。王蒙當時兼任《人民文學》主編,之前沒見過他。
那個會規模不大,有何立偉、扎西達娃、馬原、周梅森、劉索拉、徐星等十七八人。王蒙果然來了,還請來諶容、張潔給大家講了一堂。第一次見識王蒙口若懸河不逾矩的豐采,簡直驚羨,不由想起廠里錢守維那番話,果然是做領導的料兒。其實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日后的情形誰也沒法料想。
私下里,王扶跟我說,王蒙對我新寫的《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有些想法。她把王蒙的審稿箋給我看了,上邊密密麻麻地寫了許多。原以為他只是掛個主編名頭,沒想到真的看稿,還摳得很細,提了若干具體修改意見。我有些犯難,這跟我原來的思路相差太大。王扶說,要不你自己跟王蒙談一談?會議有一天安排大家游覽頤和園,在聽鸝館吃午飯。坐下來正好在王蒙邊上,上烤鴨的時候,王蒙教我怎么用荷葉餅裹住鴨肉再擱蔥絲……吃了幾口,我說起自己那篇稿子的想法。王蒙耐心聽著,最后放下筷子,只問了一句:“你確信這樣效果好?”見我自信滿滿地點頭,他也點頭了,“這烤鴨不錯,那就這樣發。”
許多年以后,大約是2009年夏天,我去青島海洋大學參加關于王蒙的一個討論會。那次的會議餐像是流水席,好幾次恰跟王蒙湊在一起。我說起當年聽鸝館餐桌上談稿子的事情,他想了想,“有這事么?”他說飯局上就怕人找他說事兒。
1985年冬天,韓少功、古華、凌宇他們邀集若干評論家和學者去湖南聚會。與會者有錢理群、吳福輝、趙園、雷達、黃子平、吳亮、許子東,我亦混跡其間。會議前三天在長沙,住在蓉園賓館,據說是從前毛澤東下榻之處。座談會與游覽節目穿插進行。愛晚亭邊討論歌德的“世界文學”,聽老錢從堂·吉訶德說到哈姆雷特。韓少功、蔣子丹帶大家去火宮殿吃臭豆腐,湖南臭豆腐是煮著吃,黑乎乎一大碗,我有些吃不慣(江浙做法是油煎或炒青毛豆)。但湖南菜很對我胃口,許多菜肴都是加豆豉干煸,干柴烈火般的過癮。
隨后去岳陽,那是古華的根據地。登岳陽樓,披襟臨風,憑欄遠眺,八百里洞庭奔來眼底。古華帶大家渡水到君山島,在島上吃飯。找一家漁民餐館,露天擺了兩桌,各種湖魚輪番端上,號稱“百魚宴”。其中有一種洞庭銀魚,味鮮肉剔。島上蒼蠅多,尋著飯菜香味都來了,圍著餐桌盤旋,就餐時須得一手挾筷子,一手趕蒼蠅。吃到半截,幾個女的扔下筷子不吃了,過了會兒男的也都撤了。人一走開,蒼蠅密密匝匝落下。可我還沒吃完,顧不得叮得滿頭滿臉,趕緊在沒落蠅子地方下箸。雷達說,就你貪吃,你看你這樣兒……
第三站是張家界,從長沙過去面包車走了十一個鐘頭。湘西,沈從文,長河與邊城,水畔的吊腳樓……一路崎嶇走入文學史記憶。車上蔣子丹、何立偉唱花鼓戲解悶,從《劉海砍樵》唱到《列寧在十月》,又用方言表演農村計劃生育段子。湖南人搞笑一流。凌宇是湘西人,翻山越嶺如履平地,爬金石寨把大家甩得遠遠的。另一日,一行十幾人沿金鞭溪逛悠,見一獵戶手里提著剛打的果子貍,凌宇說這玩意兒當地人叫“白面”,是山里珍物,便掏錢買下。在近處找了山洞里一家農戶搭伙,讓主人把“白面”剁碎燉了。連鍋端上來,大家撇了斯文相,坐地成了老饕。見許子東猛往自己碗里扒,吳亮急了,扔下筷子干脆用手抓來吃,黃子平笑稱“空手道”。
1980年代初,北京崇文門西大街開了一家名叫馬克西姆的法式餐廳,據說是當時北京最貴的飯館。有一次尚剛和我走過那兒,他說,“等咱有了錢,來這兒撮一頓!”如今尚爺是不差錢了,卻始終沒帶我去馬克西姆。
尚剛請飯喜歡在萃華樓和仿膳那種地方,還有美術館對面翠花胡同一家私人小館。大學畢業頭一兩年去北京,請我在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吃過,那時杭州沒有川菜館,頭一回領略川菜滋味覺得美妙無比。對了,那時候勁松有家叫豆花飯莊的川菜館,也相當不錯。吳彬和統一兄請我在那兒吃過幾次,有一回同時請了外國文學專家荒蕪先生。老先生翻譯過奧尼爾,抗戰時在重慶待過,喜歡川菜。夫妻肺片,大神布朗,座中不乏麻辣敘事。
后來每次去北京差不多都有《讀書》的飯局,有時是吳彬夫婦請吃。沈昌文沈公有一句名言:“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揚之水(趙麗雅)《讀書十年》后記專門提到這話,我也親耳聽老沈說過。翻翻揚之水那書,不少飯局都有我——
沈昌文沈公有一句名言:“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
1987年3月31日,中午編輯部一行外加李慶西、陳志紅、馮統一,到鴻云樓聚餐。來至樓下客堂,被告知滿座,請往樓上,方落座,忙問價,呵,一人二十五元標準,點數腰包,勉強夠得,雖知被狠敲了一筆,也不好再呼隆而撤,吃吧。計有海參、蝦仁、百葉、香酥雞等,最后一道是烤鴨。
10月17日,午間馮統一在豆花飯莊宴請黃克、李慶西、黃育海,并囑吳彬通知我們三人(王、賈)也去。辭未就,不忍也。
1988年5月10日,午間編輯部四人請李慶西在人人大酒樓吃飯。聞訊而來者趙越勝、周國平、老沈、范用、丁聰,一共十人。二樓,廣東風味。飯菜一般,唯飯后幾味甜點甚佳。
7月9日,午間《讀書》回請浙江文藝出版社的李慶西等三人,宴設人人大酒樓,王焱也受邀前來。賓以外,主四人:吳、楊加沈雙。共費三百零五元。計有清蒸活蝦、烤乳豬、紅燒排骨、玉粟羹等八款,并幾份茶點。
1989年1月7日,編輯部諸位碰面(未見賈),午飯于森隆飯莊,就餐者,吳、楊、沈外,還有李慶西。
1990年3月16日,午間吳方請李慶西、尚剛并《讀書》三人在全聚德(王府井)吃飯。冷菜四,熱菜六(炒蝦仁、拔絲蘋果等),烤鴨兩只。樓上單間雅座。
8月8日,午間請李慶西到東四的花園酒家吃飯,粵菜,清蒸活魚、咕咾肉、辣子鮮魷、牛腩煲、牛百葉、北菇蒸雞。只有魚還可吃。
……
在北京食烤鴨有許多次,以吳方那次最為愜意。冷盤是鴨肝、鴨胗、鴨掌等鴨什件,配著韭菜花、芥末等調料,精致而美味。那個門店的經理是吳方“發小”,安排很周到。不過,揚之水麗雅記錄也有未確處,如1987年10月16日一則就弄錯了是誰做東。其謂:
李慶西和黃育海來京組稿,趁便以浙江文藝出版社的名義請編輯部諸君吃飯。吳彬選了新近開張的“肯德基家鄉雞”。雖坐落在鬧市,但光顧者似不踴躍……樓下買好,端到樓上就餐。廳堂布置得頗有村舍風,樸質而雅潔。沒想到的便宜:六個人(三位東道并李陀、王焱、吳彬)一人一份“兩塊雞”,只花了四十二塊錢。不過這是最低規格的“份”,除兩塊雞外,另有一坨土豆泥,一格生菜,一個小圓面包。雖則簡單,但確能飽人,而且味道不錯,炸雞是極鮮嫩的。
其實,那回本來是吳彬請客。當時肯德基剛進入中國,在北京前門開了第一家門店。之前都不知美式快餐是怎么回事,吳彬想帶大家去見識一下。可是到了那兒被拒之門外,須憑外匯券才能消費,所以“光顧者似不踴躍”(現在人們都忘了,那時許多洋貨只能外匯券購買)。吳彬想到李陀有外匯券,馬上打電話把他喊來。結果那頓飯是李陀買單。結完賬,見他還剩一些外匯券,又敲他竹杠,帶大家去王府飯店酒吧喝酒喝咖啡。
說起王府飯店酒吧,之前沈昌文帶我去過,那回是大出洋相。身穿中式旗袍的小姐送來酒單,老沈讓我點,他自己要了咖啡。酒單全是英文,好歹記得黑方尊尼沃克的拼寫,指著那行洋字碼,卻不敢念。小姐不肯俯身看酒單,一連用英語問了幾遍。老沈拿過酒單一看,朗聲喊道:“Black Label!”小姐又問:“Ice?”這單詞我居然沒聽懂。小姐很有耐心,老沈卻煩了,扭頭說:“要加冰!”聽是中國話,小姐一臉悻悻。李陀請客那回,我不知道可用中國話點單了,囁嚅著用英語說Black Label,這回對方是一臉懵圈。
《上海文學》的飯局多半在南京西路的梅隴鎮,那是一家融入上海本幫風味的淮揚館子,內外裝折古色古香。有一次茹志鵑、李子云都在,好像很隆重。周介人把我叫去,席間說什么事情,現在一概想不起來,只記得有干燒明蝦、蟹粉蹄筋、開洋煮干絲……
從饑餓現實主義到美食浪漫主義并不很遙遠,那是狂飆突進的時代。那時我也常給《上海文學》寫稿,寫小說寫評論。
1980年代沒有“核心期刊”之說,同道中最看重三家刊物:《文學評論》、《讀書》和《上海文學》的評論版。我有幸成為這三家刊物的作者,首先是因為這些刊物都有一種兼容并包的文化氣度,亦得益于主事人和編輯們提攜后進的職業態度。在當日文壇上,李子云、周介人可謂“教父”級人物,他們也許不贊同你文章的觀點,但他們的意見無疑會讓你完善自己的論述,他們知道文學不會是某種意志的產物,江湖有江湖規則。
巨鹿路675號拐過街角不遠就是“紅房子”西菜館,周介人有時在那兒請飯。奶油烙蛤蜊、忌士烙蟹斗、葡國雞、菲力牛排。當年吃西餐有一種新鮮驚奇的感覺。甚至,吃西式快餐亦是一種時尚,《上海文學》有次搞活動,老周帶了一大幫人去延中漢堡包聚餐,不知誰還拍了我跟王安憶、史鐵生他們一起吃漢堡的照片。餐桌上喜歡聽老周聊天,在編輯部辦公室里他總是比較嚴肅。老周說,你那篇談新筆記小說的文章有點意思,新時期文學確實需要從各種不同角度去歸納和描述……老周循循善誘,總是鼓勵我。
李子云喜歡靜安賓館九樓餐廳,帶我去過幾次,記得有兩次吳亮也在。那是淮揚菜、川菜和本幫菜混搭路數,蟹粉獅子頭、煮干絲和麻婆豆腐都很不錯,白斬雞特別好。餐桌上聽李老師聊各地美食,聊前塵往事,聊上層動態。她說話挺有趣,在滬上生活既久,那口京片子略帶上海口音,卻又不似上海人說普通話,尤其字正腔圓地甩出幾個弄堂俚語,更是發噱。1950年代夏衍還在上海時,她做夏公秘書,對當年文藝界的事情很熟悉,也聽她講過夏公的許多事情。
在當日文壇上,李子云、周介人可謂“教父”級人物,他們也許不贊同你文章的觀點,但他們的意見無疑會讓你完善自己的論述,他們知道文學不會是某種意志的產物,江湖有江湖規則。
我大學畢業后,周艾若老師也離開了哈爾濱,調到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周老師是周揚的大公子,那時周揚已年邁,調周老師來是為了方便照顧。有一次在北京,我去看望他,他在外經貿大學教公共語文,離開文學教學崗位,言語間不無悵意。1985年,周老師終于又回歸本行,調入中國作協創辦的魯迅文學院,擔任教務長,其時唐因是院長。
魯迅文學院在北京東郊八里莊,我去過一次,那地方是雜亂的城鄉結合部,但文學院已初具規模,周老師帶我校內校外轉了一圈。見到作協創研室的何鎮邦,好像是調來魯院做專職教師。到了飯點,周老師讓伙房弄了幾個菜,拍黃瓜、炒合菜、京醬肉絲之類,還弄了一瓶二鍋頭。又叫來何鎮邦,一起在他辦公室里吃。周老師飲食不講究,吃什么都甘之如飴。他自己不喝酒,一個勁兒讓我喝。周老師說,文學院雖有早先作協文講所的底子,實是百廢待興,希望把我調來幫幫他(那時正式調動不易,京中許多文化部門會以借調方式先把人弄進來),我倒是想來北京,但又不愿做這種教學行政工作,沒多想就回絕了。周老師對文學院的長期發展有通盤考慮,也叫我幫他“出謀劃策”,二鍋頭喝得暈暈乎乎,我口無遮攔地扯了一通。他找出紙筆,竟認真地記下來。
王蒙的舞姿有些笨拙,竟也來了幾下新疆舞的閃肩動作。張承志在旁引吭高歌,大家合著樂拍咵咵咵地鼓掌
在北京,令人難忘的還有黃子平家宴。子平兄那時住北大勺園宿舍,一套兩居室住房布置得整潔而溫馨。1987年夏秋之際,我在北京電影制片廠修改一個劇本,沒少去子平那兒蹭飯。子平太太玫珊很會做菜,但給我印象至深不是別的,是一大盆拌蘿卜涼菜,用北京人稱之“心里美”的水蘿卜做的,不知用了什么調味汁,吃著特爽口。這道菜被大家用一位演講家名字命名,那人奢談心靈美,正合那蘿卜俗名。有一次人特別多,有錢理群、陳平原、夏曉虹、張鳴、査建英等人,一上來就風卷殘云,玫珊看情況不對,轉眼又端上一盆。
那年中秋節,我還在北影招待所,子平叫我去他家晚餐,那次還有蘇煒。餐后,大家一起去圓明園賞月,子平夫婦帶上了兒子阿力。蘇煒專門帶了兩頂簡易帳篷,在湖邊搭起來。月亮升起了,玫珊切開月餅,與大家分食。那月餅是玫珊的朋友從香港帶來,特別好吃。
蘇煒那時單身,住雙榆樹青年公寓,他那兒是文藝雅痞聚集的地兒,去過幾次都是一大幫人。蘇煒自己不開伙,他那兒沒有飯食,只有洋酒和咖啡。我不喝咖啡,喝他的杜松子酒。他從美國回來時帶了不少CD唱片,我還未見過這玩意兒,頗覺新奇。聽百老匯音樂劇Cats,覺得凄厲而迷人,讓他給我轉錄到磁帶上帶回杭州。蘇煒介紹認識了林培瑞,林是研究中國舊小說的美國人,中文說的不錯,對鴛蝴派自有見地。我問他為何不研究中國當下的文學,他說當下的許多事情他看不懂。
在北影招待所那幾個月,中午吃食堂,晚飯常被梁曉聲叫去家里。梁曉聲就住北影廠宿舍,那時他是北影編劇。曉聲家晚餐通常喝粥,為招待我總會炒幾個菜,喝點小酒。喝酒時說起拍電影的事情,我很好奇,想讓曉聲帶我去攝影棚瞧瞧,竄演個路人甲匪兵乙之類。他一本正經地說,那種角色也不是人人都能演的。燈光一打,軌道車嘎嘎嘎一響,鏡頭前你不慌神才怪。
有一天,曉聲帶我去參加張承志長篇小說《金牧場》發布會,地點在北影廠附近的雙秀公園。那實際上是一個Party,長條桌上擺了好多食品和飲料。除了文學同道,張承志還邀來一些穆斯林朋友,現場用炭火烤著羊肉串,有的打著手鼓跳舞。王蒙來了,還帶來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大家注意力一下子都被身著白色長裙的包柏漪吸引過去了。這包女士是華裔作家,還是舞蹈家出身。聽到器樂聲,她便在天井里翩翩起舞,拽著王蒙一起跳。王蒙的舞姿有些笨拙,竟也來了幾下新疆舞的閃肩動作。張承志在旁引吭高歌,大家合著樂拍咵咵咵地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