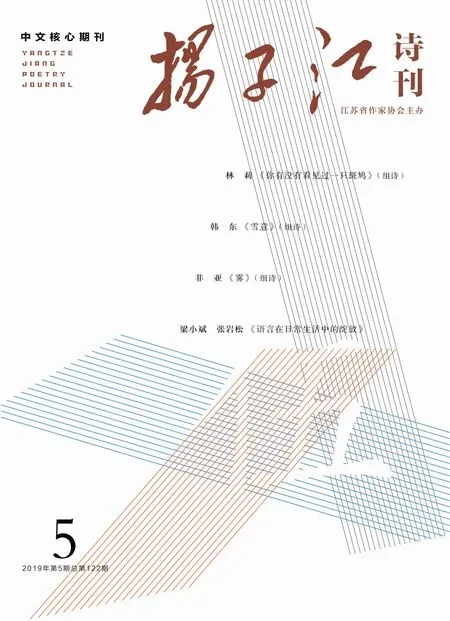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綻放
2019-11-12 14:19:12梁小斌張巖松
揚子江詩刊 2019年5期
梁小斌 張巖松
張巖松:
小斌兄好,我們相識近四十年了,你是朦朧詩人,當時給我的直觀感覺是,你的詩歌對生活,特別是對情感的描畫,以及情感遇到阻隔以后狀態的表達是非常出色的。當時翻看《詩刊》時,你的詩句,我第一次見到,也特別觸動了我。你從1984年開始告別優雅的創作,你是怎么達到這種轉換的呢?而且你當時寫下了《斷裂》。記得在你寫完《斷裂》以后,我們倆去了一趟北京,跟吳思敬先生探討了一下關于詩歌形式的走向問題。可以說,你的詩歌從溢美的方向走向生活的方向,或者是走向生活反思的方向。你能談談當時的情景嗎?梁小斌:
我所遭遇的生活我一般都喜歡對它進行一定的思考。我在想,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命名”。最初寫作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周圍布滿很多有名稱的事物。一個事物不論是我對它存在著好感還是惡感,不論我是否想深入下去還是逃避下去,那個事物都有一個名稱,那個名稱我們已經司空見慣,比如蘋果。道理是一樣的,我把我所遭遇的生活,簡單地把它歸納為幾個名詞之后,我就深入地想,我與這些名詞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一個關系?大家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事物的本來規律。所謂詩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我面對的這么一個世界,我是想和它打成一片,還是我對它有所疑問。張巖松:
從《斷裂》之后,你轉向了隨筆創作。在1986年,我個人寫作也有一個巨大的分水嶺。詩不是憑空想象,而是遭遇,詩意灑在普通人的身上。換句話說,對事物的這種看法造就了詩歌從抒情性轉向了事項性,轉向了日常性,轉向了周圍生活,我們用腳、用手、用梳子、用牙刷,都能觸及的詩。我想聽你談談,你從1986年開始轉向隨筆寫作,所感受到的是怎樣的一種狀態。梁小斌:
你講得很對,也講得很準確。我們一開始大致都有一個比較流暢的人生。就像當年我對少女的崇拜一樣,少女在我心目中有一個引吭高歌的優美形象,但是有一個少女,在車廂里吃橘子,那樣的一些情態,是我寫詩以來第一次注意到的。一個女孩子,她把橘核排在茶幾上,百無聊賴時的這個動作,我初次感到真能刻畫她的情態。簡單講,流暢的引吭高歌的人生,在仔細觀察的時候,卻發現了被忽略掉的動作和情態。比如說為了避免打攪家里人的休息,我們總是靜悄悄地吃著夜餐,這個時候,要讓這個世界顯得靜悄悄的,是我們所有人都要注意的事項,甚至是追求的目標。在一個已經萬籟俱靜的時刻,你要想沒有聲音,是不可能發生的。于是,在你敲碎雞蛋時如果雷聲大作,雷聲就幫了大忙,使你敲碎雞蛋的聲音隱藏在轟隆隆的雷聲中。張巖松:
日常性,它代表的是一種我們的生活和詩相碰撞,或者是相融合時的那么一種瞬間的感覺。把日常性送到一個祭臺上,被當代詩人崇拜的時候,這種所謂知識分子之外的寫作,是不是一種新的日常崇拜?梁小斌:
日常生活,就像一個汪洋大海,日常生活寫作對于某些重大題材的寫作來說,也許是一個輕輕的反駁。日常寫作方式,在它初出茅廬的時候,顯然對推動新事物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示范作用。但是,我們現在也要防止日常性寫作中的日常語言的泛濫。張巖松:
實際上已經是泛濫了。梁小斌:
口語化寫作的泛濫,是詩歌發展的一個正常的規律。就像一個家里面的物品擺設過于沉悶、過于繁雜,需要清減一樣,詩歌的語言可能在慢慢地走向一個由繁至簡的這么一個過程。但是至今,由繁至簡,這個“簡”的語言,究竟是指什么,詩人沒有找到。張巖松:
我是這么看,關于口語,我并不反對;寫得復雜,我也不反對。我認為詩,就是這么一個東西,當你跟它相遇的時候,我們采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捕捉到它?有一種詩是生活本身包含的,比如這把椅子上所含的詩;另一種詩呢,就是我們改造以后,經過語言的迂回所要到達的詩。就椅子而言,它的過去是什么樣子?現在和未來是什么樣子?我們擁有一雙眼睛,我們要感謝它讓我們看到很多事物,我們要感謝給我們眼睛的人,我們要感謝想象未來所要到達的詩意的東西。這個世界,有一種想象力所造就的詩意,它并不在現實中存在,但是在未來呼喚著我。還有一種就是,我們所見到的很多簡單的東西,比如墻壁上的涂鴉,詩人把這些普通的人情、人性組合起來,朝著詩的感覺去分行處理。梁小斌:
就像巖松剛才所說的,當我的眼光注視著一把椅子的時候,就試圖對這把椅子進行描述,這把椅子是如何破爛或者是如何富麗堂皇,我如何偎依在這把椅子上,這樣的一種繁瑣式的描寫,曾經有效果,現在這種有效性呢,正在慢慢減弱。在從前的寫作中,關于一把椅子的繁瑣描寫,的確具有一定的語言示范作用。世界是由多少事物構成的呢?我們可以排列出一萬個名詞,如果某個名詞開天辟地第一次在詩歌里面出現,我們認為,這不是繁瑣。我清晰地記得惠特曼,在表現人的時候,把人的五臟器官、骨頭的名稱全部寫了個遍,當時我初讀起來就感到震撼,感到這個世界被惠特曼描寫得如此豐富。這種繁瑣式的描寫,在文學史上的確起到了示范作用,哪怕我沒有見過什么新事物,但是有100個關于這個事物的名詞已經涌到我的腦海里去了。我們發現,現在所遇到的這個世界,首先蛻變成各式各樣的詞匯,各種各樣的形態,向我們鋪天蓋地地涌過來。這有助于表現人的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并且獲得博大的情懷。顯然,在開始狀態,它是必要的,問題是在這個浩如煙海的、各種名詞堆積的事物面前,詩人應該有所作為。張巖松:
現在的作品是金斯伯格式的或者是凱魯亞克《在路上》式的。金斯伯格式的那種,仍然是物體,仍然是堆積,但是有一種拒絕,有一種過濾以后的味道。我剛剛講的這些,是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的看法。中國新詩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詩歌中出現了后現代性。我是從2000年之后重新回來寫作的。詩歌中的人和我們生活中的人產生了怎樣的距離?以前我們認為詩歌中的人是一種美學的人,而生活中的人是不那么完美的,或者是不那么圓滿的人,是比較丑陋的人。那么詩歌是如何把真實的大部分人,沒有什么文學價值的人,他們身上所蘊含的詩意表達出來的?這就是我一直在進行的主要創作內容,不知道你怎么看?梁小斌:
當然所謂詩意不可能只是詩人的專利品,詩歌在我們日常工作中,時常發生,但對于大部分人來說,沒有產生回響,沒有產生效應。張巖松:
語言是中性的,詩人采用的方式是體會這個世界微弱的光亮,或者微弱的溫暖,這種微弱的感覺,是詩人需要發現的普通人身上所蘊含的詩意。大部分人都在為生活奔波,他們沒有考慮過詩。他們只知道生活不易,要去奮斗,要去養家,要去體面地生活。詩人在干什么?詩人看到他們的奔忙而產生語言的發散。梁小斌:
日常的對話,比如說年輕人的對話、群體中的對話、餐桌上的對話,所有這些對話你來一句,我來一句,為什么能夠繼續說下去呢?這里面有能夠吸引他的語言,這種語言雖然還沒有達到詩的高度,但的確和詩性無限接近。詩句肯定不是詩人首先說出來的,而是從我們日常生活的對話中蹦出來的。區別在于什么呢?詩人善于研究語言在這種日常生活中的綻放并把它記錄下來,而平常人卻忘記了,如此而已。張巖松:
目前我們面對著兩種詩的感覺,一種是濃郁的詩歌感覺,一種是沖淡的詩歌感覺。梁小斌:
千真萬確啊,詩歌是一個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會寫詩的人把它記錄下來。我舉個例子,我點蚊香,因為天氣潮,蚊香老是滅,我就盯著這個蚊香,長時間地盯著,這么一個盯蚊香的舉動,恐怕人人都能碰到。如果你想守衛著蚊香,好吧,那么把被子枕頭給你,就在那準備著長時間地守衛著蚊香吧,這種守衛著蚊香的舉動跟守衛著燈塔的意思也差不多,只不過是在守衛著一個渺小的事物。這就是說,詩,它是已經發生過了,只不過詩人善于把它記錄下來而已。我們在雪地里抓起一把雪嘗嘗,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不會讓人記下來,但把手伸到窗外抓雪吃這個舉動,讓人記住了。這的確能夠反映出一個詩性的眼光怎么看待這個事情。張巖松:
這段講得特別精彩,藝術家創作的時候,他的確看見生活本真的東西,然后進行某種詩性的操作。但有的時候,我們的生活還在,詩卻不在了,人所面臨的越來越渺小的那么一種詩意的表達,就顯得非常地晃蕩,這種晃蕩的感覺,別說接近于詩了,連接近生活的一個邊緣都夠不到!梁小斌:
巖松,你試著想象一下你自己的一些舉動。比如你出門以后停下來,買點咸鴨蛋回去給孩子吃。在詩人巖松的心中,肯定有一個孩子在他背包里尋找咸鴨蛋,那個片刻他在看著孩子,帶著一種欣喜和平靜,對孩子尋找咸鴨蛋的這個舉動肯定有所眷戀。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詩性。這種詩性繼續往下發展,孩子可能找不到鴨蛋,一下子嚎啕大哭起來。巖松肯定也有這樣的經歷,總希望孩子既能找到,又能夠在他包里亂翻時的那么一種專注神情,他在旁邊看著,內心涌動著一種父愛。在這里面就產生了我們行為的片刻猶豫,這一刻要牢牢抓住,我到底是把咸鴨蛋放在背包的表層還是放在背包的底層呢?我覺得這就是詩性的一種重大決策。這種猶豫,有時候需要三秒鐘,有時候需要花的時間很長。遇到這種場景,其實我們每個人已經回想了,但是筆下沒有注意。猜你喜歡
金橋(2022年7期)2022-07-22 08:33:14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少年博覽·小學高年級(2016年12期)2017-01-16 12:48:35
中國三峽(2016年6期)2017-01-15 13:59:16
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4期)2016-12-01 03:59:30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