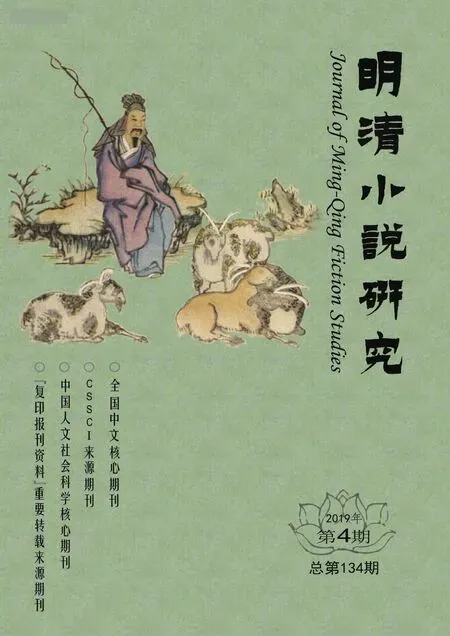詩學正義與《七劍十三俠》的敘事倫理?
·張 弛·
內容提要 《七劍十三俠》作為清末劍俠小說的集大成者,在繼承古代武俠敘事傳統的同時,對后世武俠小說創作亦有較大影響。本文將從小說詩學化、浪漫化的“正義”書寫方式,以及對劍俠形象群體的聚焦和個體英雄的虛化處理出發,探討其如何走向了一種宏大、主流、肯定性的大敘事,從而逐漸消弭了武俠傳統當中與廟堂秩序相對的批判性張力,呈現出倫理視角下中國武俠文化的精神癥候。
《七劍十三俠》是唐蕓洲創作于清代光緒年間的武俠小說,全書共三集一百八十回,分別刊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集刊行)、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二、三集陸續刊行),寫明正德年間徐鳴皋為首的江湖英雄,得“七子十三生”一眾劍俠幫助,隨御使王守仁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的故事。小說憑借著對奇幻劍術的精彩描寫、對逍遙劍俠的形象塑造,以及氣勢磅礴、虛實相生的小說結構,在晚清重新盛行的劍俠小說當中占有一席之地,接續唐傳奇《虬髯客傳》《聶隱娘》所開啟劍俠系列傳統的同時,被認為進一步促成了民國《蜀山劍俠傳》一類新武俠作品的產生。江文蒲在其初集序中稱其為“集歷來劍俠之大觀,稗官之翹楚也”,使文人讀者有“神乎其技之感,嘆為觀止”,將清代的武俠敘事又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對20世紀還珠樓主、梁羽生等人的“新武俠小說”有著直接的影響。
然而,在另一方面,《七劍十三俠》也為人所詬病,不單是其略顯粗糙的藝術質感和通篇彌漫的荒誕神秘色彩,在清代武俠小說當中一度被視為末流,“體現了清末俠義小說開始走向沒落的趨勢”;更在于,從小說敘事層面而言,這本融合了武俠、神怪、公案、講史等諸多元素的劍俠作品,卻在紛繁奇詭的劍術呈現過程中,逐步融入了晚清俠義小說已經普遍存在的倫理視角,于虛擬正義的背后消弭了“俠”的精神內涵,武俠小說傳統所構建的廟堂與江湖、權力中樞和市井世界、詩文正統與小說亞文化之間的張力,在作者刻意為之的敘述架構中消失殆盡。本文期望通過對《七劍十三俠》小說敘事的研究,探索其如何沿著清末武俠小說的發展,愈發趨向主流文化的大敘事,并呈現出倫理視角下中國武俠小說及其文化的精神癥候。
一、詩學化的“正義”書寫
“俠”在古代中國文化語境中,經歷了一個由違法亂紀、好勇斗狠,到肩擔道義、救世濟民的形象轉變過程,并逐步向主流社會關于“正義”的想象趨近靠攏。無論是《韓非子·五蠹》中關于“俠以武犯禁”的界定,還是《史記·游俠列傳》中對于其行為“不軌于正義”的評價,“俠”的行事和價值選擇,始終游離于主流社會秩序之外,縱然有太史公筆下為知己者而死的游俠、門客,但或是作為閭巷布衣,行走法外,或是作為卿相養士,任其私昵,與后世兼濟天下、懲惡揚善的俠客認知有著一定距離。直到唐代社會尚武任俠之風盛行,詩文、傳奇作品中劍客形象的大量出現,“俠”作為一種文化符號開始被主流社會所接納、頌揚,并開始與追求公平正義的主題聯系起來,李德裕在《豪俠論》中提出“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將“俠”與“義”作為二位一體、相互依存的一組并列,《昆侖奴》《荊十三俠》等傳奇中俠客開始扶弱濟貧、救人于水火,代表了當時武俠作品中以武正道、匡扶正義的愿景。
到了晚清時期,官場吏治的腐敗,司法獄政的黑暗,促使了武俠小說以另一種新的敘事模式出現了繁榮,即武俠小說與公案小說的合流,《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等小說中俠客進入到官府,協助清官斷案,成為用更加復雜的敘事格局、更加多元的俠義形態來描摹正義的典型,王德威稱之為對“詩學正義”的探究,即“敘事序列中一種想象的部署,當這一文學部署與想當然的‘正義’觀攜手并肩時,作者及讀者的意愿便得以在紙上實現”。在明代,以《包龍圖判百家公案》《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為代表的公案小說中,還存在大篇幅抄錄判詞、狀詞、卷宗的現象,具有濃厚的說法氣息和理性色彩,而晚清時期俠義與公案小說的合流,則開始將故事性和浪漫的俠義精神注入到對于“正義”的言說當中來,在俠義敘事中協助以包拯、施仕倫為代表的清官完成對于正邪善惡的快意恩仇。而在晚清時期以《七劍十三俠》《劍俠奇中奇全傳》《仙俠五花劍》等為代表的劍客、仙俠小說當中,此種由文學敘事序列,所展開的“正義”實施過程,無疑在基于司法、訴訟的武俠公案小說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如果說俠義、公案小說的合流是對于之前公案題材正義實現的一種補充,那么《七劍十三俠》等仙劍小說為代表的“正義”實施,則開始拋開現存秩序,以一種超現實、詩學化的方式,獨立承擔起有關正義的想象和部署。公案小說尚存一息的體制空間和法理訴求,在佞臣當道、清官失勢的現實中受到了阻隔,《七劍十三俠》中,權臣與強盜串連勾結、如兄若弟,讓實施正義的“清官模式”徹底失效,被譽為有經天緯地才能、不攀附奸黨的王守仁,遭到誣陷后流落江湖中,遇見徐鳴皋一行俠客,只能哀嘆自身難保,使得英雄無用武之處。小說中寫道:
王守仁說起目今宦寺專權,奸臣當道,英雄豪杰不知埋沒了多少。這班位高爵重的都是庸流,只知阿附權閹,深為浩嘆。我看公等皆是當世英雄,只可惜無進身之地。大家嘆惜了一會。
在俠義公案小說中成為某種定式的敘事模式:“江湖人士”向廟堂靠攏,作為輔助人員,協同官員伸張正義,這樣的情節設置,發生了倒置。《三俠五義》中,清官包拯以其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吸納甚至招安原本并不服從管束的俠客。小說中,包拯是“正義”理念的象征和實施主體,而圍繞其身邊的俠客則更多只是實現正義部署的工具:原本在土龍崗扎寨落草、具有情感個性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兄弟,在成為開封府四大侍衛之后,變為了鞍前馬后、站堂開道的程式化、工具化形象;“南俠”展昭在小說中最為精彩一段劍術展示,并非行俠仗義的過程,而是隨包拯在耀武樓的丹墀上為圣上舞劍,并由此收獲“御貓”之名;即使是五義中最具個性魅力的俠客白玉堂,也經歷了從叛逆到被馴服、屈膝匍匐口呼“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條,懇祈相爺筆下超生”的轉變過程。而到了《七劍十三俠》這里,王守仁失意出京,舟至錢塘,幾為奸人所害,被徐鳴皋、一枝梅等兄弟救起,全無主持公義、扭轉乾坤之力,更勿論他意欲招進江湖俠客,得到的是徐鳴皋“天生野性,難就拘束”的回答;在平定寧王叛亂過程中,本為這場歷史主角的元帥王守仁形象卻如同包拯身邊的侍衛俠客一樣,經過了淡化處理,正義的主體變成了智勇雙全、武藝出神入化的一眾劍仙俠客。
這種敘事安排恰恰對應了小說在開頭所做出的關于“正義”的預想部署,作者開篇稱,世上有三種極惡之人:貪官污吏、勢惡土豪、假仁假義。這三種極惡之人,朝廷內有奸臣照應,地方與官吏勾結,王法都治他不得,“幸虧有那異人俠士劍客之流去收拾他。這班劍客俠士,來去不定,出沒無跡,吃飽了自己的飯,專替別人家干事:或代人報仇,或劫富濟貧,或誅奸除暴,或鋤惡扶良”。小說中劍俠平定暴亂、鏟除邪惡的本事,已遠遠超出了唐代《虬髯客》《聶隱娘》《昆侖奴》等傳奇作品中的劍士俠客;而較之同時期武俠公案中樸刀棒棍、飛檐走壁等尚不脫離現實基礎的招式,他們口含寶劍、上天入地,被賦予了更多神化一般的超現實特征。《七劍十三俠》中寫到徐鳴皋的師傅海鷗子為代表的七位劍客道友,背掛寶劍、手執拂塵,似孤云野鶴,能御風而行,既有高超武藝法術、行俠仗義,又云游四海、不受管束。無論是作為劍客的精湛劍術、奇幻道法,還是作為仙俠的遁形匿跡、無處可尋,其作為“俠”的傳奇性、自由度和美學魅力都得到了充分肯定,這無疑比被招納馴服、作為清官侍從護衛的俠客要更加具有詩學色彩。小說第六十九回,寫到十三生施展劍術大破迷魂陣,其精彩絕倫、變幻莫測,竟然引得雙方兵士駐足欣賞,儼然一場劍術表演:
三枝劍又化出九枝劍來,共是十二枝劍,抵住十二道白光,空中交斗,忽如群龍戲海,忽如眾虎爭鋒,忽如一陣蒼鷹擊于殿上,忽如兩山猛獸奔向巖前。寧王此時同了軍師李自然登高觀看,看得稱奇喝彩,忘了戰陣交斗,如觀戲一般。鄴天慶手下一班將士并城上守城的兵士,沒有不喝彩的。
正如劉若愚在《中國之俠》一書中指出的,作為武俠小說的分支,這些飛仙劍俠的小說,與西方騎士傳奇有著幾分類似,“都脫離了當代現實,提供了逃避現實的仙境”。雖然唐蕓洲有關仙劍避世隱居的仙境描寫不多,但“正義”的實施過程和現實場景,得到了空前的傳奇化、浪漫化、美學化以及詩意化處理,在《七劍十三俠》《仙俠五花劍》等仙俠作品中,《史記·刺客列傳》當中行刺失敗、而為人嘆息“惜哉不講于劍之術”的慷慨悲壯不復出現,《水滸傳》中英雄好漢嗜血殺人的殘酷場面,也大大被收斂和弱化。盡管善惡依然對立分明,唐蕓洲也會效仿《水滸傳》設置“三上金山”“三探寧王府”“擺惡陣妖道逞能”“仗邪術非幻敗王師”之類的情節,來增加懸念,但關于正邪雙方之間爭奪打斗的描寫,因為來自江湖的這種超現實能力,多了自如逍遙的浪漫成分,少了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息,無需早期史傳作品中充滿兇險的近身搏斗、招式比拼,更不需要公案題材中訴訟情節與法理邏輯上的費心思量,“俠”通過這套詩學的包裝,超越了普通拳法兵器和現實清官模式,在審美過程中極大滿足了清末市民讀者有關“正義”的想象訴求。
二、英雄形象的群體聚焦與個體虛化



《七劍十三俠》筆下的綠林好漢、英雄人物群像,從江湖人物的個性層面來講,較之《水滸傳》《三俠五義》而言,則更加徒有其表,缺少神韻。如果說同為清代創作的《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武俠小說,在眾多英雄譜系里還有對于十三妹、白玉堂這類獨立完整的人物塑造,那么《七劍十三俠》小說中“綴段性”的單個人物亮相,在第四十五回“安義山主仆重逢,梅村道弟兄齊會”便匆匆完結,在后一百余回的情節中,眾位英雄進入到結拜聚義、安邦平亂的共同征程,匯聚成了一個龐大、詩化的正義群體,個體的差異性格、獨立價值被湮沒其中。即使是小說前半部分諸回,人物各自的發展,也只是數位英雄組成的小群體,在打擂臺、斬惡醫、除奸淫的過程中,完成著對小說“平叛亂”這一敘事主線的鋪墊,英雄個人的命運、性格乃至面貌、武藝特性,皆未能得以充分施展和描畫。以“七子十三生”為代表的劍客、仙俠人物,最終呈現在大而化之的正義群像里,并非作為一個個特征鮮明的形象類型為讀者所感知;英雄自我的情感意識和個性形象,則湮沒在這種眾多的、奇幻的群像中,黯淡無光。小說發展到后半部分,“七子十三生”逐步成為了正義陣營中的統一代名詞,單個人物的描摹幾乎匿跡,連珠式的名稱羅列成為小說描寫的常態,造成了一種浩蕩磅礴的凜然氣勢,例如:

這種英雄形象的總體聚焦凸顯和單個虛化模糊,不只是其形象在龐雜的江湖群體和絢麗的招式法術背后,逐漸模糊了每位英雄外部形象的特征差異,更在于長久以來武俠作品中生長的關于英雄的兩大精神內核主題——作為“俠客”的獨立意志與作為“兒女”的愛欲性情,在小說塑造的形象個體中逐漸衰微,詩學化的“正義”書寫和英雄群體的聚焦背后,單個劍仙、俠客的獨立性并沒有得到凸顯,反而成為了虛空化、被剝離了個性精神的強悍肉身和飄逸仙體。



三、走向大敘事的俠義倫理



小說作為小道,原無詩文、史傳作品中“載道”“言志”的負累,與市民社會接近,生氣淋漓,更具有民間亞文化、個人化敘述的特點,俠義作品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對于主流倫理、社會秩序的一種“否定性敘事”——對社會公平正義借以現實權力及其規則運行不能實現的不滿。而這其中,以仗劍行俠、修煉求道為主體的劍客、劍仙小說,更帶有個人性的遁世、隱逸色彩,并含有對于儒家治國平天下、忠君愛國等公共倫理的反諷意味,清代《女仙外史》《綠野仙蹤》等小說中,將劍術與道家煉丹術結合,把從唐宋開始的江湖世界推向了一個高峰,其帶有志怪小說氣質的神秘色彩,更是與注重現實秩序的史官傳統、倫理價值相悖離。《七劍十三俠》等清末仙俠作品,同樣繼承了這樣的情節設置,也出現了關于個人劍術道行修煉的討論,以及斬殺山精野獸、怪物妖人的內容,但其正義實施的過程走向,最終還是進入到類似講史文字的大敘事,使忠孝節義的家國倫理彌漫其中。
《七劍十三俠》當中,具有濃烈民間氣息的“私情”與“怪狀”被視為陳腐頹靡,遭遇了來自倫理視角的過濾,“俠腸義膽”的正義實施則與廉頑立懦的德行操守激勵聯系在一起,而這種激勵并非觀念的直白說教,而是在武俠敘事的序列中逐步展開。整部小說,江湖世界中個人的品性、操行乃至武藝修為,都被與古代社會主流的“忠孝節義”道德捆綁起來,國家、廟堂之上的公共化倫理作為最終的“能指”,確認著江湖人士個人作為“俠”的境界高低。在高度虛幻、神秘、具有美學色彩的劍術技藝展現中,也經過了倫理化的處理,小說中,同是作為道人,謀逆作亂的“反賊”與勤王平叛的“義士”,二者之間的招式對比便具有差異,寧王府中的人物非幻道人,所使武術技藝,多是借助妖風、鬼火、迷魂陣等邪術,而徐鳴皋、一塵子為首的劍仙,多使具有正義象征色彩的寶劍,或用劍招,或幻化成劍氣鏟奸除惡,到了小說后半部分協助王守仁平定叛亂時,更不只局限于作為帳下武夫、供人驅使,還可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在模糊了江湖俠士形象特征的同時,顯露了儒臣匡濟天下、澄清宇內的道德理想色彩。



結 語
無論是浪漫化的“正義”書寫方式,宏大龐雜的俠客群像塑造,還是最終與主流倫理相連接的俠義觀念,《七劍十三俠》都將傳統的武俠敘事推向了一個高峰。但是這種臻于高峰、完美的敘事背后,卻也呈現出古代俠義倫理發展衍變過程中的趨勢,個人的獨立性和江湖世界的批判功能并沒有得到凸顯,透過敘事序列當中忠君、貞潔等一系列倫理表達,傳統武俠敘事在接受與反抗權力機器之間的張力、個人情欲和家國意識之間的矛盾逐步走向了消彌,最終整合為一種公共化的大敘事。而從晚清新小說中倡導尚武任俠的革命精英,到民國以后陶醉于刀槍劍影的市民群體,再到金庸關于“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意識形態化界定,在將傳統武俠倫理與現代小說觀念融合的同時,這種典型的精神癥候和倫理意識,依舊時常可見,彌漫在各類關于俠義的新型敘事作品當中。
注釋:
① [清]聽珊江文蒲《初集·序》,《中國近代小說大系·七劍十三俠 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
② 南懷瑾《亦新亦舊的一代》,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
③ 梁軍《以奇制勝 意趣深厚——〈七劍十三俠〉的思想與藝術》,《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第1期。
④ [唐]李德裕《豪俠論》,《全唐文新編》第12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50頁。
⑤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⑦ [清]石玉昆《三俠五義》,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頁。
⑩ [美]劉若愚著,周清霖、唐發鐃譯《中國之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