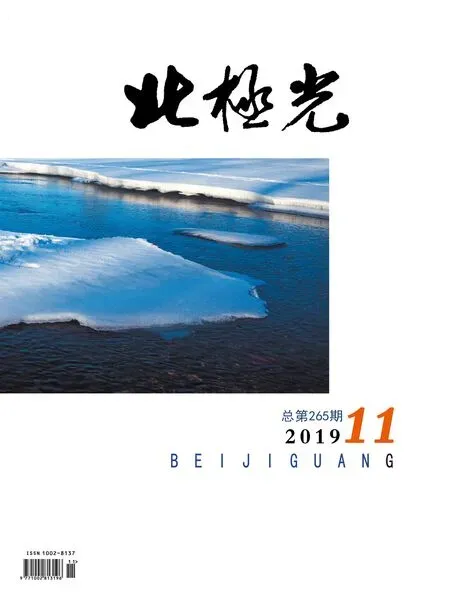醒 悟
楊慶發
劉溫學給我打電話說:“老同學,兄弟落難了,拉一把吧!”
“我也是給人家打工的,實在是能力有限,幫不了。”我這次真的不想搭理他了。
“可得了吧,你是大打工的,誰不知道你給老板支撐著半壁江山,在老板面前一言九鼎。咱們可是老同學呀,你吃干飯,也得讓我喝點稀粥吧。”
“可是……”
“可是啥,我不會給你丟面子的。我這些年走南闖北,也見識過。”
“我和老板商量一下再說。”
“我現在就坐火車去了。”
劉溫學求我辦事一直都是這么理直氣壯的。
既然他在危難之時投奔我來,我得認真對待這件事。我跟老板說明了劉溫學想來工作的事。老板爽快地答應了。
劉溫學打電話說:“我快到了,你馬上到車站接我吧。”
我開著轎車快速駛向了火車站,在火車站等了十幾分鐘,劉溫學乘坐的火車就進站了。
劉溫學身上穿著棉衣,肩膀上扛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大纖維袋子,隨著人流,脖子一抻一抻地往出站口走。他還歪著腦袋東張西望地尋找我。
我向他招手,高聲喊:“劉溫學,我在這兒!”
劉溫學看到我后,喜出望外的向我擺著手,又脖子一抻一抻地快步向我走來。他趁我接過他肩上的大纖維袋子時,快速脫掉了棉襖,里面臟兮兮的背心露了出來,散發著酸臭的汗味兒。他說:“這地方還這么熱呢,咱們家都下雪了。”
我看了看四周的人群,悄聲地說:“大庭廣眾之下,得注意點兒形象。”
“沒事,反正這地方誰也不認識我。”
“可有人認識我。”
“哦……對,我給你丟臉了。我提包里有薄衣服,我換上就行了。”劉溫學滿不在乎地拉開了大纖維袋子的拉鏈,在里面翻出一件皺皺巴巴的夾克衫,抖了抖,穿在身上。他把脫下的棉襖塞進纖維袋里。
我說:“你來得太快了。”
“等不急了,給我安排個什么差事?”劉溫學問。
我說:“還沒確定呢。”
“快點給我安排工作,要么你得管我吃住。”劉溫學說。
我原準備讓他分管十幾人的運料工作。今天他給我的印象是太不好了。雖然從前他的形象不盡人意,可那時他還挺在意穿著打扮的。沒想到兩年后,他竟然變得這般邋遢。安排這樣的人管理十幾人的運料工作,我感覺不妥當。我對他的工作安排有些猶豫了。我說:“公司里的事我得跟老板商量。”
“我大老遠的奔你來,怎么也得給我安排個管事的工作吧。”劉溫學的口氣好像我責無旁貸的應該為他安排工作。
“你想干啥?”
“你那樣的差事兒,我暫時還干不了,不過,管幾個人的工作應該能勝任。”劉溫學說。
“你讓我咋向朋友們介紹你?”我之所以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工作安排,我是想提醒他正確評估自己的能力。
“你說咱倆是大學同學,我和你一樣停薪留職了。”劉溫學說。
“那不一下子露餡兒了。”
“你不說,我不說,誰都不知道。”劉溫學自信地說。
“我是說人的氣質和素質是裝不出來的。”我說出了心中的顧慮。
“咋地,你瞧不起我?我可提醒你,我是自修過函授大學的。并且曾經被推舉過村干部,如果沒有兩下子,人們能推舉我當村干部嗎。”
劉溫學說的事我知道。別看他形象不佳,舉止不雅,卻爭強好勝,不服輸。那年因為我考上大學了,而他沒考上,他為了跟我比高低,報名自修了函授大專。三年后我大學畢業了,他的函授卻還有三分之二的科目考試沒過關。我分配到了工作,他又著急了,為了改變身價,異想天開地盯上了村干部的位置。他在村干部換屆時,極力拉攏一些村民,推舉他當村長。
我說:“此一時,彼一時,這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有
,能力不比他們強,他們不服管,會搗亂的。”
“我能干得了。再說有你在,他們誰敢不聽我的。”劉溫學認為我能幫助他,他吃不了虧。
我看他把話說到這份兒上了,轉移了話題,安慰他說:“別想這些了,先好好休息幾天再說。”
“是有些累了。”劉溫學說完仰在靠背上,不一會就打起了呼嚕。
我開車到了駐地。因為我是獨自一人來這里工作的,這兩年獨自住在辦公室里。我的同事在家中安排了接待劉溫學的午餐。
我敲開同事家的門,屋內的菜香味撲面而來,同事夫婦已經炒好了滿桌菜。
劉溫學跟我進屋后,貪婪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桌上的菜肴,嘴巴稀溜溜地一邊響著。他伸手從盤子內扯下一只燒雞腿,旁若無人地啃起來,驚得來陪客的同事直愣愣地看著我。
劉溫學回頭看我虎著臉,還給他使眼色,意識到自己犯了討人生厭的吃相。他立即放下雞腿,把帶油的手往褲子上蹭了蹭,笑嘻嘻地說:“我嘗嘗你們的手藝。我這人實在,都別介意。”
我指著劉溫學對同事們介紹說:“他就是我對你們說的劉溫學。我的大學同學,和我一樣,辦了停薪留職。他來咱們公司和大家一起共事,大家以后多照應一些。”
“我這人眼高手低,辭官不做,雄心勃勃的下海經商,沒想到經營不善,賠了本兒,這才來投奔老同學的。”劉溫學說。
“彼此彼此,都是打工的,一起共事,互相照應吧。”
“是啊,天南海北的,聚在一起,這是緣分。”
“不用客氣,是工作把咱們聚到了一起。咱們工作中是好同事,生活中是好朋友。”
同事們一邊和劉溫學握手,一邊說著客套話。
將針鐵礦配入量定為15 g,初始液固比0.4,反應溫度20 ℃,攪拌速度100 r/min, 飛灰反應15 min后取出,倒入模具中,在自然條件下分別固化1、3、5、7 d后脫模破碎,于40 ℃下烘干以便后續檢測。毒性浸出后測定浸出液中Cu2+、Pb2+濃度,浸出結果如圖6。結果顯示,兩種離子的浸出濃度隨固化時間延長而降低,在3 d后對于反應基本達到平衡。
“來,快圍桌吧,不然菜都涼了。”女主人說。
“咱們快圍桌。”我邊招呼著,邊打開酒瓶。
大家謙讓著座下了。
“有冰鎮啤酒嗎?”劉溫學看這樣盛情款待他,就不把自己當外人了。
女主人一邊擦著手,一邊歉意地說:“剛買回的啤酒,都是常溫的。”
“好辦,把啤酒瓶放到水筲里,用井里的涼水一拔,就妥了。”劉溫學一邊說著,一邊起身去廚房找水筲。
我生氣地說:“這是樓房,用的是自來水,哪來的水筲和井里的涼水!”
“可不是咋地,我坐車坐的把腦袋都坐懵了。”劉溫學一邊拍著腦門為自己解嘲,一邊臉紅脖子粗地回到座位。
我拿起白酒,把每個人的酒杯斟滿說:“既然是給我的老同學接風,咱們就得按著我們家鄉的規矩,一律都喝白酒。”
“好!聽楊總安排。”大家積極響應。
劉溫學端起白酒與大家碰杯說:“謝謝,謝謝。”
大家邊喝邊吃邊聊。劉溫學盡量克制自己的吃相。可他酒喝得有點多了時,色相又顯露了出來。他雙眼盯在了對面風韻猶存的女主人胸前。
我一個同事發現了劉溫學的不雅舉止,端杯朝劉溫學提醒地晃了晃說:“來,咱哥倆干一個。”
因為劉溫學的心思在女主人的胸前,對這位同事的善意沒絲毫反應。
我發現女主人的丈夫流露出不滿神色,為了避免事情擴大,把酒杯狠狠地往桌上躉了一下,震得桌上的杯瓶亂響。我說:“喝酒!”
“啊……對,喝酒,喝酒。”劉溫學回過神兒來,察覺到自己犯了大忌,慌慌張張地端起酒杯,和大家示意,然后把滿滿一杯酒喝得底朝天。
我感覺劉溫學有可能喝超量了,怕他喝多了再出別的洋相,及時制止地說:“咱們吃飯吧。”
大家都是我邀請來的,適可而止,符合他們的心意。
劉溫學聽我說結束了喝酒,開始吃飯,瞬間來了精神。他忘記了剛才的難堪,放肆起來,像餓狼撲食般呼嚕呼嚕地大吃起來。轉眼間,他便風卷殘云般地將桌子上的菜肴一掃而光。他的吃相把滿桌人都嚇傻了。
劉溫學吃飽喝足后,旁若無人地掀起衣角,擦了擦雙手和嘴巴,打著飽嗝走到沙發跟前,坐在沙發上,片刻就打起了呼嚕。
“他沒把咱們當外人,這么實實在在就對了。”
“對,該吃就吃,該喝就喝,比裝模作樣好。”
“坐了三天車,路上吃不好喝不好,趕上熱乎飯,他能不好好撮一頓嗎。”
我知道同事們是怕我難堪,在以各種理由為我圓場。
我看著劉溫學丑態百出的睡相,無可奈何地搖了下頭。
晚上劉溫學吃飽喝足后,在我辦公室睡了一宿。他次日清晨早早地起來給我使動靜,讓我起床。我只好起來。他說:“我的工作你安排了嗎?”
“安排了。”我不耐煩地說。
“讓我干啥?”劉溫學滿臉興奮地追問。
“本來安排你當運料班的班長,可是變了,只能讓你給運料班的班長當下手了。”我毫不掩飾地說。
“為啥變的?”劉溫學說。
“怕你勝任不了,誤了工作。”我說。
“如果我哪方面做得不對,你指出來,我可以改。我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毛病,可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呀。你怎么老瞧不起我呢!”劉溫學著急了說。
“問題是指出來,你也改不了。昨天中午吃飯時,你出了那么多洋相,工作中你也這樣,肯定不行。”
劉溫學喃喃地說:“不就是犯了吃相的錯誤嗎,因為喝多了,不能自控。工作中不喝酒,不會發生這種事。”
“還有呢。”我問。
“再就是喝酒時一走神,多瞅了兩眼那娘們兒。”劉溫學說完自己笑了。
我說:“僅僅是吃了一次中午飯,你就出了這么多丑。我又是給你使眼色,又是給你使動靜的,你改了這個,犯了那個。我沒辦法,只好提前結束喝酒。如果時間再長些,不知道你還得出多少丑。”
“以后我注意。”劉溫學說。
我說:“出門在外,最忌諱不懂規矩。人家拿你當人看,你卻不把自己當人,時間長了,誰還瞧得起你。”
“沒有那么嚴重。”劉溫學不服氣地說。
我說:“不信你就試一試,如果你不改掉那些臭毛病,即使讓你當運料班的班長,你也干不長。”
劉溫學坐在沙發上,雙手托著下巴沉思起來。
我口氣非常堅決地說:“你的能力我不懷疑,至于你的長相,畢竟是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不能要求你刻意改,可是你的吃相,色相,必須得改!”
“我下決心,保證改。不改,出門讓車撞死!”劉溫學拍著大腿發毒誓。
我將了他一軍說:“男子漢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到做到。”
“你就按著原來的打算給我安排吧,我保證不給你掉鏈子!”劉溫學站起身,向我保證著。
我高興地上前握住他的手說:“好!就要你這句話。”
“那就一言為定了。”劉溫學激動得使勁攥著我的手。
劉溫學當上運料班長后,的確沒負前言,把原來一盤散沙的運料班改變了,運料班的十幾個人干活很好。他的那些陋習也沒有了。
我去檢查工作時,劉溫學的運料班在卸貨。他一身灰土地和工人一起干活。我說:“咋樣?”
“你看呢。”劉溫學說。
我打趣兒地說:“浪子回頭金不換。”
“靠!我咋成浪子了。”
“好好干,機會成熟時,我跟老板說一說,讓你當隊長。”
“隊長比班長大,這是好事。你在老板面前為我多美言幾句。”劉溫學驚得兩只眼睛瞪了起來。
“那是肯定的。”我說著走了。
劉溫學興奮地向我揮了揮手,然后干活去了。
我看著他忙碌的身影,很欣慰。
劉溫學的突出表現老板知道了,沒等我向他介紹,他便打電話把我叫去。他說:“你找來的那個劉溫學,干得不錯,這樣的人可以多找幾個來。”
“他把原來散漫的運料班管理規范了。”
“這樣的人才咱們得重用,讓他當隊長咋樣?”
“他應該能干得了。”
“你讓他下午到我辦公室來,我跟他談一談。”
“我馬上通知他。”沒用我提,老板就先答應了。我暗暗高興。
劉溫學聽說老板找他,心生忐忑地問我:“老板不會是當面考我吧?”
“他是想看你的態度,你跟他表個態,下個決心。”
劉溫學說:“我換換衣服,洗洗臉就去。”
“不用換,你這身打扮才能體現勞動本色呢。”
劉溫學伸出大拇指說:“高,你真是高手!這才能證明我賣力干活呢。”
劉溫學從老板那里回來后,身份立刻變了,從原來只管十幾個人的運料班的班長,升職為管有五個運料班的大隊長。他有了獨自的辦公室,公司還給他配備了一輛摩托車,供他巡回幾個工地的儲料場使用。
劉溫學的職位高了,也刻意打扮自己了。每天他穿著干凈衣服,騎著摩托車,在各處儲料場檢查運輸進度和質量。他把運料大隊管理得很好。老板多次表揚他。他在我面前又開始趾高氣揚了。
劉溫學在我面前毫不掩飾地夸耀自己說:“別看我比你來得晚,可我進步快,不到三個月,我就當上運料大隊的隊長了,有可能我會與你平起平坐。”
“你管著我更好。”我話中帶有挑釁的味道。
不僅如此,我還聽說他在工人面前為了抬高自己,還顛倒黑白地虛構故事貶低我。他說他如何比我聰明,比我有能力,他曾經為了我,又如何兩肋插刀等等。
劉溫學完全忘記了我對他的幫助與提攜。
我已習慣了他翻臉比翻書快的秉性。他歷來是拉完磨,就殺驢吃。我原本也沒指望讓他感謝我。不管怎么說,他能賣力為公司做事兒,就等于幫了老板的忙。我沒必要與他計較生活小事。
劉溫學得意了沒多久,就挨了老板的批評。當時我受老板指派,去外地購置設備,需要很長時間。我分管的工作由老板兼管。老板每日事務纏身,很少顧及運料大隊的工作。劉溫學又不務正業了。他對工作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了。由于他疏于管理,運料大隊又成了一盤散沙。
我回來后,老板說:“你去查一查,看劉溫學在外面干了些什么。”
我很快掌握了劉溫學除了多次出入紅燈區外,還經常光顧本公司的材料庫區。他盯上了一個叫彬彬的女保管員。女保管員是本地人,長得標致,大約二十八、九歲,還未出嫁。她的社會關系很復雜。
我找到劉溫學明知故問地說:“你這段時間咋樣?”
“嘿嘿。”劉溫學知道我找他的意思,也不像以前那么趾高氣揚了。他從兜內掏出一盒高級香煙,抽出一支點燃。
我說:“聽說你這段時間不務正業了?”
“我想趁著這段時間工作不忙,找個對象,沒想到這些搬運工趁我不在,不好好干活。”
我發著脾氣說:“你的惡習怎么就改不了呢,你找對象也得講方式呀。”
“方法是有些不妥當。”
“你才來這么幾天,腳跟還沒站穩呢,怎么就忙著搞對象了。”
“你真是飽漢不知餓漢饑,你老婆孩子都有了,而我已經四十多歲了,還光桿兒一個人,不趁著現在風光的時候,找個媳婦怎么行。”劉溫學辯解著說。
“嘿嘿……”
“你笑什么?”
我說:“雖然我孩子老婆都有,可我來公司兩年了,還沒回過家呢。”
“我是沒記性。”劉溫學沮喪地說。
我說:“自律非常重要。”
劉溫學說:“既然我已經拉嘎上了一個不錯的小丫頭,就得發展下去。你代我給老板回個話,我保證把運料大隊弄好。”
“你拉嘎上的女人,是那個叫彬彬的嗎?”我說。
劉溫學又顯出了下賤的色相說:“就是那個小丫頭,她把我迷死了。”
“進度咋樣?”
劉溫學說:“這丫頭太傲慢,跟我不遠不近的。要么你幫我跟她說一說。”
“這個忙我不能幫。因為我不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告訴你,這個女人的社會關系太復雜了。為什么二十八、九了,還沒嫁出去?在她身邊有好幾個男人在摻和著。你想一想,這樣的女人你能養活得了嗎。依我看,你找個安分守己的中年女人踏實。”
劉溫學撓了撓腦袋說:“遇不上那樣的。”
“我看咱們公司的資料員王紅就行。她穩重,又是咱們東北老鄉。”我說的這個中年女人四十多歲。因為她誠實,辦事穩妥,再加上是東北老鄉,老板就安排她分管公司的資料工作。
劉溫學一臉委屈地說:“就她,我這不是舍了個柳木,又換了個朽木嗎。她不但是離過婚的,而且還帶著孩子,你這不是埋汰我嗎。”
“你想搞個啥樣的?”
劉溫學說:“憑我現在的身價,好賴也得搞個坐家女吧。再說我投奔你來,也得給你增點光呀。”
“我介紹誰,也不會把彬彬介紹給你。你若與她結合,會后患無窮。”我說。
劉溫學很不滿地站起身說:“靠!沒有你這個臭雞蛋,我還不做草紙糕了。不用你幫忙,我也能辦成。”
“別光顧著搞媳婦,工作還得好好干。”我在他身后高聲叮囑說。
劉溫學沒好氣地回答說:“這事兒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真拿劉溫學沒有辦法,他頂撞我,我依然得在老板面前給他說好話。好在運料大隊經過劉溫學調整,恢復了正常工作。運料大隊剛剛好轉了,他又一連好幾天不見身影了。情況反映到我這里,我瞞著老板暗地去查訪他。
這天我發現劉溫學躲在一處磚垛后邊,像小偷一般,探頭探腦地窺視著彬彬的動向。這時彬彬在不遠處與送貨的客戶辦理結交貨物手續。
我悄悄走到劉溫學身后,冷不防的在他肩上擊了一掌。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著實嚇了他一跳。他驚叫地說:“媽呀,嚇死我了。”
“哈哈……”我幸災樂禍地笑著。
劉溫學漲紅著臉說:“你怎么來了。”
“你上前談呀,在這兒偷看,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你是小偷呢。”我說。
劉溫學一臉苦相地說:“她老是忙活,說沒時間。”
“她答復你了?”
“只交談過兩次,就不搭理我了。”
“應該是沒戲了。”
劉溫學說:“有誰看熱鬧,也沒有你看熱鬧的。”
“你這家伙,圖謀不軌。”我說。
劉溫學說:“你出面跟她說一說,看到底差在哪兒,不然,我啥都干不下去。”
我想了想,覺得是應該出面了解了這件事,也好讓劉溫學安心干工作。我說:“我試一試,成了別歡喜,散了也別惱。”
劉溫學說:“你出面肯定大功告成。”
我走到彬彬跟前。
彬彬說:“楊總來了。”
“我跟你說點私事。”
彬彬說:“私事,什么私事?”
“是婚姻方面的事兒。”
彬彬用手指著在磚垛后面,探頭探腦的劉溫學說:“是不是他讓你來的?”
“不是。”
“我不信。”
“如果他讓我來,我是不會來的。”
彬彬撇了撇嘴說:“他呀,挺煩人的。”
“你們不是談過了嗎?”
“到是談過兩次,可我沒答應他。”
“我了解他,他聰明,能干,還本分。你可不要錯過這樣的人選。”
彬彬抬頭向劉溫學藏身的磚垛看了一眼說:“楊總,你是好人。他在我面前貶低你,你還幫助他說好話。你這是圖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圖。”
“他說你們是大學同學。”
“他心好,嘴不好。”我說。
彬彬說:“他把自己吹得天花亂墜,好像他哪樣都比你強。你那么優秀,他哪兒能跟你比,鬼才相信呢。”
我笑了笑說:“他的本意不是貶低我,而是想在你面前夸自己。他在你面前這樣表白,證明他真心喜歡你。”
彬彬臉紅了。
我編了一些故事,把劉溫學夸了一番。
彬彬說:“你說的我相信。”
“信我的沒錯。”我說。
“他就是形象不好。走路時腦袋老是一抻一抻的,好像要跟人家搶東西吃似的。”
“人無完人,誰沒有缺點呢。”我說。
彬彬毫不掩飾地說:“要是像你這么帥,我早就答應了。”
“我不行。”
彬彬笑著說:“你跟劉德華比是差了點。”
“聽說有好幾個男人在纏著你。”
彬彬說:“我早就與他們斷了。”
“那就好,你跟劉溫學談穩妥。”我說。
“你讓他過來吧。”
我邊向探頭張望的劉溫學走,邊向他招手。
劉溫學忐忑不安地走過來說:“怎么樣?”
“快去吧,彬彬在那兒等著你呢。我可告訴你,該吹捧你的話我都替你說了,這回你得虛心點兒。”
“知道了。”劉溫學疾步向庫房走去。
不知道劉溫學使了啥法兒,從此兩個人開始親密起來了。時間不長就同居了。
我見到劉溫學調侃地說:“進度夠快的,沒幾天就睡在一起了。”
“她主動提出來了,咱還能不答應嗎。”劉溫學得意地說。
“啥時候結婚?”
“我得攢點兒錢呀,人家是黃花閨女,好不容易翻回身,我得好好辦一次婚禮,熱熱鬧鬧。”
“你想著度蜜月,也不能影響工作。”我提醒說。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我會使出一百二十分的勁兒管理運料大隊。”
不知怎么回事,我看到劉溫學那種得意的神態,就莫名其妙的萌生了惴惴不安的感覺,又找不出是什么原因。
這天劉溫學滿面愁容地跟我說:“你說怪吧,原來那兩個服服帖帖的班長,怎么突然與我搞對立了,我說東他們往西,我也沒得罪他們呀。”
我聯想到在彬彬身邊的那幾個男人身上了……多日來,我心中不明不白的惴惴不安,得到了答案。
劉溫學和彬彬正是如膠似漆的時候,此時我不能說出疑慮,只能采取補救措施,幫助劉溫學把工作干好。我說:“如果不聽從工作安排,找兩個可靠的老鄉把那兩個班長替換掉。”
“馬上換掉。不換掉工作沒法干了。”劉溫學說。
劉溫學沒過多久又來找我了,這是在我意料中的事。他說:“你說怪不怪,剛把那兩個班長換了,其余那三個班長也不服從工作安排了。”
“全換掉。”我說。
劉溫學說:“我看夠嗆,再沒有合適人選替換他們了,并且這幾個人在運料班都挺有威望的。”
“你想咋辦?”我說。
劉溫學說:“我的意見是給他來個大換血,把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全部調整出去,都換成東北的老鄉。”
“到哪找這么多東北老鄉。”我說。
劉溫學說:“從各個工地抽調唄。”
“我哪有那大的權力,沒有老板的話,誰敢亂抽調人。再說各工地的包工頭也不干呢。”我說。
劉溫學有點六神無主地說:“那咋辦?”
“我跟老板商量一下。”我說。
老板打來電話,讓我馬上去他辦公室,說有事商量。
劉溫學有預感地說:“是不是跟我們運料大隊的工作有關?”
“或許有關。”我說。
“你多美言。”
“你出問題了,我臉上也無光。”我搪塞著說。
我趕忙去老板的辦公室。
老板不高興地說:“劉溫學怎么弄的,怎么好幾個班長都想收拾他呢?”
“我正想來跟你說這件事呢,不是劉溫學領導無方造成的,里邊是有人故意在搞鬼,不好好干活。”我說。
老板說:“他來這么兩天就得罪人了?”
“他的確是得罪人了,情況是這樣的……”我把劉溫學和彬彬處對象的事說了。
老板說:“這不是引狼入室嗎,這里的人誰不知道,彬彬為啥快三十了還沒嫁出去,不就是她身邊有些濫人嗎,正經人誰敢娶她。我早想把她辭退了。因為礙于她在當地政府上班兒的表哥面子,才留她在公司里。”
“她工作還可以。”我說。
老板埋怨我說:“你應該阻止劉溫學,不讓他跟彬彬處對象。”
“我阻止了,他不聽,還差一點兒跟我翻了臉。”我說。
老板生氣地說:“你告訴他,如果馬上跟彬彬脫離關系,還讓他當運料大隊長,如果他舍不得離開彬彬,就給他換工種。”
我把兩名剛當班長的東北老鄉找來,了解運料大隊工人不聽從劉溫學安排工作的原因。他們反映的情況,印證了我的猜測,的確有兩個與彬彬經常在一起的男人,請運料大隊中的當地工人喝過酒,接著出現了反對劉溫學的事。
我掌握了這些基本情況,準備找劉溫學商量解決辦法。還沒等我找他,他衣衫不整、面部青腫地來找我了。我驚訝地說:“你怎么了?”
“那幾個班長把我揍了。”劉溫學說。
我說:“他們居然這么迫不及待。”
“聽你這口氣,好像你早知道內幕了。”劉溫學一邊擦著嘴角的血跡,一邊疑惑地盯著我。
我說:“不是知道,是意料到的。”
“你咋不給我提個醒。”劉溫學埋怨地說。
我說:“我早就提過醒你,可你不聽。”
“你啥時候說過?”劉溫學說。
我說:“我跟你說過,你與彬彬結合,會后患無窮的話吧?”
“我跟彬彬在一起與這幾個班長有什么關系。”劉溫學說。
我說:“你還不明白呀?”
“彬彬與他們斷絕了關系,他們還摻和嗎?”劉溫學不相信地說。
我說:“你知道什么叫藕斷絲連嗎?實話告訴你,這個內幕除了你還蒙在鼓里,你們大隊里的人都清楚。不信你去問一問你新任命的兩個班長。”
“我對這兩個小子那么好,這事兒咋還瞞著我呢。”劉溫學說。
我說:“你總在人家面前夸彬彬,誰還好意思向你說這些事。你應該知道賭博出賊行,奸情出人命的話。這次他們對你是輕的,下一次有可能要你的小命。”
“沒這么嚴重吧?”劉溫學害怕地說。
我說:“當然嚴重了,要么老板能這么重視嗎。”
“老板知道了?”劉溫學心虛地說。
我說:“老板為這件事找我了。”
“他怎么說?”劉溫學說。
我說:“老板說如果你能痛下決心與彬彬斷絕關系,就繼續讓你當運料大隊長,如果你舍不得離開彬彬,就給你換工種。你這樣下去不但會給公司造成損失,還有生命危險。我考慮到你對彬彬感情那么深,讓你放棄她不可能,所以打算給你換工種。”
“你說得對,我和彬彬的感情太深了,我換工種吧。你還得給我安排管人的活。”劉溫學沒忘了自己的身價。
我生氣地說:“你在講條件?”
“不是,看同學面子,照顧一下。”劉溫學說。
我說:“沒照顧你嗎?”
“照顧了,再照顧照顧。”劉溫學說。
我說:“你暫時去后勤部,在食堂工作。”
“我靠,你咋這么安排呀。我不成普通工人了嗎!”劉溫學說。
我說:“這是為了保護你。因為后勤部咱們東北老鄉人多,為了暫時不讓你出頭露面,他們不好找你。”
“也行,我先干著,以后你再想辦法讓我官復原職。”劉溫學太在乎大隊長的身份了。
劉溫學去后勤部上班了。可他的劣性在那里又顯露出來了。
后勤部長有一次遇見我半開玩笑地說:“你同學的吃相也太嚇人了,不管剩菜,還是剩飯,一個勁兒地吃。那吃相簡直如餓狼捕食。招待客人時,我都不敢讓他去招待室。”
“朽木不可雕也!”我說。
狡猾的后勤部長說:“你得說說他,大伙對他的吃相都挺有意見。你可別說是我告訴你的。”
“他那樣我還不知道嗎,我不說是你說的。”我在空余時間給劉溫學打了電話,讓他到我辦公室來。
劉溫學嬉皮笑臉地說:“有啥好事?”
“有你這掃帚星,還能攤上好事!”我生氣地說。
劉溫學臉上的笑意一掃而光說:“又咋了?”
“你的吃相又放開了。”
“殘羹剩飯,我劃拉點兒,扔了不也是扔了。”
“吃可以,但注意點形象。”
“吃飯時就什么也不想了。”
“應該注意的還得注意。”
“吃飯考慮這兒考慮那的,還能吃順心嗎。”
“你是在單位,不是在家,在家可以不考慮,在單位得考慮。”
“我感覺你的事挺多,你這么想不累嗎。”
“我得多要求你,不然你能名揚天下。”
“我做不到咋辦?”
“我可告訴你,你在食堂必須改變吃相,不能像餓死鬼似的。”
“行,我記住了。”
“只記住不行,還得約束自己。”
“把你的招待煙給我點兒,我沒錢買煙了。”
“你的工資呢?”
“彬彬管賬,她不給我錢。”
“你還沒結婚就不當家了。”
“彬彬不讓亂花錢,想攢錢結婚用。”
“看來她是真心跟你過日子。”
“當然了。她不真心我能娶她嗎。”
我從文件柜里拿出兩條公司給我買的招待煙,用報紙包上,遞給劉溫學。
劉溫學接過煙說:“還是同學好。”
“好好干工作。”我說。
劉溫學說:“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吃公司的飯,拿你的煙,必須干好工作。”
“也注意團結同事,不要發生矛盾。”我叮囑地說。
劉溫學這次走后,我好長一段時間沒聽到有人說他不雅的話。
有一天晚上,我正準備睡覺,劉溫學突然推開我的門,滿面倦意地進來了。我說:“這么晚了,你來有事嗎?”
“今天晚上在你這兒睡一宿。”劉溫學說著攤開床上的被子。
“發生什么事了?”
“沒發生什么事。”
“沒發生什么事,怎么不回你自己那睡呢?”
“在你這兒睡一晚上不行嗎?”
“不是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
劉溫學說:“行,就別問那么多了,睡覺。”
“彬彬知道嗎?”
“我跟她說上夜班兒了。”
“食堂是不加夜班的。”
“我這謊言不像是真的。”
“你們鬧意見了?”
“沒有,就是想睡一夜消停覺。”
“晚上睡覺,彬彬不讓你消停了?”
“你想得也太多了,不愧是當領導的,都愿意往這方面想。”
“你才想歪了呢。”
劉溫學說:“你歪,還是我歪,弄明白了。”
“你突然跑到我這兒睡覺,得有個原因吧?”我說。
劉溫學詭秘地笑著說:“招架不住勁了。”
我仔細看他,嚇了一跳,他滿臉憔悴不說,還骨瘦如柴。我不解地說:“才十幾天不見,你怎么瘦成這樣了?”
“彬彬把我折騰的,可要命了。”劉溫學顯出一臉的痛苦。
我被劉溫學的表情逗笑了。
劉溫學鉆進了被窩說:“還樂呢。”
“不樂還哭呀。”我說。
“餃子好吃,可吃多了也撐得慌。”
“你給我吃。”
“你怎么這么不要臉呢。”
“我是幫助你解決困難,你不是逃到我這兒了嗎。”
劉溫學在床上翻動了兩下,然后說:“你說怪不,彬彬這些日子有點反常。”
“怎么反常了?”
“她夜里變著花樣折騰我。”
“把你美的,不知道姓什么了。”
“簡直是要命了,放在你身上你也受不了。”
我止不住笑了。
劉溫學打著呼嚕。他像死豬似的睡了一夜。我卻失眠了。第二天早晨醒來,他邊穿衣服邊說:“這一夜睡得真香,今天晚上我還來。”
“你可別來了。”
“為什么不讓我來了?”
“你再來,就要了我的命。”
“呼嚕聲太大了吧?”
“比雷聲小多了。”
“那我就不來了。”
“你不但別來了,而且別處也不能去,你想沒想過,如果彬彬知道了,不傷感情嗎。”
“言之有理。”
劉溫學穿好衣服走時,我注意到他不但腰彎、背駝了,兩只腳走路時,也撇成了八字。他的變化很大。
這一天上午,我在辦公室查閱工程資料,劉溫學開門進來了。他看見我在忙著,坐在一邊悶著頭抽煙。我把資料放到一邊說:“有事嗎?”
“沒啥事兒。”他陰沉著臉說。
“怎么不高興了?”
“覺得窩囊。”
“又咋了?”
劉溫學苦笑著捻滅了煙蒂后,左右看了看說:“這兩天彬彬夜里說夢話,還喊一個人的名字。”
“喊誰的名字了?”
“叫什么賴啟來,開始我還以為她招呼我起來有什么事,后來才明白是喊一個人的名字。”
“喊就喊唄,這有什么。”
“你裝糊涂吧。”
“本來我也不清楚。”
“你認識賴啟來嗎?”
“不認識。”我說。我知道這個男人以前經常和彬彬在一起,但我不能告訴劉溫學。
劉溫學說:“誰認識?”
“你沒問彬彬嗎?”
“她說是做夢。”
“說夢話就別當真了。”
“她沒說實話,不可能是說夢話。”
“做夢是有可能的。”
“反正我不相信。”
“你想怎么辦?”
“如果我知道怎么辦,就不來找你了。”
“你們之間感情的事,我也沒辦法幫。”
“好了,我不耽誤你工作了。”劉溫學走出了辦公室。
劉溫學說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認為彬彬和賴啟來的關系復燃了。怎么辦呢?如果我把推測的想法告訴劉溫學,擔心劉溫學不相信,或接受不了,如果不攤牌吧,我又覺得對不住劉溫學,擔心他受到更大傷害。
在我猶豫不決時,材料庫區報來了一份庫區人員調整后的名單表格,上面沒有彬彬的名字。我問送報表的女統計員彬彬的名字怎么沒在上面,女統計員說彬彬被庫區除名了,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女統計員走后,我正準備給材料庫區負責人打電話,劉溫學垂頭喪氣地來了。
劉溫學哭喪著臉說:“彬彬跑了。”
“她跑了?”
“是跑了。”
“啥時間跑的?”
“跑兩天了。”
“你真行,跑兩天了,才來跟我說。”
“我怕你說我沒本事,看不住女人。”
“不是你沒本事,是你原本就不應該跟這種女人在一起。”
“聽你的話就好了。”
“你詳細說一說。”
“前天晚上已經十點多了,她還沒回來,我給她打電話,她說因為庫區會餐,太晚了,就在女同事那兒住下了。我信以為真,沒在意,可是到了昨天晚上她還沒回來。我給她打電話,她手機關機。我到處尋找她,直到今天早晨,也沒找到她。剛才我才知道前天夜里彬彬是跟賴啟來住在了庫區里,被庫區巡邏的保安發現了,庫區把她開除了。有人看見她和賴啟來提著行李坐出租車去火車站了。我放在床底下的那兩萬多元錢被她拿走了。”
“我早就給你預言了,你跟她結合后患無窮。咋樣,現在她把你糟踐的人不人鬼不鬼。”
“當時我不是沒考慮你的話,是因為我太喜歡她了。”
“她拿走了你的錢,你馬上向警察報案呢。”
“先不能報案,說不上哪天她回心轉意了,還回來呢。”
“長點兒記性吧!快點兒忘掉她還不晚。”
“我對她感情那么深,想要忘掉她太難了。”
“真沒出息!”我實在忍無可忍了。
劉溫學強調地說:“這是感情。”
“如果她跟你有感情,能尋舊歡,把你甩了嗎?”
“她沒了工作,哪有臉面在這兒呆。”
“你以后打算怎么辦?”
“我想她轉悠一圈兒,還能回來。”
我無奈地說:“你就等著吧。我可提醒你,別把自己的工作等沒了。”
“放心,我會把握好的。”劉溫學悻悻地離開了我的辦公室。
我無法理解劉溫學對彬彬癡情的做法。我沒多問這件事。有一次我到資料室查找資料時,遇見了女資料員王紅。我們交談中提到了劉溫學。
王紅同情地說。“讓彬彬把他騙夠嗆,挺可憐的。”
“他還留戀著彬彬呢,這種人不值得可憐。”我生氣地說。
“不對呀,他對彬彬恨得咬牙切齒。”
“你聽誰說的?”
“后勤部的人都這么說。”
“那他是醒過味兒來了。”
“他那么樸實,彬彬這么風流,兩個人根本不合適”
“咱們看法相同。”
“劉溫學應該找年齡相當,知根知底的才行。”
我試探地說:“你對他的印象挺好。”
“他人挺好,也挺能干。有一段時間把運料大隊管理得多好。”王紅說。
我觀察著王紅的表情說:“你費點心,幫他介紹一個。”
“暫時沒有合適的。”
“有合適的。”
“誰呀?”
“我看你就挺合適。”
“媽呀,你咋還想到我身上了呢。”王紅笑著白了我一眼。
“咱們說正經的,我看你們倆非常般配。”
“人家愿意嗎?”
“這你就不用管了,你先表個態度。”
“孩子判給他爹了,我這頭沒意見。”
“劉溫學也沒意見。”
“誰說的?”
“我說的。”
“你說的?”
“對。”
“雖然你是他同學,他也是奔你來公司的,但這事你做不了主。”
“你一會兒聽我電話。”
“你這當領導的,頭腦有點熱了,不冷靜。”王紅眼神中流露出感激。
我想既然王紅沒意見,就應該趁熱打鐵,盡快促成他們。我走出資料室,直接去了后勤部。幾個人在一起閑聊著。劉溫學一個人蹲在墻根處想心事。彬彬出走對他打擊挺大。我說:“想心事呢?”
“你怎么來了。”
“看一看你。”
“別繞彎了,什么事說吧?”
“看你把彬彬等回來沒有。”
“我等她干啥,那爛貨回來我也不要了!”劉溫學滿臉憤怒地說。
我說:“你不想她了?”
“我恨死她了!”
“這就對了。她不值得你留戀。”
“你找我什么事?”
“你還想找對象不?”
“不想。”
“為什么?”
“你別拿我開心了。你這種做法不好,有火上澆油的用意。”
“澆點油,讓火更旺點。”
“可算了吧。我都快被燒著了。”
“我來給你滅火了。”
“你別繞彎好不好?”
“我真是來給你介紹對象的,你有了新對象,心中的怒火不就滅了。”
“讓那個爛貨把我整得這么臭,誰還愿意跟我。”
“王紅愿意。”
“可算了吧,她不搭理我。”
“那是恨你。”
“她恨我干什么?”
“我也恨你。”
“你們兩個恨我干什么?”
“恨你不爭氣,不像男人。”
“反正公司的人都瞧不起我,你們恨我也不奇怪。不過,你恨我,因為我給你丟臉面了。我跟王紅沒交往,她恨我可沒理由。”
“恨就是愛,愛就是恨,你懂不。”
“你這話說得不對,我恨彬彬,難道說我還愛她。”
“當然,你不愛她,就不會恨她。”
“我是真說不過你。”
我說:“你對王紅有感覺嗎?”
“沒有。”劉溫學說。
“為什么?”
“我就沒往她身上想過。”
“你往她身上想一想。”
“我配不上她,想不是白想嗎。”
“就說你愿意不?”
“她帶著個孩子,不過也行。”
“雖然孩子判給他爹了,她照顧孩子也是正常的。”
“孩子不是障礙。”
“你收拾收拾,跟我去找她。”
“真的?”
“假不了。”
“你跟她說好了?”
“你快去收拾吧。”我催促著。
劉溫學說:“我天天都這樣,還收拾什么。”
“你說得有道理。不過,不收拾是不是不尊重她。”我說。
劉溫學說:“結婚時再收拾吧。
“在這方面你總是迫不及待地。”我說。
劉溫學說:“已經過了羞羞答答的年齡了。”
“那也不能過于急切了。”我說。我給王紅打電話,讓她到我辦公室來。我把辦公室鑰匙給了劉溫學,我沒回辦公室。
劉溫學說:“夠朋友。”
“我只能為你做這些,下面的戲你得自己演,不能演砸鍋了。”我叮囑說。
劉溫學是在一個小時后給我打的電話。他說:“大功告成。”
“談到什么程度了?”
“結婚。”
“那就別拖了,趁熱打鐵,盡快辦婚禮。”
“謝謝,不用張羅了,找幾個朋友吃頓飯就行。”
我明白劉溫學的心思,他與彬彬的事剛過去,負面影響還沒完全消失,過于張羅不好,再說王紅是第二次結婚,也不想大張旗鼓地,所以只找了幾個朋友在一起吃了飯。
有一天我在上班路上遇見了劉溫學,他叼著高級香煙。我說:“有錢買高級煙了?”
“財權全交給我了。”劉溫學說。
我審視了一下劉溫學,才幾天不見,他臉色紅潤了,腰板兒也直了,八字腳也不見了,有著幸福感。我說:“看來王紅把你照顧得很舒服。”
“有疼有熱,還溫柔。”劉溫學說。
“看把你美的。”
“這才是生活。”
“我為你解決了這么大的事,怎么感謝我?”
“等你把好事做完了,好好感謝。”
“還有什么事沒滿足你?”
“我還沒官復原職呢。”
“運料大隊長的事,暫時解決不了。”
“為什么?”
“人家干得好好的,不能平白無故就撤職。”
“你可得當回事辦。”
“只當回事沒用,得有機會,沒機會不行。”
王紅在次日早晨來到我的辦公室。她進辦公室沒說話,表情不像平時那么自然。
我說:“有什么事你說。”
王紅說:“他想回運料大隊。”
我說:“劉溫學這家伙,真行,能讓你來找我,看來他做夢都想回運料大隊。”
王紅說:“我不想來,他讓我來……你別為難。”
我說:“我跟劉溫學說過了,現在的大隊長干得挺好,沒有理由換。就算我同意換,老板也不同意。”
王紅說:“我跟劉溫學也這么說了,他說你可以調換崗位。”
我有些生氣地說:“怎么調換?”
王紅說:“材料庫區出事后,你不是把那個負責人免了嗎,你把現在的大隊長調到材料庫,不就行了。”
我說:“你們真行,我的工作都給我安排好了,劉溫學別回后勤部上班了,到我辦公室來上班算了。”
王紅說:“你別生氣,我們想得不對,你別當真。”
我說:“你們也想得出來。”
“你是劉溫學的同學,沒把你當外人,咱自己人,說深一句,淺一句,不要緊。”
我說:“你回去告訴劉溫學,回運料大隊只能當班長,當大隊長不行,并且把現在的工作干好。”
王紅說:“你放心,他在哪個崗位都得好好干。”
我笑著說:“你能管住他。”
王紅說:“當然能。”
我說:“如果他不聽你的呢?”
王紅說:“他不聽我就不跟他過了。”
我說:“你讓他好好工作沒錯,但輕易說出不過了,就是錯,這種傷感情的話,不能隨便說。”
王紅說:“看不出來,你還會做政治思想工作。”
我說:“我得出去辦點事。”
王紅看我拿起了車鑰匙和文件包,沒再說什么,轉身走了。
我沒有外出辦事,只是不想跟王紅說下去。王紅走后,我放下車鑰匙和文件,考慮人員調整的事。雖然我想過讓劉溫學回運料大隊,但沒打算讓他官復原職,主要是怕老板不同意。這事我得跟老板說一說,看一看老板的態度。
老板來檢查工作時,我陪同他,邊走邊說,我把調運料大隊長去庫區的想法說了,但我沒說安排誰當運料大隊長。老板是明眼人,他明白了我的心思說:“你是不是還想讓你那個同學當運料大隊長。”
我難為情地說:“他做夢都想回運料大隊。”
老板開玩笑地說:“讓他回去當搬運工。”
我笑了笑,沒說話。
老板說:“雖然劉溫學有缺點,但有段時間把運料大隊管理得挺好,不計前嫌,避免缺點,看優點,還讓他當大隊長吧。”
我說:“謝謝老板。”
老板說:“咱們是朋友,你幫助我管理公司,我也得為你解決憂愁。”
我說:“劉溫這家伙是我同學,他讓我發愁。”
老板說:“愁什么,不就是個隊長的職位嗎,只要他能勝任就行。公司用誰都得給工資,何況領導職位的工資高。你是我的朋友,他是你的同學,繞了個彎,他也是我朋友。是朋友,就得幫忙。”
我說:“工作程序是不是有點亂?”
老板說:“咱們又不是黨政機關,也不是事業單位,哪有那么多程序。咱就是個公司,還不是集團公司,工作得靈活點。”
我說:“你一直認真對待工作程序的,這次破例是為了幫我的忙。”
老板說:“你得告訴劉溫學,回運料大隊得好好干,干不好,就讓他離開公司,不能總讓他犯錯誤。公司想發展,必須按照規定辦事。不能因小失大。”
我說:“你放心,如果他干不好,立刻讓他走。”
劉溫學官復原職了。因為那幾個鬧事的班長早已被辭退了,他干的得心應手。我最近外事多,沒去運料大隊,也沒見到劉溫學。
這天下午,快下班時,我接到了劉溫學的電話。他說:“老同學,有時間嗎,咱們出去喝點兒。”
“都有誰?”
“就咱們倆。”
“如果有事你就說,不用喝酒。”
“沒事。”
“沒事,喝什么酒呢。”
“近來你忙,我也忙,平時沒說機會說話,咱們聊一聊。”
“好。”我與劉溫學來到了東北飯館,點了幾道家鄉菜,要了一瓶二鍋頭。
劉溫學喝了幾杯酒,話匣子便打開了,感慨地說:“老同學,我做了很多對不起你的事。”
“沒感覺到。”我裝糊涂地說。
“老同學,雖然你嘴不說,心里卻有數。這么多年我一次次踩巴你,你卻在我遇到困難時,一次又一次幫助我……我欠你的太多了。”
我說:“咱們今天喝酒,不要說那些不愉快的事。”
“不行,今天我必須說。”
“沒必要說過去的事。”
“咱們念書的時候,我真不服你,但你處處比我強。”
“有些地方你比我強。”
“你胡說,我什么地方比你強?”
“彬彬的事我就不會。”
“你不用打岔,不提那個放蕩女人了,就說咱倆的事兒。”
“你說,我聽著。”
“我這人沒記性,一到有難時,首先就想到了你。”
“咱們是同學,找我就對了。”
“從前我總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混出個樣子,可總是碰釘子。所以我就破罐子破摔了。因為我不務正業,前妻老是跟我鬧離婚。你幫我解了幾次圍,但是我沒說過你好。當我與前妻離婚后,才想到了你的好處。我那時想,如果你還在單位上班,我與前妻可能離不了婚。那一年多,我過的不是人日子……我才決定投奔你來了。”劉溫學越說越沉重,淚珠從眼角滾下來。
“是金子終會發光的。”
“沒有你的拉扯,我上哪兒發光去!”劉溫學揉了揉眼睛說。
我說:“還是你有能力,你沒能力,我也幫不上。”
“我是因禍得福,如果前妻不與我離婚,我也會來找你,沒有你的拉幫,我哪會有今天的生活。”
“壞事變好事了。”
“有你這顆福星高照,我總能化險為夷。”
“來,跟我這顆福星喝一杯吧。”我端起酒杯。
劉溫學端起酒杯與我碰了一下,杯中酒下肚了。他拿起酒瓶,倒滿杯說:“來,好事成雙!”
“慢點喝,別太急了。”我說。
劉溫學說:“這杯必須喝下去。”
我也只好跟著喝下去。
劉溫學說:“我老是跟你過不去,但還離不開你,這是命中注定的吧?”
“這是緣分。”我說。
劉溫學喝多了,語無倫次地說:“沒有你這福星,我哪有今天。”
“沒有福星,咱們是蘿卜白菜,只是我比你早來公司幾年而已。”
“雖然蘿卜白菜都是菜,可那味道不一樣。”
“沒大區別。”
劉溫學指著盤子說:“你是香菜,我臭菜,雖然都是拌涼菜的作料,但是香菜是在園子里經過人工種植出來的。而臭菜是在山旮旯處隨便長出來的。雖然咱倆都是農村的孩子,起步一樣,可你讀過大學,有素質,而我一直在農村,檔次不一樣。”
“現在咱們都是打工的。”
“同是打工的沒錯,但你在公司里是一人之下,眾人之上,咱們還是有區別的。”
“你可別比了,都快把我比成省長了。”
“省長這輩子你是當不上了。”
“你還沒醉。”
“你在我心中是偉大的人物。我發自內心地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