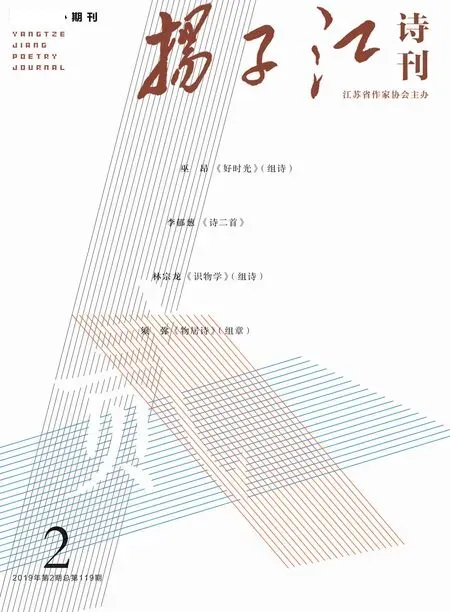雪 詩(組詩)
2019-11-13 05:07:39席地
揚(yáng)子江詩刊
2019年2期
關(guān)鍵詞:陽光
席地
寫封信
有人午夜歸來。被打破的
靜謐再次向四周擴(kuò)散。
我們結(jié)束了。
但不是以死亡為標(biāo)識。
我坐在燈下。
手里拿著一本書。
它是確定的。
但我想抓住某個片段。
也想就此給你寫封信。
描述此刻。
想到什么就描述什么。
中間穿插一個請求。
把自己簡化成另一個我。
或一張白色的信紙。
純潔性
十年前你喜歡的東西。
仍然喜歡的不多了。
但這樣的事實(shí)。
誰在乎呢。
時間是刮雨器。
我們仿佛是雨滴。
飛岀去。
近乎一句諺語。
我們始終在結(jié)構(gòu)里徘徊。
以為愛必須如此。
雪 詩
在雪上。
寧靜是言語。
為此要建造一座房子。
為一首詩。
然后談?wù)撁馈?/p>
談?wù)撍呢S腴和清澈。
他們說愛是枝條的彈性。
像一幅畫的抽象。
還不如在她耳邊
說岀的毛茸茸的細(xì)語。
是的。曾經(jīng)有過
那么一次。
我們忘記了一切。
包括雪的凝視。
山中小記
群山仍在起伏。
像工作日的例行公事。
我和朋友們
在山谷中徒步行進(jìn)。
狹小的溪流。
不時流露出湍急的歡愉。
我還沒有從它們之中。
醒悟過來。
還有些零星的場景。
需要反復(fù)記憶。
我們在松樹下。
接受一個松果落下的安慰。
它是真的。
沒有任何附加的意蘊(yùn)。
載 體
大街上陽光正盛。
房間里,
我感到有些陰涼。
我不能把這些陰涼
趕到大街上,
也不能把陽光放進(jìn)
屋子里。
我眼睜睜地看著它們。
眼睜睜地。
看它們在各自的
世界里老去。
像永不相見但又彼此思念
的一對戀人,
輪流把我當(dāng)成愛的載體。
致幻覺
幻覺被用壞了。
它蜷縮在我的懷里,
像只可折疊的貓。
正在老去。……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學(xué)生天地(A版)(2022年9期)2022-10-31 06:36:28
今日農(nóng)業(yè)(2022年16期)2022-09-22 05:37:08
好日子(2022年3期)2022-06-01 15:58:27
文苑(2020年7期)2020-08-12 09:36:36
文苑(2020年7期)2020-08-12 09:35:54
動漫界·幼教365(中班)(2020年7期)2020-07-14 03:07:21
文苑(2018年18期)2018-11-08 11:12:50
涼山文學(xué)(2016年6期)2016-12-05 11:51:42
劍南文學(xué)(2016年11期)2016-08-22 03:33:42
都市麗人(2015年5期)2015-03-20 13:3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