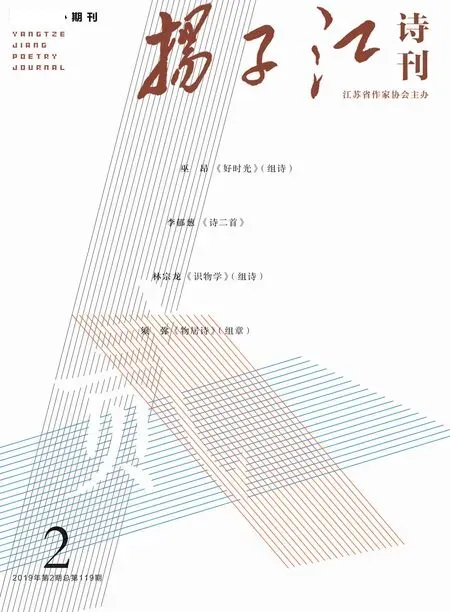《七月》的詩性蘊涵
2019-11-13 05:07:39葉櫓
揚子江詩刊
2019年2期
葉櫓
以前讀育邦的詩,總是隱約地感覺他有一種“腳踏兩只船”的意味。他一只腳踩在“靈性”的船上,另一只腳則踩在“智性”的船上。由于他的詩以短章為主,所以論及時總難免“以偏概全”。因為他在表現其“靈性”時,往往會忽略了“智性”的思考,而在表達其“智性”的思考時則會顯得“靈性”被侵占了。我們的詩評往往會追求一種全局而穩妥的立足,所以在無形中反而扼殺了詩人的藝術個性。用全面和穩妥來要求詩人,是詩評的一大弊端。寫詩評的人以此為立足點,其實是自縛手腳、舉步維艱的。
最近讀到育邦發表在《作家》2019年第一期上的長詩《七月》,這一新作不禁令我對他刮目相看,更是我近些年來在讀詩時很少有的心智的投入,忍不住想要寫點讀后的感想。
《七月》一共由29節短詩組成,每一節短詩其實都可以獨立成篇。這種隨意性的“斷簡殘篇”為什么又會被詩人組成一首長詩,而你如果仔細地研究一下,作為長詩,它又是在結構上頗具嚴謹的條理性的。我相信,這樣的長詩的寫作過程,絕不會是一氣呵成,而必定是靈感降臨時信手寫來,最后經過慎重地組構而成的,而某些篇章則必然是智性思考的慎重落筆。這恰恰形成了此詩的一大特色和優點,把育邦的靈性和智性都集中地呈現了出來。
我甚至無端地揣測,育邦對這首詩是懷有“野心”的。也許他在最初落筆時未必就想到寫這樣一首頗具規模的長詩,但是寫著寫著,隨著靈性與智性相互交錯地滲透,他終于形成了一種規模性的構思。……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兒童繪本(2018年22期)2018-12-13 23:14:52
讀者·校園版(2018年13期)2018-06-19 06:20:12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 16:58:59
讀者(2016年7期)2016-03-11 12:14:3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
文理導航·科普童話(2015年6期)2015-07-29 16:46:21
爆笑show(2014年10期)2014-12-18 22:2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