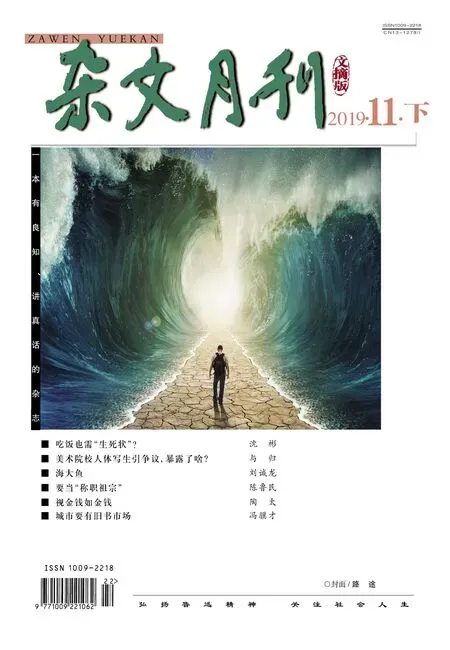吃飯也需“生死狀”?
□沈 彬
吃頓飯,又吃出了“生死狀”!
近日,武漢20 余名七旬老人組織同學聚會,因為擔心有人酒后出現意外,結果就弄出一份《安全責任自負承諾書》。
老同學聚餐,生生吃出了生離死別。
檢索一下新聞就可以發現,之前已經有太多判決。一同喝酒,有人出了事,家屬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把一同吃飯的人告上法庭。之前法院也判決過不少共飲者要承擔責任。
前幾天,隔壁鄰居阿姨拿著一疊紙跑過來問我:“小弟啊,這個東西能不能簽?”原來,阿姨退休之后參加了社區合唱團,在上海的濱江步道上唱歌,幾十號老人在一起,江風吹吹,紅歌唱唱,其樂融融。
不過,有一天,合唱團的“團長”突然鄭重其事地拿出打印好的“生死狀”,要求團員們要簽名,并要求老伴、子女簽字,不然就不讓參加合唱團了。這份東西的內容和網上流傳的“生死狀”相似:我自愿出來玩的,出了事,不要找“小伙伴”打官司啊。
這波“聚會生死狀”和十年前那一波“扶老太”的社會、心理機制如出一轍,既有對法律的誤解,又是消極自保。
那么,這種“生死狀”是否有效呢?這先得說清楚,一起聚餐時,當事人之間到底負怎么樣的責任?由于共飲人實施飲酒“在先行為”,產生一個互助的義務,即共飲人之間對相互的人身安全應當負有“合理安全保障”義務,包括相互提醒、勸告、通知、協助、照顧等義務。
什么叫“合理安全保障”?普通人之間的聚餐,不同于經營性行為,“合理安全保障”是比較弱的。比如一些法院認為只有以下行為才算是未盡到“合理安全保障”義務:一是強迫性勸酒;二是明知對方不能喝酒仍勸其飲酒,之后誘發疾病;三是未將醉酒者安全護送;四是對酒后駕車、游泳等危險行為未勸阻導致發生人身財產損害的。其實,不能把共飲人的互助義務劃得太寬泛,畢竟是一起來吃飯,人家不是保姆和家長。
大家也看得出來,“合理安全保障”有一定模糊地帶,于是才有人搞出“生死狀”。按《合同法》第53 條明確規定,合同中的關于“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免責條款無效,但是這個“生死狀”是簽給家屬看的,能夠表示同飲者、同唱者之間已經盡到“合理安全保障”義務,你不要在出事后來“搞事”。
其實,當今的過分維權正在抬高社會的成本,搞得人人自危,人人提防對方,這一定意義上是“權利走向反面”,形成一個死氣沉沉的“風險厭惡”的社會:有一點風險的事情,我就拒絕。
有人說,可以通過保險(解決難題)。早幾年,華海財險推出過“酒友險”,但不久就停售了,原來,人們發現這種保險就是“套套邏輯”:“被保險人對其他共同飲酒人未在合理限度范圍內盡到提醒、勸阻、通知、扶助、照顧、護送等基本安全保障義務的”,就不能理賠;但是,共飲人做到了這些,就滿足了前述的“合理安全保障”義務,就不會被法院判決賠償,也就根本不需理賠了。所以,你門檻精,要保險,但保險公司更懂“保險”。
要安撫喝酒前簽“生死狀”的恐慌,還得回到司法政策,就像當年解決“扶老太”恐慌一樣:這是要求法院也得堅持法定的“誰主張誰舉證”“過錯侵權責任”原則,不可以無原則地偏向受害人,否則,人人自危,就會增加全社會的信任成本、風險成本。
權利社會不是一個“刻薄社會”,權利意識也不代表斤斤計較。出了事兒,就必須找出人來賠償,“我吃了虧,我有道理”,這種想法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