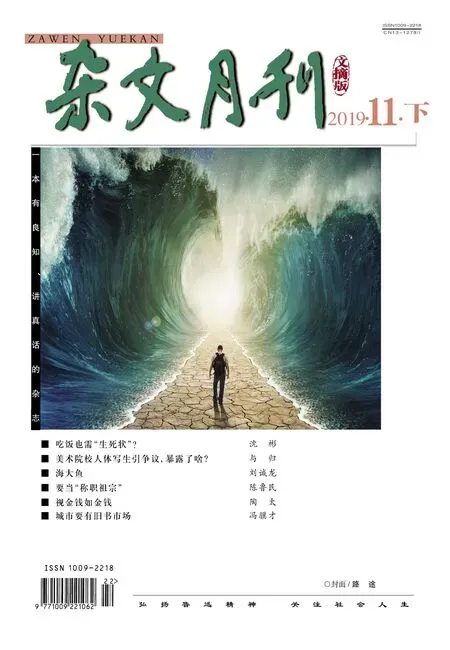生活好壞與官員好壞
●劉誠龍
曾國藩有個外號,叫一品宰相。曾國藩官拜武英殿大學士,是個宰相;曾封一等毅勇侯,官居一品,叫一品宰相,不虛,沒錯。不過這個諢名,另有所指,一品者,一碗也。慈禧太后櫻桃小嘴,貝殼小齒,“吃一粒糖便像懷了孕”(錢鐘書語),而獅子開口,卻是全席滿漢,天天過年;張居正視察地方,碗挽碗,碟疊碟,每餐不下百菜四十湯,仍是嘆息“無下箸處”。曾國藩官階,與慈禧比不上,與張居正一般高矮,若論起餐桌上那些事,卻是差若霄壤,張相吃的是天上龍肉,曾侯吃的是地下土豆;張相吃的是懸崖燕窩,曾侯吃的是籠里雞蟈(雞蛋)。曾國藩曾以“六事”戒子弟:“一曰飯后千步,一曰將睡洗腳,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骨,子弟宜學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不沾點菜。”
第六條便是曾侯的碗中歲月,所謂吃白飯,是光光一碗白米飯,不加鹽,不加油,壇子里的蘿卜皮與紅辣椒都不上桌,更莫說是咖哩雞飯蛋炒飯了。曾國藩領袖湘勇,號令三軍,都吃白飯。枕戈待旦,夜急行軍,容不得革命小酒天天醉,抓起一抓白米飯,塞滿肚子便渾身力氣,滿面精神。大腹便便,油頭粉面,能打甚仗?時有稱者:淮揚菜是“官菜”,粵菜是“商菜”,湘菜是“軍菜”。無湘不成軍,湘軍是湘菜打造成。
出生湖南卑濕之地,多是重口味,曾國藩飲食卻是小清新。曾國藩出身農民,從小粗茶淡飯,蔬食自甘;后來當了官,還是保持勞動人民本色,以素食和蔬菜為主,出白菜吃白菜,出蘿卜吃蘿卜,出茄子吃茄子,出豆角吃豆角,春夏來了,萬類菜蔬竟菜園,便去園里摘蔬菜。曾家四菜一湯,青青綠綠,紅紅白白,一清二白,皆無公害;偶去市場買豆腐,煎得兩面黃,便是打牙祭。日午入夜有客來,紅米飯南瓜湯,顯然不合待客之道,曾國藩囑咐老仆,去菜市場或剁斤把豬肉,或買一副豬腸,二者不可得兼;或買一尾草魚,或購一塊“腹水牛肉(肥瘦相間)”,二者只居其一,曾侯餐桌上,便有素有葷矣,三四樣蔬菜拱一盤葷味,曾侯因此得了諢名,號一品宰相。
若說曾國藩全是小清新,也不對,他也有湖南人的重口味,一向喜歡壇子菜:“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常做些寄與我吃。”腐乳,便是腌豆腐,紅辣椒裹四面八方,里里外外都是鹽,咸得要死,卻最便拌飯,一塊四方麻將大小的腐乳,可供一桌人吃一餐,湖南人稱之為“送飯菜”也。一碗飯淡出鳥來,死咽死咽,咽不下肚去,此時沾點腐乳,飯便如泥石流,直往肚子灌;與腐乳一樣有送飯菜高稱的,還有壇里姜:“鹽姜頗好,所作椿麩子醞菜亦好。家中外須講求蒔蔬,內須講求曬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曾侯這里說的曬小菜,大概說的是,將鮮蘿卜曬成蘿卜皮,將青芥菜曬干制作鹽菜吧。
海瑞評張居正,有個八字評:工于謀國,拙于謀身。這話有解是,張居正為國謀劃,不怕得罪袞袞諸公,將自身安危置之度外,如王安石,“雖千萬人,吾往矣”。是這個意思不?不曉得。張居正生前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呼風喚雨威武雄壯,而其身后差點掘墳碎棺遺骸喂犬,兒孫未保無限凄涼,謀了國,未謀身。一代名相落得如此境地,全怪帝國太惡乎?自身原因有沒有?張居正飲甘饜肥,奢侈無度,還真是拙于謀身,比不上曾國藩,講求曬小菜,足驗家興衰。
節儉是美德,于私人,是私德,是養身之道;于公人,是公德,是奉國之道。節儉,對吃公家飯者來說,不只是經濟問題,尤是家國大計。領工資的,沒誰能一天三包煙,一包一千五百元;領工資的,沒誰能三餐百余碗,一碗群眾吃半年,非要朱門酒肉臭,除非是權力弄貪腐;一個官人弄貪腐,弄得一家,家破人亡;整個官人弄貪腐,弄得一國,國破朝亡。官人日用之道在哪里?正道在袖中,政德在碗里。袖里乾坤大,碗中家國長。
清官看套間,好官看飯碗。節儉不定是好官,工農多是節衣縮食的,工農是沒得吃與穿,不得不節儉;好官一定是節儉,干的是工作,拿的是工資,當的是工人階級,沒誰有資本揮金如土鐘鳴鼎食。曾國藩諢名叫一品宰相,于成龍諢名是于青菜,大清第一清官湯斌,其諢名是豆腐湯。于成龍每餐上桌都是青菜蘿卜,湯斌三餐以豆腐作羹,此之謂:吾貌雖瘦,必肥天下;反之定是:吾貌若肥,必瘦天下。
官員是好官還是壞官,可審看他這,可審看他那,這里審那里查的,好生復雜。復雜之審不可廢,簡單法子也是有,治大國看烹小鮮:投之兩眼,看他一碗。有個做官定律,難說放諸四海而皆準,卻也放諸宦海差不離:碗里生活好的,做官做得多半壞;碗中生活壞的,做官做得多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