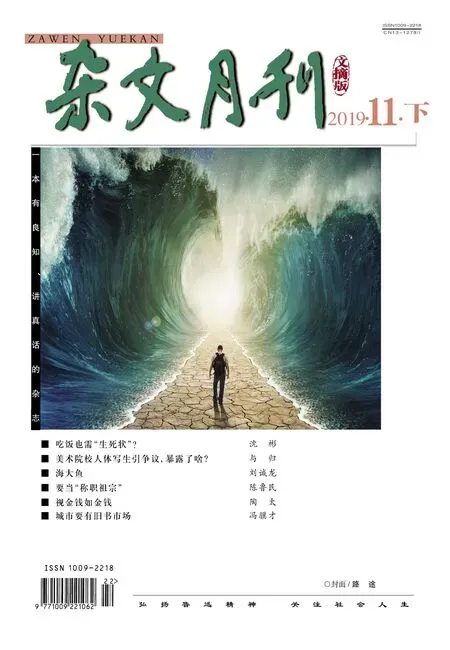“盛名”水分及其他
□黃桂元
名氣這個東西,一經歲月的深究,常常捉襟見肘,破綻百出,所以大可不必當真。細想,人還是那個人,臉還是那張臉,腹中還是那些貨,怎么可能因名氣的驟然飆升而脫胎換骨?范曄在《后漢書·左周黃列傳》感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可謂一語道破玄機。一個人,因某種機緣巧合有了光環,繼而漣漪被擴展,形象被放大,若在適度范圍,也并非不能接受,一旦“盛名”神乎其神,天花亂墜,不可理喻,人們就要警惕了。
現代資訊社會,在“近水樓臺”的位置處處占先者,想不出名都難。記得某位前央視主持人曾深情回憶,當年如何在小地方辛苦打拼,如何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央視,最終收獲了事業的回報。這里面有個錯覺,該主持人忽略了一個事實:平臺越大,越容易有社會的辨識度和知名度,以央視主持人來說,由于“臉熟”,輕而易舉就可以成為公眾人物,或者說,名滿天下,大致是其工作性質決定的,個人努力與之不能說沒有關聯,但不起決定作用。我在魯院學習的時候,聽過一種“外省批評家”的說法,曾被大家認同。“外省”的概念來自巴爾扎克小說的啟發,在19 世紀的法國,巴黎往往象征著中心、權力、高貴、傲慢,“外省”則意味著偏遠、弱勢、落后、卑微。所謂“外省批評家”,是指那些身處邊緣,遠離文化中心背景,缺少權威平臺和話語權的“二三線”批評家,切莫小看“中心”與“邊緣”的區別,同樣是勤奮努力稟賦突出的批評家,身處“外省”,在全國成名只能是小概率事件。
一些頭腦清醒的世界級大作家對“盛名”的弊端洞若觀火,不希望自己的寫作受其干擾。米蘭·昆德拉認為突然而至的“盛名”,“就像一場可怕的災難,比一個人家里失火還要糟”,因為“名譽毀了作家的靈魂”。斯坦貝克對諾獎帶來的虛名很恐懼,他對記者訴苦,“我害怕得它,怕得要死,我不在乎它有多么令人垂涎……我感覺,似乎獲獎者之后就再也寫不出什么好東西或有勇氣的東西來了。這個獎就仿佛讓他們退休了似的”。福克納也曾遺憾,初進文壇時,沒能像伊麗莎白時代一些作家那樣回避署名,而僅僅讓自己的文章流傳下去。
“盛名”還會帶來社會心理的偏差、傾斜,和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合理。《新約·馬太福音》記載了一則寓言:某國王出門遠行前,交給三個仆人每人一錠銀子,吩咐道:“你們去做生意,等我回來時,再來見我。”國王回來后,第一個仆人報告:“你給我的一錠銀子,我已賺了十錠。”國王遂獎勵他十座城邑。第二個仆人報告:“你給我的一錠銀子,我已賺了五錠。”國王遂獎勵他五座城邑。第三仆人說:“你給我的一錠銀子,我怕丟失,一直包在手帕里。”國王于是命令,將第三個仆人的一錠銀子賞給第一個仆人,由此衍生出“馬太定律”,即“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1968年,美國科學史家羅伯特·莫頓用此概括出了一種著名的“馬太效應”,質疑一種社會現象:“相對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聲名顯赫的科學家通常得到更多的聲望; 即使他們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樣地,在一個項目上,聲譽通常給予那些已經出名的研究者。”
水分永遠是水分,總會被歲月濾盡和風干,就好比修史這件事,當朝者的書寫難免失真,需要未來歲月的糾偏和矯正,才能取信于后世。人們相信“是金子總會發光的”。倫勃朗和梵高分別生活在17 世紀和19 世紀的荷蘭,一生籍籍無名,窮愁潦倒,同時代人沒有誰認為他們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的價值。只活了41 歲的卡夫卡落魄一生,貧病纏身,他在寫給好友勃羅德的信中預感自己的下場很慘,“我的路一點都不好,我必將(據我所見)像一只狗一樣完蛋”,他留下的遺囑也很決絕,“凡是我遺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記也好,手稿也好,別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無保留地讀也不讀地統統予以焚毀”,所幸勃羅德違背了卡夫卡的遺愿。他們生前寂寞孤苦,身后尊享“盛名”,歷史老人的火眼金睛,實在令人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