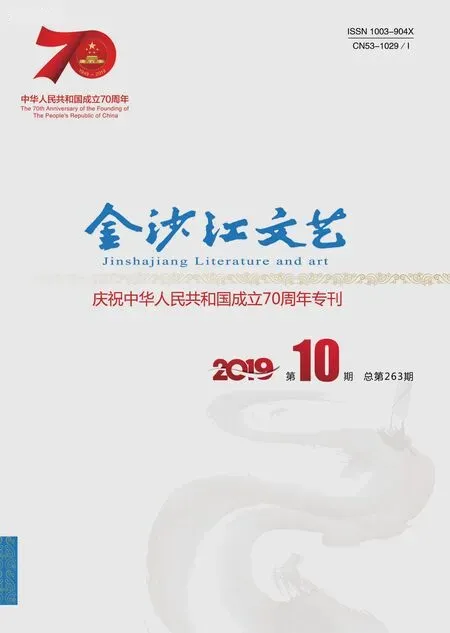一路梨花
我的老家在一個(gè)偏遠(yuǎn)的小山村,門(mén)前倒流河上的六座橋,近兩年陸續(xù)通車(chē)了。二叔收起挑了多年的扁擔(dān),鳥(niǎo)槍換炮開(kāi)上了小三輪,不論是采瓜摘果還是運(yùn)送豬食糞草,總看到他騎著車(chē)一路“突突……突突……”騰起一陣煙塵,滿(mǎn)山的棠梨花應(yīng)和著,蕩起一片花海。
讀小學(xué)時(shí),祖母帶我去河對(duì)岸放牛,得繞過(guò)磨盤(pán)山。磨盤(pán)山山頂圓如磨盤(pán),山勢(shì)陡峭,峰奇石秀,林木茂密,飛鳥(niǎo)出入其間。越過(guò)倒流河,對(duì)岸的山坡有圓潤(rùn)肥胖的沙棘果和粉白閃亮的棠梨花。一街河蜿蜒曲折,河與路如同兩條系在大山里的絲帶,不見(jiàn)其發(fā)端也不見(jiàn)其終極,一路向西綿延長(zhǎng)遠(yuǎn)。
聽(tīng)父親說(shuō),祖父是出過(guò)民工的人,15歲便征調(diào)去修滇緬公路,路修得越長(zhǎng),家離得越遠(yuǎn),吃盡了一路的棠梨果,滿(mǎn)帶著一路的酸澀,生病返鄉(xiāng)后大伯接替祖父出民工,有幸留在了路橋公司,一輩子與公路打交道,成了人人羨慕的公家人。
父親還說(shuō),祖母是大理人氏,13歲便隨外曾祖父 “走夷方”,那時(shí)的外曾祖父是茶馬古道上的挑夫,馬鍋頭下的二趕子。祖母因感染風(fēng)寒,途徑一街,路過(guò)曾祖父門(mén)前,被寄居在曾祖父家里,托付給老草醫(yī)的曾祖父照料。
說(shuō)起這些,我立刻端起下巴,一副想要聽(tīng)書(shū)的架勢(shì),父親斜瞪我一眼,我像被電了一下,瞬間被甩出老遠(yuǎn)。
你知道什么是 “走夷方”嗎?
我搖搖頭。
亦是滿(mǎn)臉的不解。父親也不說(shuō)話(huà),就只聽(tīng)得耳邊水煙筒轟隆轟隆的聲響。
過(guò)了一會(huì)兒,父親說(shuō),解放前,云南人 “走夷方”是出了名的,大多數(shù)人是到普洱一帶采購(gòu)茶葉,富豪商賈還會(huì)遠(yuǎn)走緬甸,采購(gòu)產(chǎn)自英國(guó)的日用百貨,這些 “洋貨”通過(guò) “走夷方”的馬幫運(yùn)進(jìn)了國(guó)內(nèi),甚至遠(yuǎn)銷(xiāo)西亞等國(guó)。南華一街是經(jīng)過(guò)南景線通往緬北,往北穿過(guò)下莊到達(dá)祥云、下關(guān)的一個(gè)重要節(jié)點(diǎn),八九十年代仍還有少量馬幫和零星馱隊(duì)經(jīng)過(guò)此條線路販運(yùn)木材和茶葉。
“走夷方的苦你們不懂!”父親一聲長(zhǎng)嘆,身后又是猛吸水煙筒時(shí)轟隆轟隆的水聲。
這么一說(shuō),我似有領(lǐng)悟, “走夷方”的苦,生活之苦,還不都是無(wú)路少路之苦!
祖母聽(tīng)天由命和祖父成了家,一輩子沒(méi)有離開(kāi)過(guò)林家村,每每到棠梨花開(kāi)的時(shí)節(jié),祖母便會(huì)背著花籃到山頂撿拾風(fēng)干的松樹(shù)果,裹腳的奶奶拄著拐杖一個(gè)人望著那條細(xì)如羊腸的小道,久久不動(dòng),眼圈兒紅紅的滿(mǎn)是淚水。那顆老山茶下,纖瘦的奶奶一襲青布藍(lán)衫像極了一束捆扎過(guò)的藤條,冷風(fēng)里颯颯作響,周?chē)鷿M(mǎn)是開(kāi)滿(mǎn)白花的棠梨樹(shù),星星點(diǎn)點(diǎn)。
艱難的祖母被萬(wàn)水千山阻隔,或許記憶里的老家早已渺遠(yuǎn)得如拳如豆,又或許正如眼前灶膛里閃爍的火星兒,明滅可見(jiàn)。年邁的祖母滿(mǎn)臉頹唐,思緒漸漸的也只剩下馬脖頸上那鈴鐺一聲長(zhǎng)一聲短的“叮咚——叮咚”的聲響,以及那漫山遍野的棠梨花和羊腸小道上數(shù)不清的馬腳跡。
水煙筒上,父親的煙卷兒只留下一個(gè)紅紅的點(diǎn)兒,陽(yáng)光透過(guò)鏤空的窗花照著父親瘦削的臉龐,照著他凸起的顴骨和高高的額頭,分明看到他鬢發(fā)里的風(fēng)霜。隆隆的水聲震蕩著滿(mǎn)屋子起伏彌散的炊煙,父親仿佛整個(gè)兒又陷進(jìn)了深深的回憶。
祖祖輩輩生活在這樣閉塞少路的大山,想想父親對(duì)于我,是寄托著希望的。
考上大學(xué),我的戶(hù)口從小山村轉(zhuǎn)入了玉溪市紅塔區(qū)鳳凰路134號(hào),仿佛是一跨龍門(mén)到了 “不遠(yuǎn)萬(wàn)里”的地方,學(xué)校與家之間,路又拉長(zhǎng)了我淺淺的鄉(xiāng)愁,只是在玉溪依然能吃到甜中帶著酸澀的棠梨果,紅塔山腳下的棠梨花也有的星星點(diǎn)點(diǎn),有的一團(tuán)一團(tuán)像碩大的絨球。
四年后,戶(hù)口又隨著我遷回楚雄州南華縣馬街鎮(zhèn)小廟村26號(hào)。我們一起進(jìn)村的兩個(gè)大學(xué)生,不到半路便暈車(chē)嘔吐得眼角掛滿(mǎn)血絲,奄奄一息。
我問(wèn)小張,你為什么來(lái)這么偏遠(yuǎn)的地方教書(shū),他說(shuō),我外地的,之前壓根兒就不知道還有這么偏遠(yuǎn)的鄉(xiāng)鎮(zhèn)。
我問(wèn)小李,他說(shuō),報(bào)考的崗位我考了第七名,前一二名都放棄了面試,是被補(bǔ)錄過(guò)來(lái)的。
他們回問(wèn)我,那你呢?
我脫口而出,這里是我的家鄉(xiāng)。
其實(shí)心里,不也和他們一樣,暈得變形的臉上寫(xiě)滿(mǎn)忐忑。希望我走出大山的父親,又該會(huì)是怎樣的悵惘。
好在路不斷延伸著我們的希望,也在加快著家鄉(xiāng)脫貧致富的腳步。南華人民對(duì)路的追求自古以來(lái)就沒(méi)有減弱,以至于南華被譽(yù)為 “九府通衢”地,道路博物館。滇緬公路穿城而過(guò)連接滇緬,一路能感受到偉大抗戰(zhàn)的歷史氣息;高鐵開(kāi)到家門(mén)前,北上廣不再遙遠(yuǎn);楚南大道暢通便捷,把州府與縣城腕在了一起;南永公路縱橫南北,直通川滇;南景線把璀璨多彩的九個(gè)鄉(xiāng)鎮(zhèn)串在一起,像一條散落在哀牢山脈的珍珠項(xiàng)鏈。
一條條路,又像一條條臍帶維系著城里鄉(xiāng)下,進(jìn)城打拼的人們不斷改造著鄉(xiāng)村,老家的水土仍然在萬(wàn)物的輪回中滋養(yǎng)著我。
山連著山來(lái)水連著水的故土,烙上了祖輩的腳印,走進(jìn)新時(shí)代,縈繞在心頭的鄉(xiāng)路,不斷煥發(fā)新顏,四通八達(dá)一路梨花,也將烙下我們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