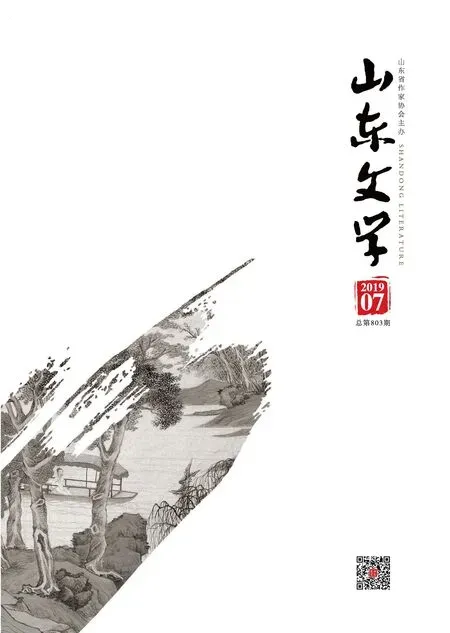不要攔截決堤的河流
劉星元
每一篇散文,我都會構思很久。有時候是一兩個月,有時候是三四年。長久的構思并非是在為某一章節、某一段落、某一詞匯服務,相反,我只是在尋找、觸摸一種整體的氣氛。
我始終覺得,作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便是為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種獨特的氣氛,使這氣氛能與這篇文章匹配。這種氣氛來源于作品所敘述的內容,更來源于作者與內容進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切身的體會。除此之外,那些細微的部分,我不做深思。
這種絕無細微可言的構思,讓我為整篇文章定下了“留白”的創作機會。是的,我將它稱之為“機會”,有機可乘,但也可能會坐失良機。這是一把雙刃劍,握著這把劍,面對我沒有下足功夫的內容,就像面對一個陌生的敵人,我找不到他的弱點,每一次進擊都是無的放矢,于是又一篇失敗之作誕生了。幸運的是,我偶爾會抓住一些時機,在早已營造好了的氣氛的推動下,很多完全超出自我預料的詞語、段落乃至章節就流淌了出來。我多么喜歡這些旁逸斜出的部分,它甚至打亂了整篇文章的結構,就像是一條決堤改道的河流,我不愿把它攔截到河床里,讓它規規矩矩地流淌。它愛怎么流就怎么流吧,唯有這樣才能保持它的野性,唯有如此才能流出它自己的樣子。
《為名所困》和《六畜凋敝》這兩篇作品都不能看作是結構嚴謹的作品。不但不嚴謹,甚至它們還有些“偏”,偏離了主題,偏離重點,偏離了我最初的構思。值得說明的是,我對“構思”沒有太大的責任感,我從來都不愿一以貫之地效忠于它。依然是那條決堤的河流起了作用,在寫作的進程中,河流開始沖破之前的構思,流出了讓我都感到有些陌生的軌跡。這軌跡就如窯變,或許會讓我這名制陶工匠制出的作品支離破碎,也或許會以神靈之手的名義提升了它的藝術品位。單單就這兩篇文章而言,它們“窯變”的結果如何,作者本人無法也不愿細究,只留待讀者和評者驗證。
《為名所困》這篇文章一部分來源于我真實的經歷,一部分來源于我飄渺的夢境。當然,夢境其實也是真實映像的一種表現形式。大多數文學作品都是作者對自身生活經驗的提取和揮發,一個人幾乎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局限去書寫完全陌生的題材,農民之子、縣城小民和鄉村教師這三重身份,讓村莊、縣城和學校構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三個坐標。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專程回了兩趟老家,站在二十年前我所就讀的小學校園里,那些與名字有關的故事又飄了出來。“你的名字是什么?”面對這個構建起我兒時煩惱根源的問題,二十年前,我無法完成一個既真實又為人所信服的回答;二十年后,面對社會的巨變,我自身的顛沛以及我與這個時代的相互磨礪,我依然無法參破答案。在時間的長河里,一個人的生命何其短暫,但名字或許不是。我想到,再過很多很多年,當我已銷聲匿跡,我已失去了對我名字的所有權,但我的名字或許依然還在這個世界上隨著另一個人輾轉漂泊。和我一樣,那個在許多年后持有我名字的陌生人也會經歷與我相似的際遇。比方說,他被自己的名字困住的經歷也將不斷重演——以名為證,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以一個符號作為特征,構成了另一個我。
《六畜凋敝》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對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單一問題的疑惑。從結構上來說,這篇文章非常簡單,無非是前與后的對比;從思想上看,這篇文章十分陳舊,無非是對六畜凋敝的傷懷。然而,我想把它納入我稍微比之大一點的寫作框架里去——在這個時代的書寫體系中,有人在謳歌,有人在批判,有人在反思,而我只是在用自己無解式的嘮叨去撫摸我所面對的人和事。但我作品中的內容未必都是真實的,我有時會在合理的尺度中摻入虛構的內容,正如散文家周曉楓所說“虛構的目的是為了靠近真實”,虛構有時候比真實還要真實。值得一提的是,在《六畜凋敝》這篇文章里,我引用了與我同居蘭陵這座小縣城的詩人辰水的《在鄉下》,這是在我的閱讀體驗中最接近我想要表達的氣氛的一首詩,就在那個節點上,我承認我傾吐出的語言未必能超越這首詩,所以把它抄錄下來,既是討巧,也是致敬。
“文學作品中的神秘,往往源于作者的無知或故作無知。”這是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寫下的一句話。這句話可謂是自嘲。我有時會在一些作品里營造出神秘的氣氛,并樂此不疲,但我直到現在都不能明確這是一種獨特的跡象還是一種拙劣的表演。因為尚不明確,我或許還會固執地嘗試下去。
在我看來,就散文創作,任何嘗試都是有意義的,因此,我從不攔截任何一條決堤的河流——決堤的河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河流老老實實地沿著河床流淌,更可怕的是河水已經徹底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