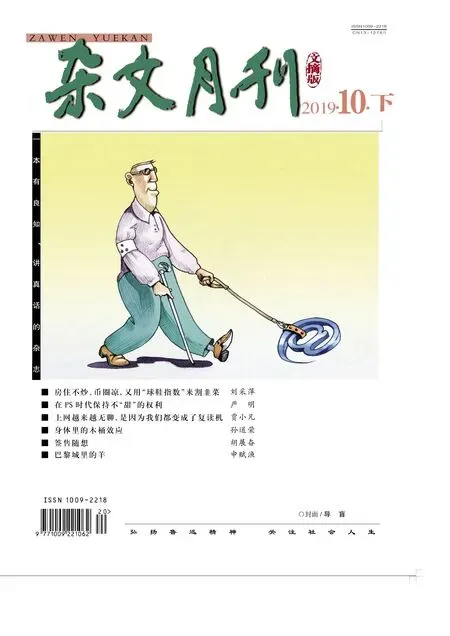“流量明星”在街頭
□肖復興
讀翁偶虹先生的《春明夢憶》,有一段寫他陪高慶奎逛廟會的文字,非常有意思,讀罷讓人感慨,讓人尋味。
高慶奎何許人也?如今的年輕人,大概很多是不大清楚了。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高慶奎是京劇老生高派的創始人,當年和余叔巖、馬連良齊名,被譽為須生三大賢和四大須生之一。他和梅蘭芳掛雙頭牌在上海演出,曾經盛況空前,一票難求。按照現在的說法,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流量明星”。
廟會上,還有一位“流量明星”,就是綽號叫做“面人湯”的湯子高。在老北京,湯氏三兄弟,如同水滸傳里阮氏三杰一樣,都是京城捏面人的高手,名噪一時。湯子高是湯氏三兄弟中的老三,被人稱作“湯三兒”。他擅捏戲曲人物,人物造型精準,帶有故事性,曾經為不少京昆名角捏過戲人,造像逼真,頗受好評,一位戲人,價錢居然最高達一塊現大洋,在當時,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翁偶虹先生稱贊他“風格如國畫中的工筆重彩”。
這一天,兩位“流量明星”,在廟會上相會,按照現在的想象,該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景?
湯子高久仰高慶奎。高慶奎也久聞湯子高的大名。這是他們的第一次相見,不是在舞臺上的鎂光燈閃爍之中,不是在宴會上的燈紅酒綠之中,不是在電視節目的明星訪談節目中,也不是在觀眾葵花向陽一般的簇擁中,就在街頭的廟會上,在熙熙攘攘熱熱鬧鬧的人來人往中。
寒暄過后,湯子高技癢,好不容易見到久仰的高先生,便直爽的要求高先生為他擺一個《戰長沙》的身段,他來照葫蘆畫瓢,當場捏個面人兒。這頗像畫家的寫生,卻又比寫生還要有難度和有意思。因為畫家寫生的對象可以是一般的人,而湯子高面對的可是京劇名角。這不僅要考驗擺出身段的人的本事,也是考驗作者的本事,別在高慶奎的面前演砸了,露了怯。
高先生也不推辭,或如我們當今一些“流量明星”一樣扭捏作態,而是爽快地一口答應。
《戰長沙》是一出有名的紅生戲,也是高慶奎的拿手戲,講的是關公和黃忠在長沙一戰生死結盟的一段故事。高慶奎就在湯子高的攤位前擺了個關公拖刀的身段,顯示出的是“刀沉馬快善交鋒”的雄姿,很是英氣逼人。但是,這是個單腿跪像,對于湯子高而言,捏起面人來,不是一個好的角度,他覺得有些棘手,一時不好下笊籬。
好不容易見到了名角,又好不容易讓人家為自己擺出了身段,按照我們如今想象力的發揮,該如何是好?或者,就坡下驢,知難而進,捏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或者,不好意思,虛與委蛇,委婉逢迎,讓高慶奎覺得盛情難卻,自己換個身段。那時候的藝人,畢竟不是如今的“流量明星”,沒有那么多的派頭和心思,而是直爽得沒有一點兒拐彎兒。
湯子高看高慶奎這個關公拖刀的姿勢不靈,立刻請高先生換個姿勢。高慶奎沒有覺得這個要求有什么過分,或者是對自己有什么不尊重,立馬兒換了個關公橫刀肅立的亮相姿態,立在湯子高的面前。
那么多人圍看,那么長時間站立,高慶奎沒有一點兒不耐煩,和在舞臺上正式演出一樣,那一刻,他不是高慶奎,是紅臉的關公。
其實,并沒有用太久的時間,只是湯子高心里覺得讓高先生立在那里時間太久,心里有些過意不去。湯子高沒用兩碗茶的工夫,面人兒捏好了,他把面人裝進一個玻璃匣中,走到高慶奎面前,奉送給高先生。高慶奎一看,面人捏得惟妙惟肖,他愛不釋手,對湯子高說:手工錢我領了,但玻璃匣錢照付。說罷便拿出錢來——是多出一份手工費的。
這便是當時的藝人,在藝術面前,透著對彼此的尊重和惺惺相惜。如今,不要說藝術品的漫天要價,或高昂的出場費和演出費,就是讓那習慣于被前呼后擁的“流量明星”,當街攤前為“面人湯”擺個身段,一個不行,再擺一個,這樣的情景還能見得著嗎?
想起美國學者戴安娜·克蘭教授在她的《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一書中曾經說過的話:“工藝品產生于個人階級的文化世界,而藝匠的作品產生于中產階級的文化世界。”克蘭進一步指出,后者的文化世界則是以純粹贏利為目的的。克蘭在這里指出的“工藝品”,很有些像湯子高的面人,擴而言之,也可以說是高慶奎的藝術。而克蘭說的“藝匠”則是我們如今很多的流量明星。文化世界不同,各種追求不同,在市場和人為的操縱和哄抬下,膨脹的流量明星和藝術,已經無法和前輩的藝人與藝術相比擬。我們再也看不到高慶奎為湯子高當街擺身段的街景,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