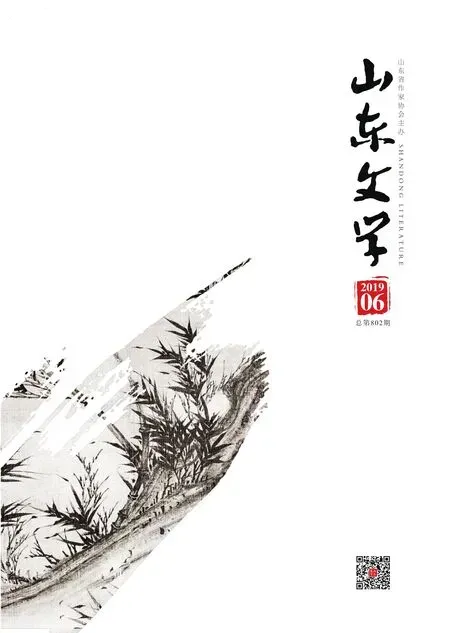村莊肖像
青年河
盡管村莊的變化是緩慢的,但我見到的村莊正在一點點脫離開原來的模樣。印象中的村莊慢得如蝸牛,有人說她在拖著時代的后腿。毋寧說,她在堅守著古老的傳統,讓古老的風尚不至于一下子就被滌蕩殆盡。古老風尚,就是我們走過的每一步。古老風尚里散發出的溫暖讓當下的生活真實而詩意充沛。在慢與古老里,我們得以神定氣閑地去勾畫她的模樣,描摹她的姿態。村莊的慢的真實讓我們得以看清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她的物事、煙火、聲音、氣息構成了我們發展史中的基本要素,也是村莊肖像的全部。唯有在村莊,我們才能找到自己的來處。
村莊多么簡單。名字、位置、人口、地畝、產業,村民由來構成了她的全部。這是村莊肖像的題記、說明。因為做文化資源普查,我一度迷戀地名文化,與某尊敬的老人討得一本地名志,讀來十分有趣,文字簡省,是志的一種,從中也能看出當下非虛構文學的端倪。一些健康、樸正的素質在文字間隱藏,是當下泥沙俱下的文學所缺失的。但我看重的是潛行于敘述干凈的文字里的信息密碼,它是我們生活的基礎,想象的源頭,文學的母本。地名或者村名的形成,是祖先、職業、生活、事件、榮耀的集合,它囊括了我們生活的全部。人類學由此得以出發,接受啟迪。
我知道,在海邊或者大河流的邊上,還有與海或者河有關的元素。放大中國地圖,會看到有一些帶水的地名,比如喊水、響水,其實那里是干旱地區,水是那里的人們祖輩的夢想。對于我的村子,從地名志的記載里,我只看到簡省、干凈,這是中國多數村子的樣子。也是他們數百年如一日生活的寫照。小村子簡單,干凈,從不用一點多余的東西修飾自己。所有的冗長都顯得累贅。她不為誰而低頭,也不為誰而高傲,就如一個自信者,所有的修飾都顯得冗長,是累贅。地名,猶如一個人的簡歷。時常在一些人的簡歷里看到太多讓人臉紅的東西,因為他們的不自信。太多的榮譽疊加或者名不副實的東西一次次地暴露了自己淺薄、脆弱、卑小的內心。他們真應該回到自己的村子,在村碑面前低下頭去,仔細地讀讀村碑上簡約的文字,讓自己紅一會兒臉。然后望向村子里,想想父老鄉親。他們只關心莊稼,只關心子女,只關心身邊的事。他們把遠方秘密地收藏進自己的內心,從不輕易示人。內心的事業是一個人的甜蜜。小村子里走出的人,憨厚、樸實,他們臉上微微笑的樣子是一直以來的狀態,這也是他們與你分享私密的唯一途徑。他們的內心與外貌是一樣的。他們不炫耀,也不低下,不卑不亢。僅僅村莊的這一啟示,便讓我們心生敬畏,永不停息地去追求。
曾經,作為一個從小村莊走出的少年,內心簡單,對村莊的認識也僅局限青年河畔的十幾個村子。小村子把我包裹得嚴嚴的,讓我對外面隔膜。高中剛入學幾天,與后面的同學互相介紹,他說他家是小劉家的,我說我也是。我們互相感到不可思議,一個村子的居然互不認識。然后是各種可能的說辭,互相解釋不認識的理由,接著又是各種自我否定,最后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們村子400口人,家家戶戶大人孩子沒有不認識的。但這事居然這么蹊蹺。幾天后是另外一個同學的對話揭開了謎底。原來我們是兩個村子,村名相同,不在同一個鄉鎮。幾年后去千里之外的海邊讀書,也遇到類似的事情,晚飯后與同學去夜市散步,路上看到一輛帶棚子的三輪車門上寫著李莊鎮,以為是從家鄉來的,感到很是親切,想等車主來與他說幾句話。結果在邊上等了一二十分鐘沒見人來,同學催我趕路就失望地離開了。若干年后,搜集資料時在地圖上看到許多同名的地方,想起了年輕時候的這一往事,覺得自己鄙陋、簡單,但內心幾近透明。我想,這都是小村子給我的。回首小村莊的時光,如水干凈,代替青年河洗滌我心。這是村莊肖像畫的題跋或者落款。
土灰色的鄉村在想象中安靜、隱忍。高大、葳蕤的樹木恰到好處地遮蔽過來。樹是村莊的影子,讓村莊盡綻綠顏。灌木、綠草也是修飾。從遠處,我們只能看到郁郁蔥蔥。郁郁蔥蔥也成了村莊的樣子。綠草叢生,樹木勃發,安逸、靜謐里的村莊如赤子。村莊草木豐盛,面對諸多熟識的面影,我只能說出它們中幾種的名字,有錯誤的指認也未可知。就如河畔周邊的人群,一張張面孔和藹、熟悉,但大多卻無法叫出他們的名字,也說不出他們來自哪個村子。回到村子里,去鄉村集市上,有人打招呼,有時候我也只能含混而又不失禮貌地招手、寒暄。一次回鄉下,母親領著我去青年河南的棉田,在村口碰到一位陌生的老太太與我打招呼,我模糊地答應著。過去后問是誰,母親說是丫頭奶奶。是這個可愛、勤勞的老太太已經老得讓我認不出了,還是我一點點里離開這個小村子。而我也只是諸多離開者中的一例。草木里就有我們猶豫、不安的影子。我能說出的樹木是棗樹、榆樹、楊樹、槐樹、柳樹,偶有異類,比如迷糊爺爺屋后的六七棵高大的臭椿,寶銀老爺爺家前面樹林子里有一棵挺拔的柏樹。我能說出的青草有爬蔓草、狗尾巴、茅草、蘆草,野菜有燕子尾、鳧子苗、青青菜、灰菜、曲曲菜、苦菜子,我還無法為蘆葦歸類,大多數于我就是長著一副熟悉面孔的陌生者。草木的青澀氣息、花朵以及成熟果子的或淡雅或濃郁的香、甜浸染透村莊。割回家的青草被父母曬到屋后的空場上,晚上堆起,第二天放開的時候,青澀味道、霉味混合在一起彌漫著,藏身其間的說不上名字的小蟲子飛舞起來,吸引來蜻蜓在半空里嗡嗡著。在青綠中,村莊一片富饒。樹是有精神的,經過歲月滄桑的被稱為樹精,上了年歲的人能夠感受到它的精、氣、神在村莊里的彌散。我家后面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樹,我說不上它的由來,父親也含混。我們后面的院子原先是大爺爺、二爺爺在這里住,老哥倆共同管著石榴樹。后來父親與二爺爺換了地方,我們搬過來,二爺爺搬到前面的院子去。石榴樹就由大爺爺一個人管著。從石榴樹發芽開始,經過開花、結石榴、收獲,大爺爺天天笑瞇瞇地圍著石榴樹轉悠。石榴樹結的石榴又多又大。大爺爺走了后,石榴樹也失去了精神,跟著衰老下來。前邊的院子里的那棵槐樹,夏天里枝繁葉茂,把不大的院子遮蔽的滿是陰翳。我就在陰涼、發暗的院子里玩耍。我們搬出來后,二爺爺住過去,頭幾年我還經常去院子的樹下玩耍。后來我離開村子,二爺爺故去,院子空下來,直到最后院子拆除,槐樹依舊在路邊葳蕤。好幾次有人出高價錢要買這棵大槐樹,父親思索再三沒有賣。我也與父親說過,這棵樹不能賣,家里沒人之后,它就屬于村子的。是的,這棵樹成了神。它的精、氣、神與整個小村子融為一體。每個經過它的人,或感到親切溫暖,或懷有敬畏,或感到神秘。它,是親人故友,是還在的長輩,是不說話的神靈。
如果在村前畫一條綿長的河流,村莊肖像就是完美的。當然會有河流,河流是村莊的血脈,也或者是無可代替的引領。村莊始于河流。想象開初,是河流把祖先迎來,讓他在此住下來,繁衍生息,墾田耕種。河流,讓完美的村莊飽滿、富有。鄰村有人曾羨慕地對我們說,你們村上的青年河把東北上的鹽堿地都變成了寶地,不像我們村,躲在后面,不靠河,澆地有多費勁。這是一條河流給予村莊的全部。當然,其間會有豐富的細節展開,那屬于肖像畫的細部。從河流開始,村子里的人們會引出河流的分支,或者挖長長的溝渠。村子里的人們先后從青年河向西北、東北方向開挖了一條地上溝渠、一條地下河流。地上溝渠的盡頭有一個大水塘,我們叫坑塘。地下河流一直通向東北,讓東北的數百畝鹽堿地成為沃野。后來,狗嫌哥的土地都分在了青年河南岸,他就在河岸又蓋了房子,樂呵呵地把家搬過去,悠哉游哉地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女兒結婚才搬回村子里。村子里在青年河南的土地少,但很多的時候大人孩子都愿意蹚水過河去種地。種地累了,就下到河邊坐下來洗臉、洗腳,男人們會跳到河里洗澡。坑塘邊也是不錯的地方。圍繞著水,我們豐盈滋潤。河流,是村莊所有詩意的起源。
這時候,從村莊里走出了人,一個,兩個,三個……也許有更多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孩子。畫師正好捕捉了這些,村莊肖像畫里就有了人群。他們說話或者嬉笑的聲音在畫面上流動著。村頭東來哥屋后根里的樹蔭下,長慶爺爺、立軍在下象棋。這一老一少,老的個子矮小,原先在隊上當隊長不做農活,后來在外面謀了一個差事,現在退休在家,更加悠閑;少的兒時就身體有病、走路也不方便,不能干莊稼活,但這孩子懂事,就在家里燒火做飯洗洗刷刷不閑著,忙完家里的活就搖搖擺擺地出來活動一會兒。老的為人開朗,說話干脆利落,前幾年突然得了腦血栓,說話結巴、含混了。冬天他家里生了爐子,好些人去他家里打撲克,他一個人出來站在村頭路口瞎轉悠。少的有病但善良,受人敬重,村里的人有時候會與他開善意的玩笑。少的也聰明,下棋、來土方,幾乎在村子里找不到對手。往里走就是十字街口,最早是和爺爺、常增大爺、曾祥大爺這些人的地盤,他們抄著手站在這里或者坐在墻根的棒子秸上,曬著太陽天南海北地說閑話。現在這里變成了健身廣場,有健身器材,一些老頭老太太也像城里人一樣健身。白天里,男人們坐在存祥爺爺門口朝向廣場的樹蔭下閑聊。老頭們也換了人,原先的那幾個老頭都走了。原先那些年輕的面孔上也多了蒼老的皺紋。冬天里,他們也會在建國家朝向廣場的門口的陽光下敲鑼打鼓,或者打撲克。晚上,會有放電影的來。電影是老電影。看電影的多是上年歲的老人,還有中年人,他們仰著頭,看得認真,有那么一瞬也好像想到了什么,或許是在緬懷舊時光。他們試圖在捕捉舊影里的時光,以便在虛幻中回去。我家與長德叔家門口,坐著迷糊爺爺、父親、母親、連云大娘、常德叔兩口子、西來嫂子。新農村建設,弄得胡同比以前整潔、漂亮了。只是人比以前少了很多。原先狹長的胡同里十來戶人家,足足有五六十口人,孩子哭大人吵,打打鬧鬧的;現在只剩下三五戶人家,不足二十口人,幾個老頭老太太整日里如雕像般坐在胡同里。沒有誰能敵得過時光。也或者,變化的是我們,時光還在原來的位置不曾前進抑或后退分毫。
在村莊里的,還有生靈們,它們就在外面身邊。它們無所事事地在村莊里游蕩。這村莊也是它們的。馬或者牛,是我們的畜力,種莊稼的幫手,家家戶戶都有。我家先是有一匹馬,后來換成了牛。馬,曾經與牛一樣,是村子里常見的畜力。后來牛的價錢提高,人們就都養了牛,畜力與經濟兼顧。此后,馬就成為我夢中的物象。在懷念里,它是溫暖、俊逸、野性的復合體。在馬的往事里隱約散發著一些熟悉的人的氣息,是養馬的人、騎馬的小伙伴。偶爾也會想起馬在勞累之后它低垂著眼瞼的溫順樣子,那個時候,它就像我們家中的一員。然后是牛,沒用多久,它在村莊里也成了少見之物。據我所知,目前只有發小勝利還養著牛。記得一年家里的牛產了小牛,由于沒照顧好,小牛剛生下一會就死掉了,母親在邊上一直流淚。這是復雜的感情,養久了的動物,也會與主人產生相互依賴。最先記住的應該是羊。母親在前面的院子的磨坊里養了羊,后來聽說是讓我與弟弟喝羊奶,我們不記得喝羊奶這事情。姥姥家也養羊。我喜歡小羊羔,小羊羔與我們一樣,天天在姥姥的院子里瞎踢蹬。姥姥家東屋的前面是一個糞堆,邊上是半堵矮墻,我與小羊經常爬到矮墻上玩,然后順著矮墻爬到屋頂。村子里勝利家養羊,記得他每次去東北的地里干活,總是牽著幾只羊在我家門前走過。羊走一路,拉一路羊糞蛋蛋。后來金來、西來、狗嫌他們哥幾個先后買了三五十只綿羊在村外放著,冬天里就偷偷把羊趕進麥田里啃麥苗子。羊啃過的麥苗,就死掉了。村子里都礙于情面不好意思去說他們。一次鄰村放羊的到我們村東北的地里放羊,被村里的人逮到,把一群羊都趕回村子里。這些都成了稀有的生靈。記得小時候村子里最多的是雞,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十來只雞。街道上、胡同里、村子的樹林子里都會有咕咕著低頭覓食的雞。我與發小們幾乎都有趴在自家雞窩邊上偷雞蛋的不光彩歷史。偷了雞蛋,然后拿著去店子街橋頭換錢,攢夠了錢買小畫書看。若是誰家的雞丟了,家里的女主人就會爬到房頂上把想象中的偷雞賊的祖宗十八代叫罵一番,最后累得氣喘吁吁才意猶未盡地順著梯子下來,雖然沒有討回丟失的雞,但總算出了口惡氣。母親還在家里養過鵝。鵝是看門的好手,比狗都好使,不過有時候這笨家伙連主人也不分。家里養鵝的日子,每次回去我都會在家門口喊人,不過首先迎接我的就是伸著長脖子哦哦地叫著的七八只鵝。見此我會在門邊隨手抄起木棍自衛。那時候小女兒才一兩歲,在鄉下由母親看著。小孩子天天在院子里與鵝在一起,我擔心她被鵝啄了。母親看了我的表情笑著說,家里的鵝誰都啄,就是不啄小妮子。她天天蹲在院子里看著鵝,有時候她一起身還嚇得鵝都四散開呢。與養狗不同,養鵝是為了賣鵝蛋。收鵝蛋的來了,走過每一條胡同。女人們把攢下的鵝蛋交給收鵝蛋的,收鵝蛋的問清男主人的名字然后用鉛筆寫在鵝蛋上。過些時日,孵不出小鵝的就會被根據上面留下的名字退回,女人再把當時收下的鵝蛋錢算好還給收鵝蛋的。退回的鵝蛋被腌制或者炒菜用。鵝因為能補貼家用,只有女人喜歡。男人喜歡的是狗。對于狗,我又愛又恨。六七歲的時候我被狗咬了小腿肚子,從此害怕狗。后來發小送給我一條狗,養了幾年,說是禁止養狗,被秋來哥宰了。他送我狗肉,我不敢吃,家里人也不吃。幾年里,它早已經成了家里的成員。還有鴨,有貓,還有黃鼬、狐、刺猬、蛇這些少見者,還有老鼠……它們獨立特行,也偶爾在村子里露面,我們會被它們中的一些嚇一跳,也會把其中的一些禍禍掉。還有太多我們叫不上名字的。它們一直或明或暗地與我們在一起,為我們喜愛,或者厭惡。有了它們,村莊才不孤單。它們也是村莊的住戶,有的比我們還要長久。
有建筑,才會構成村莊的大致模樣。所謂的建筑,就是一個個毗連的農家院。一個個的農家院落把村莊分成一兩條主要街道和大大小小七八條或者十幾條乃至更多的胡同。院落、街道、胡同讓村莊有了基本格局。房屋總是深深地烙刻著時代的特色。原先是土房子,房屋是土木結構。記得我上學的時候,學校里就開設土木工程專業。土房子昏昏欲睡,閉上了嘴巴,成了文物或者記憶。水泥、鋼筋、瓷磚成為房屋的基本材料,樓房也不再是村子里的新事物。四十年前,我們搬到后面與大爺爺住一個院子。父親蓋的磚與泥土混合的房子,房頂掛瓦,大爺爺依舊住他低矮的小南屋。小南屋是土的,墻體厚實,夏天里一進大爺爺的小南屋,就有一股涼涼的感覺。下鄉扶貧,去所在村的大隊部,領路的越過掛了牌子的、好看的大隊部,去了后面的舊房子。問原因,解釋說磚瓦房好看不實惠,夏天熱冬天冷。然后領路的指著土房子的墻說,你看這墻多厚實,夏天曬不透冬天凍不透,冬暖夏涼,隊上也不富裕,這樣夏天少用點電冬天少點點煤。對門迷糊爺爺住在他的土房子里,隊上說給他蓋新房子,他不去。他說他離不開土房子,磚瓦房住不慣。他說沒幾年的活頭了,就讓他在土房子里踏踏實實地走吧。土房子與土地散發著同一味道。陰雨天偶有受潮的霉味,也是大地的味道。散發著霉味的還有常年在南墻根里的神仙屋子。幾乎多數人家都有神仙屋子。我家的神仙屋子就是立起兩塊土坯,上面斜搭兩頁瓦。神仙屋子好像是奶奶的專屬,每年她都讓爺爺給她重新搭一次。神仙屋子里供三仙。三仙是龍仙、狐仙、柴仙,即蛇、狐貍、刺猬。與奶奶一起的福增老奶奶、玉柱奶奶、和奶奶這些老太太們稱呼這幾種動物為仙家。有時候奶奶把我惹急了,我就會報復性地去搗毀她的神仙屋子。她氣得直打哆嗦,又追不上我,只能把我上下罵一通,然后讓爺爺再給她把神仙屋子搭好。這一波老太太之后,村子里已經不見神仙屋子了,幾乎不再有神秘氣息。神秘氣息是村莊精神不可少的厚重。村莊日漸單薄。
最莊嚴的是祠堂。一個村莊,應該有祠堂或者宗廟。這是祖先們居住的地方。祠堂是肅穆的圣殿。祠堂建筑宏偉,有太多的講究與禁忌。我們被禁止去祠堂。祠堂沖門是影壁,這是每戶人家所沒有的。祠堂建筑的木、磚、石上有花紋。對此,我們不明就里。祠堂的院內干干凈凈的,好像每天都有人灑掃。大門的正上方有好看的題字,大而有勁。在祠堂里,能找到自己的來處。有大事的時候,我們會被喊到這里來。在祠堂里,我們會產生莫名的敬畏。大家都畢恭畢敬的,接受長者的垂詢或者教導。祠堂的邊上,就是學校,孩子們都在這里接受啟蒙。祖先在邊上,老師在眼前,孩子們也不敢過于放肆。當然,這只是鄉村肖像畫的想象部分。祠堂早就沒有了,我從沒有見過村子里有祠堂。我們缺少了敬畏,失去了儀式感,模糊了出身,我們成了一個個來歷不明的人。想想我們日復一日的行走,輕飄飄地沒有了根基,這有多荒謬。
村小學不知什么時候空下來的,我曾經在那里讀過書,我鄰村的初中同學還來學校代過課。我清楚地記得在這個學校上過課的每一位老師,教過我的,沒教我的:范老師、存祥爺爺、新華叔、孟老師、張老師、書芹(本村的女孩,我們一直同學到高中)、國民(鄰村的,我中心小學、初中同學),村子里的人們尊敬他們每一位,對他們心存感激。當父母把孩子交到老師手上的時候,會畢恭畢敬而略帶羞赧地與老師說:“老師,就當您自個兒的孩子吧,調皮搗蛋了,該罵就罵,該打就打。”完了轉身狠狠地對自家孩子說:“一定聽老師話,不聽話回家再拾掇你。”此后,父母們就不再輕易踏進這個神圣的院落。現在孩子們都出去讀書,家長接送或者坐校車。孩子們不方便了,家長也把時間耗費到接送孩子上。重要的是,好像是村子失去了某種什么東西。再小的學校,也是神圣的地方。村小學里生長著村莊文化的根。一個村莊的文脈由此綿延。聽到孩子朗朗的讀書聲,大人們就覺得生活有了奔頭。也學會克制著自己,去明禮儀……村小學成了一些人心里飄忽的影子。十幾年前,給人家做養老女婿的天增爺爺一家回到村子里,沒地方住,就買了學校暫住。沒過幾年,他們就在學校原址蓋了新房子。他們一家可曾隱隱聽到孩子朗朗的讀書聲?
祠堂、學校應該是村莊肖像畫的神來之筆,也是村莊想象的部分。村莊里,還有什么將要成為想象的部分?當想象也失去依憑的時候,村莊也就隨之消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