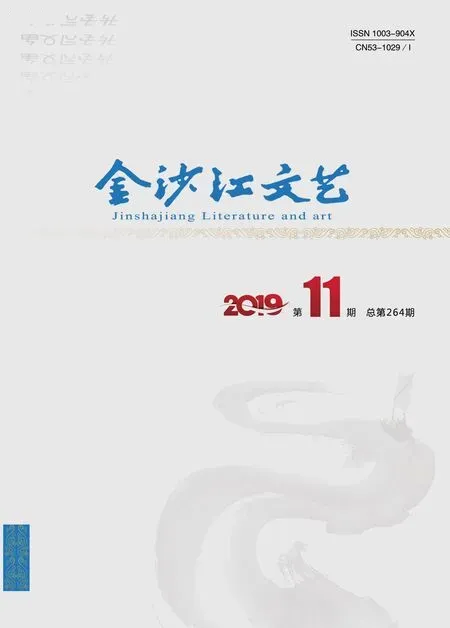還想去雙柏
◎李 剛
據說,在很早以前,這個地方有兩棵高大的樹格外引人注目,人們雙柏雙柏地叫起來,于是,就有了雙柏這個縣名。
有位詩人說,雙柏,是挺拔的,挺拔著虎虎生威的山民;雙柏,是碧綠的,碧綠著一脈纖塵不染的山水。
在我眼里,雙柏,是神奇的,神奇在原始祭祀和遠古的圖騰;雙柏,是原在的,原在著泥濘的稻場和烈烈的火犁;雙柏,是多情的,多情在“你要來的噶”交杯酒的眼神里;雙柏,是快樂的,快樂著人神共舞的大鑼笙,快樂在愛情與艷遇的大山里。
一
一位雙柏的文化人,在一部尚未出版的彝文古籍中看到這樣的記載:有一個地方,森林像大山一樣茂密,茂密的森林里有許多野獸,野獸中最勇猛的是老虎,它在族人中被稱為百獸之王。這個地方是何名何地?這部彝文古籍中沒有說。但是,根據彝文古籍中所提供的地理方位、山形地貌,有關專家考證,那個地方就是現在的雙柏。
一部彝族創世史詩《查姆》,訴說著雙柏的古老神奇。
地處哀牢山腹地的雙柏彝族文化,實際上就是以神性為主的查姆文化。從彝族文化的源頭說起,“查姆”就是萬物起源的意思,彝族相信萬物有靈,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皆有靈性,天、地、神是彝族世世代代信奉的主神。在這部《查姆》史詩中,彝人以玄幻的想象描述了天地萬物的誕生:一只猛虎倒地后,它的頭化為天頭,它的尾化為地尾,它的鼻化為天鼻,它的耳化為天耳;它的左眼化為太陽,它的右眼化為月亮,虎須化為太陽的光芒,虎牙化為滿天繁星;虎肚化為大海,虎血化為澎湃海水,腸子化為江河,虎皮化為大地,毛發化為森林。
在古代彝人社會里,彝人自稱“羅羅”,“羅”就是虎的意思,虎就是他們的圖騰,老虎、豹子作為儺的形象,登上了祭壇。在雙柏,“笙”不再是一種樂器,而是舞蹈的形式,這就產生了大鑼笙、老虎笙、小豹子笙等等儺舞名目,頑強地存活在哀牢山深處,至今雙柏還原始地保留著6500多年前虎圖騰文化,演繹著古老崇拜的活劇。
秘境雙柏,是神奇而誘人的。在哀牢山深處曾經有“九隆神話”的哀牢部落,在那片絕域荒外的哀牢國地,曾居住著古哀牢國人,留下古哀牢夷生活的遺跡。走進這片古老的土地,漫步在青山密林中,四處彌漫著山川大地的泥土氣息,把我的身心回歸到大自然;走進那篝火烈烈,笙歌動地的儺舞天地,那起起落落的舞步,把我的遐想拉回到遙遠的時代;走進祭火、跳笙現場,看到那灼熱的犁頭從火堆里挑出,祭火人光著腳踩上去,用舌頭去添冒著煙的火犁,那場面,震撼著我們的魂魄。
雙柏的朋友對我說,來到雙柏,一定要去法脿鎮小麥沖走一走,那是一個偏僻的彝族山村,村子所在的山為虎子山,村子東面的山稱為母虎山,北面的山叫公虎山。在村子東北山腳箐邊的蛇洞田附近,有一塊形似老虎的石頭,稱母虎石。村子南邊的叫魂嶺上,有虎子石。在村西通往法脿老公路的石閘門旁,有公石虎。每年正月法脿開街(趕集)這一天,小麥地沖人都要到公石虎前磕頭,凡出遠門的要專門祭祀,求虎神保佑。有專家考證,老虎笙就濫觴于此,每年的正月初八都要跳老虎笙。
藏在哀牢山深處的大麥地,也是一片神奇的熱土。大麥地峨足村的小豹子笙,一種祈福的祭祀儺舞在大山深處沿襲了數百年。每年農歷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這里的彝家人都要跳小豹子笙,大人把小孩子裝扮成小豹子的模樣,全身赤裸,臉上身上畫滿了豹子的花紋,粽葉遮面,手持棍棒,從山頭下來,在家家戶戶的屋頂上跳來跳去,從屋頂跳下來,又涌進各家各戶和莊稼地里攆鬼祛病除害,祈求平安。
大麥地還是《查姆》的故鄉,彝族創世史詩的彝文經典版本就流傳在大麥地的彝族畢摩中。1958年云南民族民間文學楚雄調查隊發現的《查姆》就是大麥地的施學生畢摩翻譯的。之后,大麥地又出現了一位叫方貴生的《查姆》傳承人,他還珍藏著一部彝文《查姆》手抄經典,這部經典,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方貴生像保護生命一樣保存著它,躲過了“破四舊”這一劫。神奇的大麥地,來過許多研究中國民族文化的國內外專家、學者,成為世界旅游者踏訪之地。
二
雙柏,我要對你說,我來晚了,沒有趕上祭神的日子。但,我趕上了法脿鎮李方村的火把節。
當雙腳踏進雙柏,就聞到了火把節的氣息,祭火、跳笙的場景使流嵐落霞的哀牢山燃燒著火一般的激情。
哀牢山上,火紅的篝火,遍野的碧綠,那紅,那綠,使人陶醉。
那是一個讓人心跳的夜晚。
2014年7月23日(農歷六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們跟隨著村民從縣城一路朝李方村走去,崎嶇的山路上,哀牢山泉水潺潺,和著沙沙的腳步聲,鄉親們手執小火把,潮水般涌向鑼笙源廣場。只有半個足球場那么大的稻場,一下子就擠滿了上千人。篝火燒紅了天,火苗飄向石鑼,我看清了石柱上的“鑼笙源”三個字,才明白為什么四面八方的村民都朝這里涌來,原來這里是大鑼笙的發祥地。
銅鑼撼動了山寨,火把映紅了臉龐,踏地而響的娛樂大舞跳出矯健的舞步,迸發出粗獷與原始律動美;人神共舞的天地,熱浪翻卷,烈烈焰焰的篝火,姑娘小伙燃燒的情感,在手牽手的舞步中和那迷人的眼眸里澎湃著。
夜幕下,我們從山上走下來,樹林里發出一陣陣嬉笑聲,我看見幾個小姑娘從樹林里躥出來,后面幾個小伙子在追,第一個追上去的小伙子緊緊地抱住一個姑娘,后面的小伙子朝前面小姑娘拼命地追……放眼望去,山上晃動著火把和電筒光,整座山成為年輕人追逐愛情的情場。
一路陪我們下山的法脿鎮鎮長楊輝對我們說,明天下午送火神更有意思,你們要來的噶。
那晚,深夜下了一場大雨,綠茵擁抱的山莊清新而寧靜。
三
一覺醒來,陽光已鋪滿遠處的山巒,云遮霧罩的村寨若隱若現。
一大早,大隊人馬就朝白竹山走去,上白竹山要經過一個山坡,當地人叫櫻花坡,坡道兩邊長滿馬櫻花樹。一到春天的三四月,盛開的馬櫻花把櫻花坡變成火紅的一片。我們是在找野生菌的季節過櫻花坡的,沒有馬櫻花,卻在這片山坡樹林里找到了小朵小朵的野生菌,這意外的收獲樂壞了這撥媒體人。過了櫻花坡,眼前是一大片草坪,草坪上開滿白色的小花,樹上吊著些不知名的野果,宛若進入到世外桃源。草坪邊上有一棵奇特的樹,一棵樹上長出兩種不同的樹,當地人叫“情人樹”,大伙兒感到很稀奇,湊過去拍照。往前走,不覺之中,我們已經進入到哀牢山深處的原始森林,眼前是遮天蔽日、郁郁蔥蔥的古樹林,腳下是松軟的落葉,各種野花散發出馥郁的芬芳,大樹上竄來竄去的小松鼠,還聽到喜鵲、布谷鳥的鳴叫聲。這天籟之音、自然之景連同我的心境一起回歸到自然……
中午,從白竹山下來,大家動手把拾到的野生菌在農家樂洗干凈,阿老表已經把土雞燉熟了,放上雞樅和野生菌,不一會,熱氣上來,香噴噴的,坐在松毛地的草墩上,美美地吃了一頓。
趕到鑼笙源廣場,已經是里三層外三層圍得滿滿的。原以為,火把節只是晚上熱鬧,沒想到這炎熱的下午,來的人更多。我從人群中擠到最里面,一個個扮成祭祀圖騰形象的彝家漢子在鑼鼓聲中亮相,跳笙(“笙”即舞蹈的意思)的一群彝家漢子將一個牛頭高高舉起,祭祀天神、地神、山神、祖先。畢摩念誦完祭祖經文之后,12個彝家漢子把氈子披在身上,裝扮成老虎的模樣,臉上繪彩,敲著銅鑼,模仿著勞動的一切節奏,在雨后泥濘的場壩上粉墨登場:犁田、栽秧、薅秧、除草、收割、入倉……師公師母戴上木制的面具,穿草衣,著短褲,赤腳與跳笙的人們共舞。鑼聲鏗鏘急促,粗獷矯健的舞步,鑼與人融為一體,發揮到極致,一招一式變幻無窮。人神對話的舞蹈場面,莊嚴肅穆的祭祀場景,震撼著我的心靈。
一些“發燒友”每個人都帶來兩個相機,輪番搶鏡頭,央視的記者也在攝像。我和同行的記者們圍向老畢摩張成興,66歲的老畢摩神氣十足,有問有答,記性特好。我湊過去聽他講了個大概。哪朝哪代他也說不清,只是說,從前,有一位皇帝落難到李方村白竹山下羅婺部落時,羅婺青年用99窩馬蜂擊敗追兵,使皇帝躲過了大難,并用苦蕎粑粑蘸蜂蜜,給皇帝充饑。為感謝羅婺搭救之恩,皇帝想封羅婺為大臣,羅婺不愿,皇帝就與他結拜為兄弟,贈給他12面大鑼,封他為大王,還下了圣旨,凡是大鑼響過的地方都叫羅婺部落。羅婺人為紀念他,就敲起銅鑼跳起舞蹈,這就是“大鑼笙”的來源。每年農歷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彝族羅婺支系過火把節都要跳大鑼笙這一傳統祭祀舞蹈,就是從李方村、者柯哨、雙壩流傳開來的。村里人舉牛祭祀,圍火起舞,從一鑼跳到九鑼,用鑼聲來訴說心中的苦情,表達所經過的磨難,驅惡除邪,祈禱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就這樣一直沿襲下來,老畢摩說得很玄,大家聽了入迷。他還說,我們這里鑼鼓一響,雨就來。還真靈驗,頭晚祭完神、跳完笙就下了一場大雨。這時的場壩上還是一片爛泥巴,跳大鑼笙的彝族漢子已經跳了十多個套路了,越跳越起勁,根本不顧腳踩爛泥沾了一身。我踏著稀泥巴擠進人群中去抓拍,戴著面具的師公師母從我身旁跳著過來,一群大人和兩個小孩跟在后面跳。在旁邊的另外一位畢摩看我拍得很起勁,湊過來對我說,這場面還是這幾年才看得到的,以前村里的年輕人并不把這些老輩傳下來的習俗當回事,后來,這里就成了鑼笙源廣場,中央電視臺的那撥人來這里拍過老虎笙以后,這幾年,火把節、虎笙節的時候,外地人來的越來越多,還有老外也來過,村里的年輕人才發現這是祖宗傳下來的寶貝,也跟著跳起來,還把小孩也拉來跳。
祭火、送火神精彩的場面還在后頭。趁跳笙的隊伍還在場壩,我們去村子里溜達,前面走來一群彝族婦女,有說有笑地忙著去廣場上跳大娛樂舞。晌午才過了一會,只見一家農戶已炊煙四起,我們走進去,主人正在忙著做飯菜,見我們來,立馬給我們沏茶,寒暄幾句,才曉得主人叫張國龍,今年輪到他們兩兄弟籌辦祭祀活動,像辦喜事一樣,全家人忙得不亦樂乎。堂屋供桌上擺放著米、酒、肉、水果及香燭,鍋灶上炒的炒,燉的燉,雞肉、牛肉、小炒肉,大鍋大鍋的。一會兒,央視的記者也來了,央視節目組的是等著拍跳笙隊伍進他們家的場景。不一會,大門外,大銅鑼開道,一對師公師母領舞,逐戶笙歌。到了張國龍家,全家老少笑臉相迎,跳笙者從院子里跳至堂屋,然后把鑼置于堂屋中央,主人端上米酒,由領頭的跳笙者吟唱彝族古歌。唱畢,鄉親們入席,主人把飯菜置于鑼面上,逐桌端了去。
到了誦經、祭火神的時候了,跳笙隊伍繞寨子一圈后,踏著松毛鋪就的石臺階來到了師公師母圖騰大廣場。一位叫畢正良的畢摩誦完經后,只見他用長棍從篝火里挑起一個滾燙的火犁放在泥土地上。這時李華文、李興仁兩位彝族民間祭火人圍著篝火跳了一圈,李興仁用光腳板踩踏冒著煙的火犁,李華文用牙齒把火犁頭叼起來,放下去之后,畢摩又挑起來,李華文又用舌頭去舔滾燙的火犁。在場的人驚叫起來。央視女記者,一邊用手摸著踩過火犁的李興仁的光腳板,一邊問他“燙傷了嗎?”他說“沒事”,畢摩在一旁說,誦過經后,有神保佑就沒事了。
踩、舔火犁結束,跳笙隊伍又圍著一堆火在跳,女的在里邊唱“啊伯嘞”(用彝語演唱的一種原始生態彝族民歌),跳開后又跳攏,最后從火上跳過去。祭火神的儀式結束,送火神歸山。由畢摩手執火把領路,跳笙者鳴鑼,隊伍隨后,向山上走去。
送完火神之后,一場豐盛的森林晚宴在灑滿松毛的地上鋪開了,老畢摩舉著一個熟牛頭,從主桌開始,一片一片劃開敬客人。席間,我問老畢摩,這里的人對火神為什么如此崇拜?老畢摩說,我從小就聽大人講,祭火神是從遠古就傳下來的,每年栽完秧到了這個時候,村村寨寨就要扎火把,點起篝火,最初是拿著火把去莊稼地里燒,驅滅蝗蟲,踩火犁、舔火犁是對火神的親近,也是民間藝人的絕活,代代傳下來的。我問這絕活還會傳下去嗎?老畢摩說,看來有點難。
回到縣城的酒店,已是深夜,沒有倦意。跳笙的鑼鼓聲、畢摩的誦經聲,還縈繞在耳畔。
我不是在夢中,而是在現實走進雙柏,走進這片神秘的熱土,這片詩意的秘境呈現給我的不僅僅是山險水秀,人杰地靈,更是古樸悠遠,無限神奇。置身雙柏笙歌動地的場景和那祭火儀式驚心動魄的場面,我看到,在這個彝人社會里,把遠古祖先的圖騰符號和陳述儀式演化為豐富完整的彝族虎文化,在世世代代彝族文化接力中,傳承著以儺舞為載體的文化內涵;我看到,雄渾的哀牢山,雄風卷揚,承前啟后的彝族兒女,繼承和發展創造著獨具魅力的彝族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社會怎樣地發達與變遷,保留文化傳統和美德的民族,是這個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