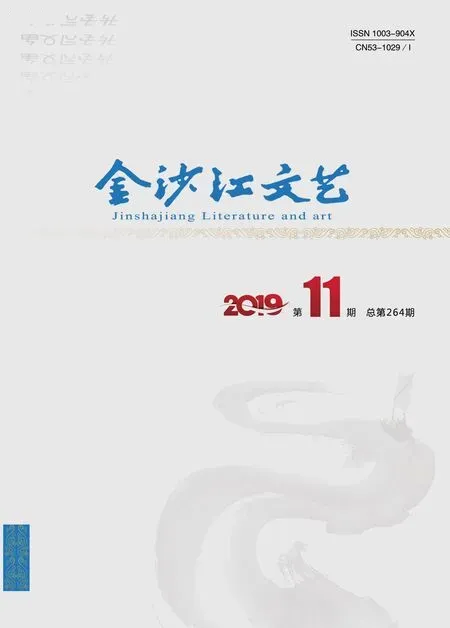高山頂上茶花開
◎李光偉
走在化湖廣場、中園廣場、彝和園青石板街道上總能聽到這首簡潔明快的左腳調:
高山頂上茶花開,阿哥阿妹跳腳來,摘朵茶花胸前戴,胸前戴,彝家姑娘人人愛,人人愛……
我認識牟定的左腳調也是從這首開始的,每當聽到這熟悉的旋律,總讓我想起諾買,她那雙清澈的大眼睛和那嬌羞如山茶的臉龐仿佛就在眼前。
1987年秋,我剛從學校畢業,被分配到一個邊遠的山區小鎮的煙葉收購站工作。和我一個工作組的是四個活潑的彝家小伙,在他們眼里我是組織分配去的國家干部,他們是季節性招去的臨時工。可我一心向往城里,并不關心小鎮的一切,也不計較他們用那我聽不懂的彝話整天嘰嘰喳喳說話。
看得出他們的帶頭人是瑞哥,由于他們工作熟練能吃苦,工作就這樣順利的進行著。
一個趕集天,收購場上賣煙葉的群眾很少,瑞哥不知什么時候悄悄溜了。回來的時候似乎很興奮,他們在說著什么,討論著什么,不時地亮出一支翡翠手鐲。最后仿佛決定了什么,慎重地來向我報告。
瑞哥在集上遇見了九道箐的姑娘們,和她們說成了一回“日子”。三天后和姑娘們在高山頂“趕熱鬧”。對方有五位姑娘,一定要我也參加。他們反復說明后,我似乎理解了一些。這“趕熱鬧”就是集體約會,“說日子”就是口頭說下約會的時間地點。一般姑娘都會取下手鐲,有信物為證。
看得出小伙子們很是期盼三天后的約會,工作之余他們把弦子調了又調,用松脂把那二胡的馬尾擦了又擦。看得出那三天他們都在為約會而興奮著。
夜幕低垂,附近村里隱約傳來弦子的聲音,小伙們急急地做完了收購場上的活。飯后,匆匆忙忙換上那繡滿山茶的彝族服裝悄悄地出了門。出門,瑞哥要我拼了一塊八角錢到供銷社買了一背簍糖果、餅干、菠蘿汽水。
順著一個山梁子往前走,月亮升得越來越高,把汪洋一樣的彝山朦朧得如詩如幻。山風徐來,松濤陣陣。我似乎忘記了這是去“趕熱鬧”。小伙子們很習慣走這樣的山路,一路把弦子彈得錚錚響。
高山頂是一個真真實實的地名,在山梁的盡頭。密密的松林里突然空出一塊足球場大小的草場。月華如水,山梁、松林、草場,一切仿佛在牛乳中洗過一般。一股久違的興奮竄上了心頭,興奮的不是要與姑娘約會,是那山風,是那月色。
我們到的時候,姑娘們也到了。看得出他們都很熟悉,相見甚歡,不停地笑著,不停地嘰哩咕嚕地說著彝話。那個看去安靜,顯得很孤單的就是諾買了。瑞哥把我介紹給了她。
平日里聽這些小伙子們彈弦子,節奏簡潔明快,總以為左腳舞也很容易跳的,如在學校里跳迪士高、跳交誼舞一樣,只要踩著鼓點就是。可那晚高山頂上的左腳舞讓我出盡了洋相,無論我怎么仔細聽,都踩不合節拍,出腳總是不一致。這一身格子衫、牛仔褲也與他們格格不入。與他們優美的舞蹈相比,我簡直是小丑。兩圈下來,已是汗流浹背。只好退出,枕著月光看他們盡情地揮灑青春的旋律。
總想在他們優美的舞姿中找到固定的規律,可是每一支調子都有單獨的舞步,不論是直腳、踮腳、崴腳、對腳、合腳,看去都是靈活自如、輕盈飄逸。我退出后,舞圈里的諾買顯得那樣的孤單和多余。
“高山頂上茶花開,阿哥阿妹跳腳來,摘朵茶花胸前戴,胸前戴,彝家姑娘人人愛,人人愛……”
“小郎也合妹的心,小妹也合郎的意,郎合心妹合意,合心合意做一家。”
“隔是隔山箐,箐呀箐隔山,隔山阿老表,你要來呢嘎,隔山隔水不隔心,做姊做妹要真心。”
一曲過后又一曲。她們熱情、摯著地把自己的感情全都傾注了進去,弦子的音調也就特別悠揚歡快,舞步更是優美翩翩,小伙子們的動作矯健有力,精心打扮過的姑娘們都如同一朵朵鮮艷的山茶花。
也許是跳累了,也許“趕熱鬧”的形式就是這樣,這時大家坐下來喝酒,吃餅干。雖然我聽不懂,可還是感覺到了他們聊得那樣真情,那樣開心,笑聲隨月光灑落山谷,灑落草地,灑落樹林。
這時諾買也坐到了我的身邊。諾買是個身材修長而俊俏的姑娘,一雙大眼睛在月光下更加清澈,跳腳后,紅紅的臉龐一如盛開的山茶。我不知道與她聊什么,分工的不如愿,心情長久地壓抑著,此時只想頻頻舉杯邀明月。
諾買從她的背簍里拿了她家自制的火燒干巴遞過來:“少喝點酒,回去的山路你走不慣。”雖然有著濃濃的彝家口音,我還是感到了溫柔,感到了關懷。
月亮被跳得越來越低,眼看就要落到山那邊去。舞曲少了那開始時的歡快,多了一份離別的愁緒。“阿老表,天亮了,阿表妹,天亮了,小小公雞叫呀叫三聲,天亮不亮送你回家了……”看得出他們是多么的依依不舍。雖然感覺自己始終只是一個旁觀者,此時也是眼里噙著淚水一起返程的。
回到收購站已是深夜,我問那姑娘叫什么名字,瑞哥睡意朦朦地回了兩個字“諾買”。那夜,諾買沒有入我的夢。
此后的許多天里,小伙子們一直興奮在這高山頂上“趕熱鬧”的情緒里。對這次“趕熱鬧”似乎有說不完的話語。我一樣的組織著驗級、過磅、入庫、開單、付款的工作。
一個多月后的一天,瑞哥又說成一回“日子”,依然是那個手鐲,依然是那五個姑娘,依然是高山頂,我勉強答應了他的再三要求。小伙子們又開始興奮和期待。一樣的調弦,一樣的準備晚上高山頂赴約。縣公司突然來了電話,說我們站在煙廠的驗收中降級嚴重,必須立刻翻庫整改,等待第二天縣公司的檢查。站長訓話后,小伙子們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加班至凌晨兩點,平日嘻嘻哈哈的老表們那一晚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清晨,睡意正濃。老站長站在陽臺上罵開了,收購站的大門被用白刺花的枝條柵得嚴嚴實實。很快真相就大白了,這是姑娘們對失約男人的懲罰。油嘴滑舌的瑞哥此刻低沉著頭任憑老站長訓話。其余小伙子們也低頭沒有一點聲息。我忍俊不禁。結果是:瑞哥必須寫一份檢討,深刻認識不誠信給收購站聲譽造成的不良影響。當天瑞哥必須請假去九道箐向姑娘們道歉。我們又每人湊了一塊八角錢給瑞哥,說是還手鐲用的錢。
傍晚,瑞哥滿面春風地回來了,姑娘們不僅原諒了他,還把他招呼得酒足飯飽。收購場上依然歡聲笑語。
收購快要結束的時候,姑娘們約著來交售了一次煙葉。她們在大門外的水池邊洗過臉,換好自己縫的繡滿山茶的服裝才進來,姑娘們并不在乎自己的煙葉檢成什么等級。不管小伙子們說什么也只是笑,相比諾買依然安靜,依然孤單。只是總覺得她衣上繡著的山茶比別的要盛開得更鮮艷。
走的時候,諾買從小背簍里拿出一包軟軟的東西送給我,我準備打開時被她制止了,再一看她,哦,“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我只能是道一聲珍重。
諾買送我的是一件粉藍色的繡著山茶的彝家小伙穿的上衣。衣袋里裝了兩包春城牌香煙。衣服試穿過一次,很漂亮。香煙兩天就抽完了。
收購季快結束的時候,工作很清閑。小伙子又開始唆使我和他們一起去竄姑娘房,說諾買也在其中。我知道竄姑娘房是要和姑娘們和衣同床共眠的,那該是多么尷尬的事。也不知怎的,當時竟說出了那句讓他們笑話很久的話來:“我可是國家干部,怎么能同你們這樣去亂精神呢?”
終于我能調離那小鎮,那晚用大碗和小伙子們喝酒。三碗過后想起諾買,便囑咐他們抽空去看諾買,代我向諾買問好。他們還是那樣鬼鬼地笑。終于明白,諾買只是彝家對姑娘的統稱,我連那姑娘的真實姓名都不知道。
此后的時光里,偶爾有走在彝家那些山梁上的機會,常看到那林間空出的草場上有一圈一圈的不長草的印跡,像一朵朵盛開的山茶。我知道那是小伙子們跳腳“趕熱鬧”的地方,是約會的情場。
隨著歲月的流逝,那件繡著山茶的粉藍衣裳是穿不上了,越來越感覺當年年少不更事。那山風、月色、草場、諾買、小伙子們、甚至老站長的訓話都是那樣美麗,想起都還在心底嫵媚。
你現在好嗎?流落在了哪個人的夢境里?那里也是繁花似錦,嫵媚翩躚嗎?
如果今生不曾錯過,在化湖、在縣委廣場、在彝和園或是隨一處的農家小院,就著這《高山頂上茶花開》的旋律,一定有我們共同揮灑激情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