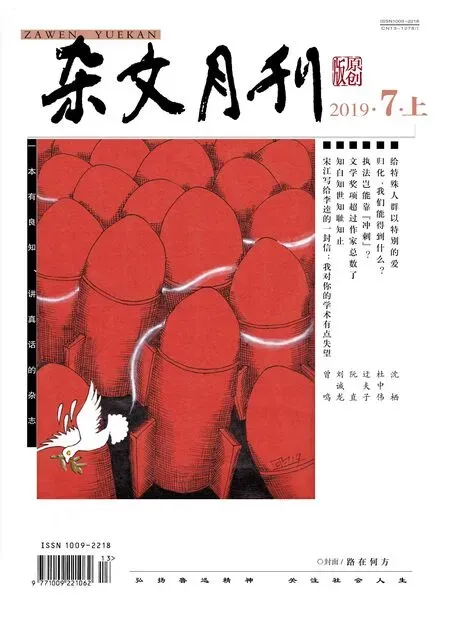唯有廉者真愛國
●張桂輝
唯有廉者真愛國。這是四月底的一天下午,在福建莆田與近百名雜文家、雜文人同謁“玉湖陳氏祖祠”得出的“結論”。位于莆田市區荔園路1026 號的陳氏祖祠,26年前,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那天,我在進入祖祠之前,發現門廊兩側,懸掛著“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兩塊豎書標牌,牌子不算醒目,卻吸引我的眼球、引發我的思考。隨后,一番參訪下來,心中肅然起敬的是,發生在玉湖陳氏身上濃烈的愛國情懷、可敬的清廉之舉。
玉湖陳氏始祖陳仁的四世孫陳俊卿,以榜眼及第,官至左相。他為官清廉、忠義直諫、不畏權勢、任人唯賢,是宋代著名的忠臣賢相。有“理學廉臣”之譽的俊卿四子陳宓,嘉定三年(1210年)秋,調任安溪知縣。當有縣吏依“慣例”向他送上各種不必上繳、可自行支配的銀子時,陳宓正色道:“一旦這錢成為私有,便是贓物了。這個‘慣例’,壞了多少賢士大夫啊!”當即下令,把錢歸入縣庫。民族英雄、陳俊卿五世重侄孫陳文龍,其仕途“第一站”,是今浙江紹興越州鎮東節度使判官。上任伊始,便毫不猶豫地舉起革除政弊之劍,揮動反腐懲奸之斧,公開聲言:為官“不可以干以私”。后來,陳文龍官至監察御史,不辱使命,秉公執紀,屢屢彈劾曾經極力舉薦他、又想利用他的權臣賈似道。咸淳八年(1272年),臨安知府洪起畏,在賈似道授意下,推行用劣等公田強行更換肥腴良田的“類田法”,導致“六郡之民,破家者多”。陳文龍慷慨上疏,終于逼迫賈似道廢除此法,黎民百姓稱贊其“乃朝陽之鳴鳳也”……
這些青史留名的玉湖陳氏,所以忠貞節義、愛國清廉,與其優良家風,密不可分。以陳文龍之叔陳瓚為例,雖是一介平民,卻身在莆陽,心懷天下。宋末,政治腐敗,元軍侵擾,天下大亂。值此危難之際,家有遺風的陳瓚,時常散發糧米,以濟饑寒百姓。他說:“吾家世受國恩,當為國收民心耳。”德佑元年(1275年)春,元朝大軍沿長江東下,南宋政權瀕臨崩潰,朝廷重新起用陳文龍為侍御史。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興化城陷落。文龍被俘,陳瓚義憤填膺:“侄不負國家,吾當不負侄。”于是,秘密部署,招募義軍,誓死抗元。次二年十月十五日,元兵攻破興化府城墻后,拒不歸降、年僅45 歲的陳瓚,被唆都下令五馬分尸。公道自在人心。陳文龍以身殉國,陳瓚壯烈犧牲后,分別獲謚“忠肅”“忠武”。因而,叔侄二人并稱“抗元二忠”。
離開玉湖陳氏祖祠多日了,“愛國”“廉政”連同上述兩塊牌子,不時在腦際浮現,聯系到陳俊卿、陳文龍等人的壯舉廉舉,心中感慨良多。白居易有詩曰:“惟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由此推論,當今少數腐敗分子,涉案金額,動輒幾百萬、幾千萬,不論是貪污,抑或是受賄,從小處講,是在刮民脂民膏;從大處講,是在挖國家墻腳。至于外逃貪官,更是令人發指。以“百名紅通人員”為例,他們不論職務高低、身份如何,哪個不曾接受過愛國主義教育?哪個不知為政清廉的要義?可是,當他們狐貍尾巴行將暴露時,一個個如喪家之犬,惶惶然逃到國外。據悉,四年多來,先后已有56 人歸案,其中不乏主動回國投案者。如,“紅通”頭號嫌犯、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其輾轉多國,逃亡時間長達13年,曾經聲稱“死也要死在美國”。假如不是我國反腐追贓力度大,且其后期在美國成了“無人可靠”“無錢可花”“無路可走”的三無人員,說不定至今還心甘情愿寄人籬下呢。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之間以及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都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的。綜上所述,頓有所悟:愛國與廉政,并非相互孤立的,而是有內在聯系的——真心愛國,必須廉政;唯有廉者,方真愛國。反之,既無“愛國”可言,更不配說“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