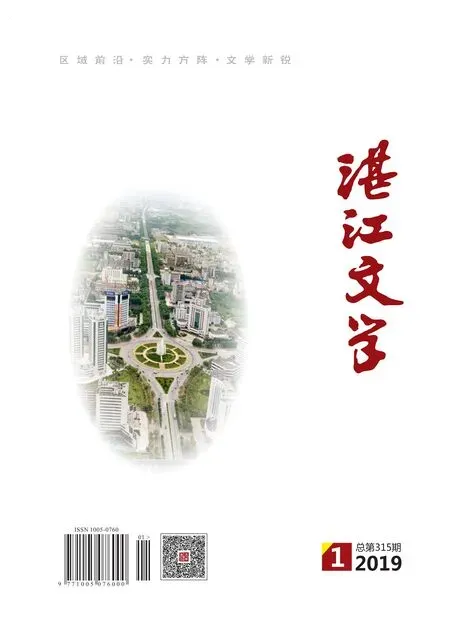古老埠頭一畫癡
◎龍 鳴
大通街繁盛于清初。舊時鋪砌路面的青石、苔蘚斑駁的商鋪,以及梯級踏跺式的古埠頭都還在,只是舊瓶裝了新酒。繁忙嘈雜的新日子,過久了也成為立體復印的尋常生活。可是,自2015年10月27日開始,人們突然感覺不同了。五號埠頭附近的那間四壁蕭然小房子的燈滅了,大通街上,華珠踽踽行走的身影消失了。零星分布老街各處的古井,依然只眼望天,可它們的凝視中,再也沒有華珠的倒影。在這里生活超過十年的人,潛意識中會以為已經習慣的尋常生活會永遠重復。可是,華珠退場了,人們感覺少了一種聲音,那種聲音,雖然單調、單純,但是悠揚,優美。人們感覺少了一層色調,春夏秋冬,大通街上的枇杷樹雖然不乏色彩變幻,但是遠不如華珠所展現得豐富。少了這么一個不起眼的人,沒想到如此扎心。華珠的死,其實是赤坎古街上的一次精神事件。
判斷人的社會價值有個簡單方法:看哀榮。華珠一生孤苦,身后哀榮卻異常隆重。他的獨特與執著感動了無數粒柔軟的心,捐款者逾百上千,皆取于升斗。孩子們也受到感染,收斂頑皮嬉鬧,省卻嘴邊零食,對逝去的老畫家鄭重致敬。街坊們專門成立委員會,為他辦畫展,出畫冊,完成他一生的奢愿。一時間,一陣華珠風起,電視報道,報刊發文,名人唁電致哀,朋友著文追悼……華珠生前從來沒有如此風光!
華珠是個苦人,姓梁,祖藉茂名,流落湛江。初中畢業后到湛江市博物館就職,跟隨畫家鐘錦濤學畫,文革中失去工作,又患疾病,從此陷入死循環:無工作——無收入——無體面——無妻無后,孤苦無依。最苦的那些年,冬天蓋報紙取暖,在控制不住的牙齒咯咯聲和報紙瑟瑟聲中,度過漫漫長夜。幸而,湛江的冬夜雖然寒濕,卻少了奪人性命的嚴酷,才把他留給翌日的太陽。雷州半島,是可以把生活成本壓得極低的地方。華珠是個孤身男人,又出入藝術殿堂。對女性美自然會有欣賞和追求,就他的情況而言,這種追求只能是單向的。他在深街古巷追女子,眼睛里放著光,讓人忌憚或害怕。很快就有綽號加身:花癡。
梁土富先生在悼文《傷逝》中說:“華珠日子好過些,是自認識老友胡賢光開始。”
胡賢光祖藉浙江,在赤坎老街長大。從小在街上跑,隱約有“花癡”的故事從耳邊飄過。直到2004年,在市工商聯工作的老胡開始分管赤坎廣州灣商會舊址,經常舉辦一些書畫展覽。住在附近的華珠天天跑到商會,纏著要賣給他畫,以濟炊米。
胡賢光翻看華珠的畫,喜歡,更多是同情。便聲稱要”收購“他畫,并動員愛心人士購買華珠的油畫。梁土富說:“有能力就支持,當做善事也罷,老友開始了每月定期資助華珠,為其呼吁有關部門、朋友的贊助,以改善其生活”。
華珠無緣專業訓練,但一直追求專業色彩。他潛心臨摹世界名畫,最心儀的是19世紀俄羅斯杰出的風景畫大師列維坦。列維坦滿懷深情地把伏爾加河畔的天空、森林、河流、土地分別置于黃昏、傍晚暮色中,用一幅幅驚世杰作揭示大自然與心靈的神秘聯系,在每一個細微處與它們深情對話。列維坦的生活也與華珠一樣,凄涼、慘淡。他在畫面上發出的余溫,表達的愿景,一把一把地扯動著華珠的愁腸。只要能吃飽,華珠就整天蜷
在他十平方的小房里,呆呆地盯著列維坦的畫。此時他的靈魂飛出貧病交加的軀殼,飛過四壁蕭然的蝸居,飛越嘈雜的赤坎市井,飛向那遼闊的荒野。闊海邊,巨流旁,星空下,往往有一座孤伶伶的小屋,或者一條單薄的小船,在大自然的遼闊中,渺小、孤獨、凄美。那里似乎有人煙,有溫情,有慰藉淪落人心田的暖流。華珠鉆入畫中,久久盤桓,直到蹲麻的腿和轆轆饑腸把他喚回小屋。華珠有這樣一幅畫:天空云層交疊,極高處黢黑,中間層是巖石般的鋼色冷藍,與地平線相交的低端云層得到夕陽暉潤,散發出溫暖的柔情。云層下,草地上,光與影和諧之處,有兩個渺小的人兒深情相擁。華珠題此畫為《天空也溫暖》。讀此畫,想想華珠身世,想想他的花癡”綽號,真使人情緒澀滯,淚腺酸塞不得暢流。華珠一生足不離大通街,可他在畫中卻走得很遠,且看他為畫作題的名字:《遠方的路》《金色的原野》《湛藍的天空》《春的腳步》《靜湖》……
老友的呼吁和推廣成效顯著,有人來看望和資助華珠。華珠腰包偶爾鼓起來,臉上就會泛出紅潮,眼神迷離,胸中欲望奔突。這時他會離開蝸居,四處亂走。一種陌生的幻像吸引著他,他大量購買彩票,想把眼前浮現的海市買下來,這種心神不寧的等待讓他多日不碰畫刀,直到希望破滅。
這時的華珠,最渴望有人欣賞他的畫,讓他沉浸在被人尊重的價值感中。老胡說:“從華珠多彩的畫面中,你可以感覺他的內心是快樂幸福的,他永遠會陶醉在作畫的歡娛中。每當畫畫,他就活在這幅畫里,外面的世界與他毫無關系。”老胡的“收購”讓華珠變得勤奮,他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這里沒有妄想、算計、猜忌、等級、敵意、諂媚,只有信任、興致、追求和詩意。老胡和朋友給華珠鋪展開一塊綠草地般的畫布,足可放養他的興致和詩意,任他畫出心中的濃綠與蒼涼。梁土富說,有了生活保障的華珠,“畫面那層灰暗的天空少見了,色彩變得明亮燦爛起來”。給老胡交了畫,華珠會把沒有捂熱的錢分出一點,到市場買兩條蝦,舉著走過街市,遇到古井他會往里面端詳半天,照一下自己幸福的身影。
老街坊們接力似經久不息的佑護,使華珠有條件,有精神進行高貴的心靈追求。十余年間,華珠的人設慢慢被修改:從“花癡”到“畫癡”,再到“赤坎老街上的梵高”。
一個好奇的追問一直盤旋在所有人腦際:華珠的畫,藝術價值如何?有人說他清醒時畫得好,有人說他糊涂時畫得好。為此,我把華珠的畫冊拍成照片,專門請教我高中的同學,曲師大美術學院院長,著名畫家張煬。張教授說:這位老畫家的畫有特色,但一些畫太“行”了。這是美術界的術語,張教授解釋說,所說“行”,是隨行就市的“行”,有媚眾的意思。我理解,華珠“清醒”之時,為換取稻粱,心目中掛上畫商和無數雙大眾的眼睛,在他們的品評中,用學到的技法不斷修改畫稿,偶爾追求俗套的流行樣式,把自己胸中奔突的想法丟到一邊。所謂“糊涂”之時,是他創作生涯最為珍貴的時刻,此時,他完全放松,忘掉功利,不管技法,也就掙開了枷鎖,畫刀隨意切涂,揮灑胸臆,把從心中長出來的情感意像涂在畫布上,留下只屬于自己的精神風光。翻看老胡的收藏,這樣的畫不在少數。
后人閱讀這段歷史,會感到華珠像一顆孤獨的流星緩緩劃過赤坎老街歷史的天空,不太明亮,但悠長。在那些與他生活在同一風俗畫框中的人們心中,在雷州半島的繪畫史上,留下長長的光痕。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說:假如生命有根基,那么它就是記憶。華珠歷盡磨難的肉身已去,其獨特的形象卻存在于那么多人的記憶中。等這些記憶消失了,那些畫還會流傳。或許在幾百年后,還會有收藏者沿著傳世的畫作追尋、追憶作者生平。這么說,也算是青史留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