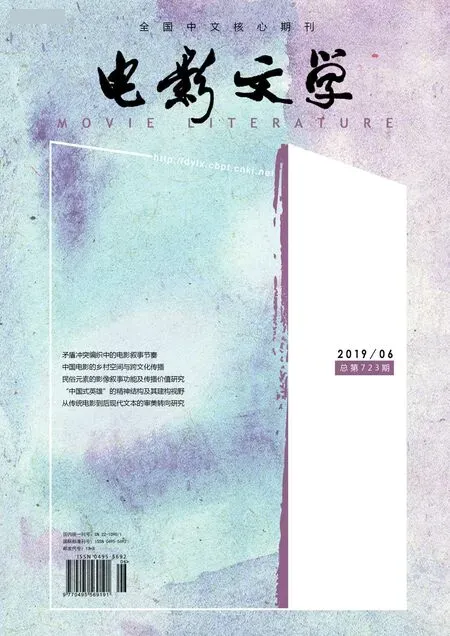民俗元素的影像敘事功能及傳播價(jià)值研究
孟改正 (寶雞文理學(xué)院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陜西 寶雞 721013)
民俗文化的誕生可以追溯到人類形成群居生活之初,群居的社會性決定了民俗文化本質(zhì)是一種規(guī)約與認(rèn)同。影視藝術(shù)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物,通過光與影的巧妙結(jié)合投射社會與人倫的演進(jìn)變化,為人類提供了反觀自身生存狀態(tài)、審美追求的一面鏡子。影視與民俗的風(fēng)云際會是兩種藝術(shù)形式相隔千年的探尋與碰撞,民俗的異彩紛呈為影視提供了豐富而真實(shí)的社會底蘊(yùn),影視的流光溢彩提升了民俗文化的特性與質(zhì)感。電影中民俗的構(gòu)成復(fù)雜多樣,地域建筑、服飾飲食、婚喪嫁娶等民俗元素具備影像敘事的內(nèi)在推動與外在拓展功能,影像作品為民俗文化的表達(dá)與傳承搭建了傳播平臺。
一、民俗文化對影像敘事的內(nèi)在推動功能
影像敘事的內(nèi)在張力通過人物形象、故事情節(jié)、影片主題三方力量推動完成。
(一)特殊場景著力再現(xiàn),塑造人物形象
人是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會塑造出性格迥異的區(qū)域人物特點(diǎn),而相似民俗環(huán)境下的個(gè)體會有相近的歸屬感。影視作品中的特殊場景正是用來交代故事發(fā)生的環(huán)境或者背景,是故事主人公形象塑造的著力點(diǎn)。由陜西作家陳忠實(shí)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白鹿原》,開篇即為俯拍陜西小麥成熟的移動鏡頭,王全安導(dǎo)演不惜用兩分鐘的鏡頭展示關(guān)中地區(qū)麥浪翻卷的自然場景,正是為后面出場的諸多人物形象提供環(huán)境支撐,側(cè)面點(diǎn)明了北方農(nóng)耕文明為主的自然村落養(yǎng)育出了恪守族規(guī)的白嘉軒、勇敢耿直的黑娃以及坦蕩大膽的田小娥,這群生活在大西北的人物身上具備從古至今烙下的典型地域性格特點(diǎn)。隨著情節(jié)的進(jìn)展,原野上風(fēng)吹麥浪的場景鏡頭多次出現(xiàn),重復(fù)蒙太奇的剪輯技巧象征了白鹿原上的這群人如麥子一樣,無論戰(zhàn)火摧殘還是國事動蕩,他們的堅(jiān)忍頑強(qiáng)是這一方土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保障。
(二)異域風(fēng)情彼此碰撞,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
情節(jié)的起伏演進(jìn)是影像作品講述一個(gè)好故事的必要條件,懸念、矛盾、沖突是構(gòu)成故事情節(jié)一波三折的重要元素,這三者最終要通過影像作品的人物命運(yùn)變遷完成。個(gè)體所持有的文化意識受特定的民俗觀念影響,不同生活背景下的民俗生活積淀,會讓個(gè)體在面對同一現(xiàn)象中呈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反映,影片中具有異域風(fēng)情的民俗觀念碰撞形成沖突,能夠推動故事情節(jié)有序發(fā)展。最典型的例子來自電影《刮痧》,刮痧是一種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醫(yī)療保健手段,但美國人缺少對東方這種古老而又傳統(tǒng)的民間醫(yī)術(shù)的認(rèn)知與體驗(yàn),本國又格外重視懲治家庭內(nèi)部的暴力傷害,他們憑借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判斷孩子背上的紅印痕是家人虐待兒童,影片正是在東西方民俗文化的差異化中展開敘事情節(jié),完成對人性美的主題呈現(xiàn)。
2012年拍攝于陜西渭南的電影《孫子從美國來》,就是通過中美不同民俗背景下生活的中國爺爺和非血緣關(guān)系的美國孫子在生活習(xí)慣、語言表達(dá)、行為方式、思維見解以及文化觀念等諸多方面的對抗、排斥,形成電影情節(jié)的矛盾、沖突。二人經(jīng)過波折不斷的相處到最后爺孫彼此包容、接納,凸顯了長輩對晚輩的關(guān)切愛護(hù)以及雙方從對立走向友好的過程。這部影片同時(shí)揭示出隨著民俗環(huán)境的改變,處于其中的個(gè)體也會不斷去接受新事物及適應(yīng)新的民俗風(fēng)格,比如影片中的爺爺盡可能滿足孫子吃漢堡、喝牛奶的飲食習(xí)慣,孫子也接受了一頭金發(fā)被爺爺強(qiáng)行染成了黑色的事實(shí),影片的情節(jié)正是圍繞一老一少從相互抵觸、認(rèn)可再到建立感情展開。
(三)本土藝術(shù)傳承聚焦,深化創(chuàng)作主題
圍繞本土民間藝術(shù)傳承問題展開的影片,主題都非常明確,即著力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與保護(hù)。此類影片常常憑借其中典型的藝術(shù)符號,深化創(chuàng)作主題。“一些以民間藝人生活為題材的影片中所展現(xiàn)的民間藝術(shù)形式都為拓展和深化影片主題起到了重要作用。”[1]電影《百鳥朝鳳》就將鏡頭聚焦在西北一個(gè)以吹嗩吶聞名的小村落,反映嗩吶這門民間藝術(shù)在當(dāng)下社會的境況以及幾代鄉(xiāng)間藝人堅(jiān)守與傳承的主題。影片在闡述這一主題的基礎(chǔ)上,通過嗩吶這個(gè)意象符號深化了主題,表達(dá)出對鄉(xiāng)間德行、禮儀的信守,“嗩吶演奏作為民俗儀式既是一種儀式過程的象征,也是一種精神意義的象征”[2]。比如焦三爺強(qiáng)調(diào)嗩吶藝術(shù)的巔峰之作“百鳥朝鳳”只給那些德高望重的亡人演奏,這是對他們?nèi)松鷥r(jià)值的最高肯定,觀者聞之無不萌生敬仰之意。焦三爺在選擇嗩吶繼承人的時(shí)候,放棄了天資更高的徒弟,看中了善良、執(zhí)著、大義的游天鳴,對這門傳統(tǒng)而古老的民間藝術(shù)而言,能堅(jiān)守藝術(shù)的德行更為可貴,這也在告訴眾人,用人方面品德重于才華。嗩吶聲聲,這門民間藝術(shù)不僅帶給觀眾藝術(shù)的熏陶,更是對一方精神力量的傳揚(yáng)。這種精神在或悲壯、或激越、或熱烈、或憂傷的嗩吶聲中直抵人心,無形中產(chǎn)生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形成特定區(qū)域內(nèi)群體公認(rèn)的價(jià)值觀、世界觀。
二、民俗文化對影像敘事的外在拓展功能
民俗文化對影像敘事的外在拓展功能要借助構(gòu)圖、光線、色彩、聲音、畫面隱喻與象征等影視技巧完成,注重挖掘影像自身的講述能力,動態(tài)承載故事進(jìn)程。
(一)色彩影調(diào):增強(qiáng)視聽沖擊力,調(diào)整敘事節(jié)奏
影視劇中的場景是物質(zhì)民俗的一種,場景設(shè)置與畫面的影調(diào)選擇息息相關(guān)。影調(diào)是影視作品結(jié)構(gòu)、色彩、光線的客觀再現(xiàn),能起到藝術(shù)展現(xiàn)導(dǎo)演創(chuàng)作意圖與表現(xiàn)手段的雙重作用,取景范圍、拍攝角度、光線構(gòu)成都能影響影調(diào)的構(gòu)成。影調(diào)本身帶有一定的感覺能量,比如高調(diào)給人以明快、輕松的感覺,是光明、溫暖的象征,低調(diào)則意味著故事主題的肅穆、悲涼。不同的影調(diào)選擇是導(dǎo)演對影視劇人物的立場、情緒、情感的把控,它既是導(dǎo)演對影視作品創(chuàng)造性的體現(xiàn),又是導(dǎo)演通過視覺刺激激發(fā)觀眾情緒和想象力,引領(lǐng)大家體悟故事情節(jié)之外的創(chuàng)作意圖。“影視藝術(shù)具有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而且直觀感受性非常強(qiáng)。人容易接受其傳達(dá)的思想和文化內(nèi)涵、民俗事項(xiàng)等。”[3]以陜西本土電影《老腔》為例,它是國內(nèi)第一部以陜西非遺藝術(shù)老腔興衰存亡為主題的作品,電影影調(diào)以中間調(diào)為主體,灰色是主打色彩,這種色彩運(yùn)用到大自然場景上,能使景觀呈現(xiàn)出素雅、恬靜、柔和之美,既表現(xiàn)了鄉(xiāng)村生活的寧靜,又使影片整體籠罩著一種莊重、肅穆之美,灰色本身的厚重還體現(xiàn)了老腔藝術(shù)在歷史發(fā)展長河中遭到冷遇的悲涼現(xiàn)實(shí)。
(二)音樂音響:渲染人物情緒,烘托作品氣氛
民間的音樂音響帶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與民族傳統(tǒng),在烘托氣氛、渲染情緒方面有獨(dú)到的價(jià)值,能增強(qiáng)影像作品藝術(shù)感染力。電影《白鹿原》中大篇幅展示了一段原汁原味的老腔民俗藝術(shù),華陰老腔作為陜西地域流傳千年的民間藝術(shù),如黃土般厚實(shí)樸素,“體現(xiàn)的是數(shù)千年來陜西民眾最基本的生存法則,傾訴的是關(guān)中民眾的勇武和頑強(qiáng)”[4]。麥客們投入聆聽同伴酣暢淋漓地唱了一段老腔,黑娃端著大老碗聽得癡迷,老腔熱烈躁動的韻律足以激發(fā)年輕人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和狂熱,勇武的黑娃與大膽的田小娥命運(yùn)的膠著相連正是從此處展開。老腔輔助故事的敘述,在這里起到了一定的渲染情緒、烘托主題的作用。老腔倔強(qiáng)而開放的藝術(shù)內(nèi)蘊(yùn)暗示了兩個(gè)年輕的生命敢于沖破世俗的禁忌,從彼此愛慕走向相親相愛,老腔高亢而又沙啞的唱腔是他們克服重重阻力生活在一起的寫照,但同時(shí)老腔無畏悲愴的厲聲嘶喊也渲染了他們的感情坎坷悲情的結(jié)局。
(三)畫面意象:選取民俗形象,形成敘事隱喻
民俗文化涉及社會各個(gè)層面,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一些民俗場面被契入影視情節(jié)中,既是再現(xiàn)正常生活的需要,同時(shí)又可以在其中寄寓多重文化或思想含義,構(gòu)成敘事隱喻性。以飲食文化為例,飲食是人類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我國飲食文化源遠(yuǎn)流長,成為中華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傳統(tǒng)飲食文化恰當(dāng)?shù)剡\(yùn)用到電影創(chuàng)作中,不僅有助于影片鋪陳情節(jié)、塑造人物,還能負(fù)載諸多或直觀或抽象的文化信息。“從我國傳統(tǒng)觀念來看,儒家文化曾明確提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用人類不可或缺的‘飲食’來類比人們的生理或情愛欲望,可謂十分貼切。”[5]電影《白鹿原》中有兩處關(guān)于飲食的隱喻性敘事,起到了對劇中人物情愛表達(dá)與欲望發(fā)泄的象征作用。一是端著大海碗吃面的黑娃夸贊小娥做的面好吃,面條作為北方人最喜愛的主食,營養(yǎng)豐富、制作簡單,是普通老百姓踏實(shí)過日子的基本保證,一碗面見證了兩個(gè)年輕人的情愛滋生就是為了在一起好好過日子;一處是鹿子霖借著幫田小娥打探黑娃消息來到她家,小娥為他準(zhǔn)備了酒菜。酒文化在中國有多重寓意,可鼓舞士氣、消解憂愁,亦可使人沉迷墮落、忘乎所以,鹿子霖借著酒力侵犯小娥,不過是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發(fā)泄欲望。可以說,影視作品中的飲食場面在發(fā)揮敘事功能的同時(shí)還兼具表意潛能,成為增強(qiáng)影像藝術(shù)特性的有效元素。
三、影像藝術(shù)對民俗文化表達(dá)的傳播價(jià)值
(一)通過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賦予民俗文化新的生命力
影像藝術(shù)是視覺沖擊力較強(qiáng)的感性傳播介質(zhì),民俗是一定的歷史積淀形成的文化體系,民俗文化通過感性的傳播載體呈現(xiàn)在大眾面前,要經(jīng)過一定的藝術(shù)轉(zhuǎn)化與加工,才能實(shí)現(xiàn)二者有機(jī)契合。影像藝術(shù)極強(qiáng)的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功能,一曲百鳥朝鳳的影視版演奏能通過鏡頭的翻轉(zhuǎn)變化、節(jié)奏的靈活調(diào)整、影調(diào)的巧妙處理,尤其是對當(dāng)事人藝術(shù)形象的傾情塑造,多方因素通力合作,極大可能打造出比現(xiàn)場版更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民間藝術(shù),這也是新舊藝術(shù)融合、共同走向更有影響力的雙贏選擇。
《老腔》《百鳥朝鳳》等塑造了一個(gè)個(gè)頗有個(gè)性的民間藝人形象,作品對執(zhí)著于老腔、嗩吶演奏的兩代人形象的著力刻畫,既有對他們堅(jiān)守古老技藝的尊敬,也深切表明依然有那么一批人用他們的熱血、生命維護(hù)著面臨衰落的傳統(tǒng)民間藝術(shù)。此類影片最突出的藝術(shù)價(jià)值在于讓生活在影像時(shí)代的年輕觀眾領(lǐng)略到老腔、嗩吶的藝術(shù)魅力,折服于民間藝人堅(jiān)忍頑強(qiáng)、古樸執(zhí)著的精神品質(zhì),倡導(dǎo)更多的相關(guān)人士為保護(hù)、傳承它們盡一己之力。可以說,以反映傳統(tǒng)民間藝術(shù)生存境況為主題的影像作品,本身能賦予民俗文化新的生命。
(二)適應(yīng)社會發(fā)展潮流,增強(qiáng)民俗文化的傳播力
近30年來,技術(shù)與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讓中國社會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消費(fèi)文化、民間文化融合并存,快節(jié)奏的生活使人們在閑暇之余更愿意尋求簡單直接的藝術(shù)消遣。直觀的圖片、影像帶來的感官刺激顯然更能迎合年青一代的審美追求,傳統(tǒng)藝術(shù)飛速走向沒落成為不可回避的社會現(xiàn)實(shí)。但是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帶有鮮明特色的傳統(tǒng)文化和民間藝術(shù)有其獨(dú)特的存在價(jià)值,它是任何一個(gè)國家區(qū)別于其他國家的鮮明標(biāo)志,它是諸多流行文化創(chuàng)作的素材庫和靈感源泉。
在社交媒體盛行的今天,《老腔》《百鳥朝鳳》等這類傳承民間藝術(shù)、抒寫民族精神的影像作品因其厚重的文化意蘊(yùn)與歷史使命感,受到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與好評,他們通過個(gè)人社交平臺積極推薦宣傳,使作品贏得廣泛關(guān)注,再憑借新媒體交互式轉(zhuǎn)發(fā)、幾何式傳播,大大增強(qiáng)了影片及民間藝術(shù)的傳播力。
總而言之,影視作品中民俗元素的構(gòu)成是豐富而復(fù)雜的,能夠巧妙傳達(dá)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意圖,在影像敘事過程中起著關(guān)鍵性作用。民俗文化在影視劇中的恰當(dāng)呈現(xiàn),是導(dǎo)演用個(gè)性化影視語言詮釋中國民族精神、展現(xiàn)民族特色的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