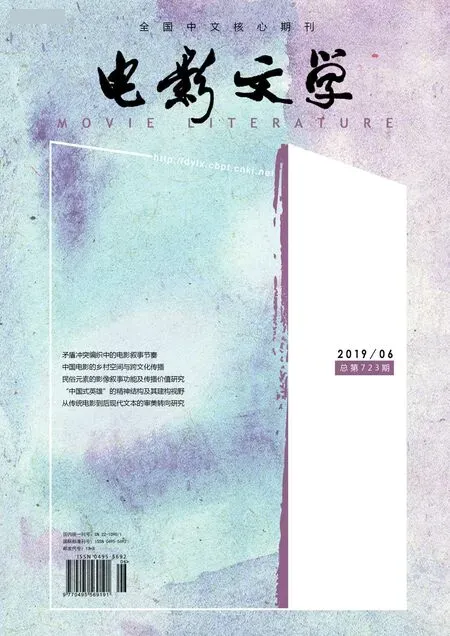中國早期電影國族主義遮蔽下的女性困境
徐雅寧 (西安外國語大學 藝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8)
清末民初時期的中國要在30年之內完成西方300年的任務,所以將一些社會進程予以提速及整合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地位卻是截然不同的。政治革命,擁有毋庸置疑的話語權威,對包括女權、啟蒙等在內的社會革命發號施令,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偏重個體解放的社會革命的訴求和內涵。正如李澤厚所言:“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斗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所有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饑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體權利的注視和尊重。”[1]
與西方女權運動相比,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缺乏性別立場鮮明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可以被看作是后發現代性國家反抗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入侵的抗爭在性別問題上的一種體現。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女性解放成為反抗殖民入侵、爭取民族獨立的一個子命題,女性解放在更廣闊的層面被納入到民族解放的軌道中。
由于與民族國家話語的聯姻,導致了中國早期電影中性別論說的豐富內涵和復雜糾纏。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民族國家對婦女群體的壓制和許諾,也可以窺見婦女群體及女性個體對民族國家的屈從和反抗。
一、去性別化:女性作為苦難民族的隱喻
自鴉片戰爭以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帶來的救亡與憂患意識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切身性難題。在這種環境中誕生并成長的中國電影,就不能僅僅當作一種單純的電影創作來看待,在它的文本中呈現著當時非常復雜的文化現象。中國早期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大多作為一個政治符號存在于文本中,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形象對應著中華民族的現實境遇。
在清末民初時期,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異族王權的腐朽促發了國族主義的劇烈上升,這使得文藝作品中的女性身體成為國族話語策源地。在當時的電影創作者看來,女性形象承載了文化歷史所賦予的“可觀看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起注意和同情,所以女性的身體反復承載著苦難、卑賤與被侵占的想象。
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剛剛走出萌芽階段,這一時期的電影創作首先追求的是技術上的成熟和敘事上的完整,以求在外國電影的傾軋之下能夠尋得立足之地。但這時的一些電影已經開始在蹣跚學步中關注現實,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進行了曲折的反映。比如《大義滅親》中的財政總長梅國魯私借外債導致國家權利喪失,《愛國傘》中的富商傅卜仁置災民于不顧,賣國借款,《誘婚》中礦物會辦席頌堅為一己之力,將中原地區原油開采權賣給“野心國”,《偽君子》中的劣紳史伯仁為了競選市長,將“全市交通權”賤賣給了“口木公司”等,以及《秋扇怨》《不如歸》《揚子江》中涉及了軍閥混戰、“與鄰國開兵端”等背景,呈現了封建階級、地方軍閥與外國勢力相互勾結,賣國辱權,傷害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現實。這些影片中的女性角色都有著悲慘的命運,但是造成其悲慘命運的直接原因更多指向了封建腐朽思想所導致的愛情悲劇上,其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控訴和亡國滅種的警醒是比較曲折和間接的。將女性悲慘命運與國家危亡勾連起來的敘事模式進入20世紀30年代才逐漸明朗起來。
進入20世紀30年代,民族矛盾日趨尖銳,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之后,反帝救亡的呼聲空前高漲,這種呼聲自然也反映在新生的電影創作中。更重要的是,在左翼進步影人直接參與到電影創作之后,電影的教育和戰斗功能更加凸顯,批判帝國主義侵略、號召大眾民族救亡成為這一時期電影創作的一大主題,正如左翼影評家王塵無所說,這一時期的中國電影“從一般娛樂轉變為民族解放的武器”。[2]
但是受制于上海被殖民狀態的現實困境以及各種電影審查制度,當時的電影不能夠直接表現帝國主義、國民政府、各地軍閥、封建勢力等對中華民族的傷害,只能通過巧妙的藝術構思,在災難深重的國土與遭受折磨的國民之間建立起一種隱喻的聯系,以起到暴露社會黑暗、呼吁奮起反抗的效果。《馬路天使》一片中歌女小紅演唱《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的兩個段落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片段,通過聲音、畫面、剪輯三位一體,隱晦地表達了創作者的愛國思想。小紅在茶館演唱《四季歌》,伴隨著第一段“春季到來綠滿窗,大姑娘窗下繡鴛鴦,忽然一陣無情棒,打得鴛鴦各一方”的歌詞,畫面中切入的是炮火連天,兩軍對壘的場景,間接介紹了女主角小紅的身世,也借小紅的歌唱抒發對日本侵略者的家仇國恨,傳達了進步影人號召民眾群起抗日的硬性主題。類似的人物設定還發生在《天明》中的菱菱、《船家女》中的阿玲、《火山情血》中的柳花等角色身上。通過女性角色們備受摧殘的身軀,中國早期電影隱晦地表達了對當時中國被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封建勢力等壓榨的現實境遇的關注,女性身體被新式知識分子整合進家國敘述中,成為國家和民族的象征符碼。
但是這里要指出一點,這些電影在描寫這些受難女性形象時存在著很明顯的唯美化和情色化傾向。在這種唯美化、情色化描寫中,女性的個人痛苦以及抗爭和犧牲常常被浪漫化處理了,反派角色對于女性肉體的侵犯,象征著帝國主義和封建舊勢力對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女性的犧牲和反抗也升華為一種國家的使命。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女性所遭受的苦難經歷和慘痛感情卻被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了。正如當時一些男性詩人的詩詞中所寫的,“最是令人忘不得,桃花血染玉肌紅”;[3]“我愛英雄猶愛色,紅顏要帶血光看”。[4]這些悲慘女性的身體受難經歷被避而不談,女性的受難身體被作為“看客”的男性電影創作者加工成一種可供凝視的極端美學體驗。然而,女性本身卻變成了一個“空洞的能指”,僅僅作為一種投射男性欲望想象的載體呈現在大銀幕上,進而提供一種隱藏在宏大主題之下的審美愉悅。
二、姿色救國:男性賦予女性的歷史使命
在列強環伺、亡國滅種的危急環境中,中國社會尤其是上海的十里洋場充斥著一種躁動和奢靡的末世情緒。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女體和革命或許是最具刺激性和煽動性的噱頭。正如進步影評人柯靈在評價當時的電影廣告時說的,“利用宣傳文字,信口雌黃,說得天花亂墜,來欺騙一部分淺視的觀眾,或者專門在廣告上運用各種性誘惑的詞句,如什么‘香艷肉感’‘酥胸坦雪’‘玉體橫陳’‘十六歲以下的童子禁止觀看’等,來吸引性欲狂的小市民觀客,但近來常常引用‘愛國’‘革命’‘義勇軍’等刺激興奮的名詞了”。[5]
在借助女體的損害激發起大眾對國土破碎的憤慨之后,如何使女體為革命、救國服務是中國早期電影創作者所著力思考的問題。這種革命進行時中的性別敘述,在消費了女性所遭受的災難之后,開始征用女性的容顏和身體。
伴隨著自清末以來婦女解放思潮的推進,在當時中國的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中出現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對這些女性形象加以深入分析會發現,在這些形象所彰顯的女性自身價值之上,始終籠罩著另一種高高在上的價值——即國家和民族的利益。1928年5月,以籌款支援北伐戰爭為由,電影界興起了一股“以腰救國”的風潮,當時一個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阮玲玉以腰許國》的文章:“摟腰救國之議既成,某君登女星阮玲玉之門請求加入。阮曰:以腰求利,舞女也,非我輩燦燦之星所能為,請君勿再羅索,否則面斥莫怪。某君曰:跳舞大會之充當舞女,其價值非尋常舞女可比,蓋一則為國,一則為個人生計也。為國而犧牲其人格,愛國也。阮玲玉挺身而起,慨然而言曰:我愿以腰許國矣。”[6]
在當時的古裝片創作中,幾乎毫無例外地強調了片中女性主人公寧死不屈、舍生取義的愛國氣節,以起到喚醒民眾、號召救亡的作用。這在當時的電影宣傳中有著明顯的體現,比如《明末遺恨》的廣告詞寫道:“俠妓殉國,嚼舌以死,一代文士,慷慨就義,忠義歷史愛國戰事古裝巨片。”[7]新光大戲院為《賽金花》發布的廣告,突出賽金花“以一介弱女挽全城浩劫,憑兩片櫻唇,救百萬生靈。近百年來一頁痛史,女性群中一代奇人”。[8]天一公司為《木蘭從軍》的廣告說“花木蘭代父從軍,千古播為美談”,稱贊花木蘭“以一弱女子居然能有這般偉大的懷抱,實可謂千百年來女界的唯一榮光”。[9]
以“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為分界,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電影在表現女性的救國行為時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20世紀20年代的電影中,女性的革命救國行為多與報父仇或報夫仇結合在一起,鼓勵女性救國的思想被嫁接到傳統“三從”倫理上。在號召女性參加革命的社會動員中,電影創作者一直在凸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女”“烈女”情愫,不斷賦予女性的生命與犧牲以道德/政治意義。在當時的中國,救亡圖存是一種不容置疑的國族權力話語,意味著一種權威話語權力。通過將“孝女”“烈女”的復仇故事與對于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的憂患意識結合起來,電影成為具有教育功能和宣傳效果的文化資本。
《大義滅親》中,梅麗蘭得知了抓走愛人鄭民威的叔父梅國魯也是害死其父親的兇手。梅麗蘭攔住總統的汽車“告御狀”,將財政總長梅國魯賣國借債的惡行暴露出來,這一行為同時達到了報父仇、救愛人、救國家三個目的。《誘婚》中,高云英為了青梅竹馬的愛人史裴成,偷到了席頌堅將煤油礦產出賣給“野心國”的證據。《孝女復仇》中,胡氏女子的父親曾經和無良軍閥武尚讀同為清末革命黨,武尚讀出賣胡父,導致胡父被殺。胡氏女子為了報父仇,先是嫁給了武的衛隊長為妻,以接近武。之后,又在武的納妾之夜,假扮成新娘,刺殺了武。《和平之神》中,甲乙兩省軍閥屯兵邊界,大戰一觸即發。凌云飛奉乙省督軍之命,前往甲省和談,卻被甲省好戰軍官扣押。凌的未婚妻林素薇帶著妹妹前往甲省營救,利用計策救出了未婚夫,并且向甲省督軍表明了和談意愿,避免了戰爭。《北京楊貴妃》中,黃正華集家仇國恨于一身,欲刺殺趙大帥,卻不幸被捕。被趙大帥霸占了的名伶楊小真一直愛慕黃正華,為了營救黃正華不惜以身犯險。這種敘事手法體現了社會轉折時期新舊思想相互沖突、相互妥協的特殊文化生態,為父/為夫而甘愿自我犧牲的女性形象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父愛”/“夫愛”思想的綿延,它的價值和內涵都以從父/從夫為基礎的儒家價值理念為根源。由此,在“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傳統無所寄托的時刻,知識分子的革命想象就通過對“為父報仇”的行為以及充滿浪漫色彩的“革命情侶”摹寫而表現出來。
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中出現了一些新式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的人生價值的實現開始脫離傳統思想中“家庭”的束縛,不再滿足于為人女、為人妻,而是為了某種理想或主義,為了民族利益而奮斗。比如《三個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貞,《女性的吶喊》中的少英,《現代一女性》中的安琳,《新女性》中的阿英,《黃金時代》中的張小妹,等等。雖然這些女性角色在片中大多戲份很少,基本上都是以一種“政治符號”存在,但是體現出對女性的統屬權開始從“家庭”向“國族”的移交。
三、男性書寫下女性性別主體的缺失
梳理清末民初時期的中國女性主義思潮,會發現兩個生發點:從帝國主義殖民的框架中追溯,有一個“西方”的源頭,即中國的女性主義思想發生自帝國主義入侵的刺激;從現代民族國家的框架中追溯,則有一個“男性”的源頭,即中國的女性解放直接來自男性知識分子的倡導。
受此影響,中國早期電影的女性形象書寫表現出一種向前遞進的演進過程:首先是“受難者”形象,以此象征危急時刻的國族;之后是“革命覺醒者”,以起到警醒大眾、奮起反抗的效果;再之后是“革命參與者”,協助男性完成革命救亡的歷史使命。這一演進過程在《大路》中茉莉這一角色身上體現得十分清晰,導演孫瑜巧妙地將音樂、影像和新聞資料片結合在一起,其藝術構思在今天看來仍屬上流。茉莉為筑路工人演唱《新鳳陽歌》,伴隨著第一段歌詞:“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畫面上出現的是無數的災民背井離鄉逃難的場景,其中穿插著幼兒哭鬧、老人疲憊的特寫鏡頭。第二段歌詞:“說鳳陽道鳳陽,鳳陽年年遭災殃。堤壩不修河水漲,田園萬里變汪洋。”畫面上是洪水泛濫的影像,無數房屋被浸泡、倒塌的悲慘景象。第三段歌詞:“說鳳陽道鳳陽,鳳陽百姓苦難當。從前軍閥爭田地,如今矮鬼(筆者注:即日本侵略者。當時國民政府審查嚴苛,電影中不準出現日本、東北、侵略等字詞)動刀槍。”畫面中呈現出的是慘烈的戰爭畫面,其中一個仰拍坦克履帶從上而下壓下來的特寫鏡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到這里,將個體女性所遭受的磨難與苦難的民族聯結起來,完成了第一個階段的任務。之后,茉莉運用智慧和身體,從賣國賊家中救出了被關押的金哥等人。片尾,茉莉脫下了旗袍等女性服裝,穿著工裝加入了男性拉鐵磙的隊伍,并且加入了男性演唱《大路歌》的大合唱中:“壓平路上的崎嶇,碾碎前面的艱難!我們好比上火線,沒有退路只向前!大家努力,一起作戰!大家努力,一起作戰!背起重擔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
以《大路》為代表,中國早期電影中的女性響應革命的召喚,在男性導師的指引下完成了獲救和成長,并獲得了一定的革命主體性,但女性自身的性別主體性卻逐漸淡化直至被完全遮蔽。女性被解救出來,在走上自我解放和解放同胞的革命之路的同時,自身的性別意識卻全部被國族意識所取代。當民族主體和性別主體二者不在一個水平面上,而是構成了一種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時,企圖超越男性/國族“主體”去尋找中國女性的“性別主體”是不可能實現的。換一個角度來講,也正是借助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男性/國族話語的不斷建構和再構,中國女性才逐漸形成了特定類型的客觀形象和主觀認知。一旦將男性/國族“主體”所賦予的意義抽離,所謂的“性別主體”也隨即成為一個空洞的能指而不具備任何實際意義。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而言,在中國早期電影中成為一種去性別化的文化符碼。
相對于男性穩定的自我而言,女性可以根據不同需要而被賦予不同的身份,并依據不同的身份被賦予不同的價值。從上述影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要么被男性征用成為指向政治、經濟或生理目的的工具,要么成為掩飾男性錯誤的替罪羊,即所謂的“禍水紅顏”。而女性作為歷史的親歷者、體驗者和創造者的身份被抹殺得一干二凈,作為歷史敘述者的資格也被徹底剝奪,只能無聲地等待并接受男性的“書寫”。
自清末以來,女性被先后賦予了“新賢妻良母”“國民母”“救國英雌”等多種身份,這在當時的電影中都有所體現。這些身份始終貫穿著男性的民族國家對女性一如既往的期許和詢喚,雖然在外延上有著不同的邊界,但是其內涵都是一樣的。從女性在整個家國敘事中的位置來看,她們始終是協助男性實現救亡圖存理想的從屬性力量。正如《馬路天使》中小紅唱的《四季歌》的結尾處,“血肉筑出長城長,奴愿作當年小孟姜”。這些銀幕形象所體現的仍然是女性自我意識面對強大的父權時的退守和臣服,所不同的是父權被諸如民族、革命、救亡等置換了。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由男性主導的話語體系中,女性或許連書寫客體都算不上,她們只是書寫的場域。在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男性在女性身上書寫著關于國族的“宏大敘事”,在救亡圖存的社會現實的名義下,女性自身的性別困境成為無人顧及的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