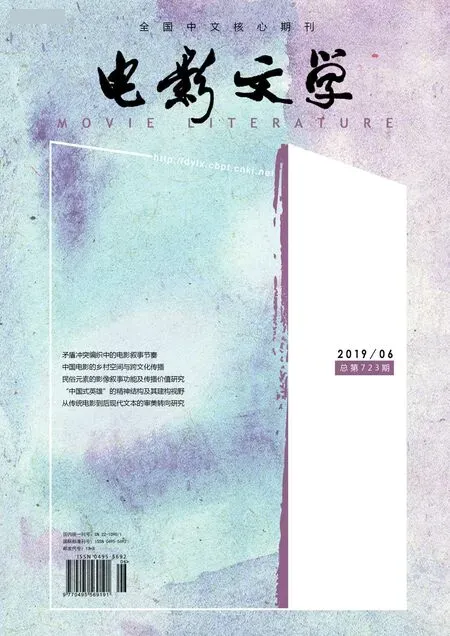從梅蘭芳的電影生活看他的電影觀
沈后慶 (廣西藝術學院 影視與傳媒學院,廣西 南寧 530022)
梅蘭芳愛好廣泛,除了擅長京、昆之外,對于其他藝術形式,諸如字畫、電影乃至舞蹈、體育等幾乎無所不涉,無一不通,海納百川的胸襟對他藝術水平的提高毋庸置疑,也是形成其自成一格“梅派”藝術的重要基石。考察梅蘭芳近現(xiàn)代以來的從藝、商演生涯中,可以看出他在戲劇商演之余,和電影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從最初20世紀頭10年代抱著娛樂的態(tài)度觀劇,到20年代的初次“觸電”,再到30年代出訪考察以及頻繁與中外電影人士的互動,再到40年代攝制成真正意義上的有聲影片,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50年代拍攝關于本人的紀錄片,梅蘭芳在不斷演戲、觀劇和電影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電影藝術的獨特魅力,并從感性到理性,形成了基于戲劇基礎上的電影觀念。具體而言:
一、電影的審美、教化功能高于娛樂功能
在一封答復美國記者阿維蘭脫女士詢問梅蘭芳對中國舊劇和電影看法的信件中,梅蘭芳給予了這樣的回答:“中國各種舊戲,演唱已久,而仍能受社會之歡迎,此誠極奇妙之事,推原其故,當不外乎舊劇之演作唱白,乃至喜怒哀樂種種表情,均有一定之規(guī)則,而日成一種特殊之技術,觀劇者能于此種特殊之技術,積有經(jīng)驗,以了解演唱之意思,斯能感受趣味,故觀眾對于舊戲,于特殊之技術,批判各伶人演唱之優(yōu)劣,伶人亦于此特殊技術中,研究其變化,以充分發(fā)現(xiàn)劇之情緒,臺上臺下互相呼應,故戲劇雖舊而趣味常新,舊劇所以維持不敗,此實最重要之原因也。”[1]“且舊戲有以善為目的者,如勸善懲惡,教忠教孝之類,有以美為目的者,如注重歌舞服飾之劇,及描寫悲歡離合之劇等類,此與社會生活之關系,頗為切妥,亦其持久之原因。至鄙人所扮演角色,重在將各種婦女性質(zhì),恰如其分以表現(xiàn),而對于婦女等角,所以幸負時譽者,則以古代裝束本為最美也,鄙人素嗜電影,歐美各國有名之影片來華演映,幾無不往觀,就中尤欣賞者,為葛力夫氏所編之《賴婚》,其余電影如星,如飛爾班瑪麗辟克福假波林康斯鈿羅克諸伶之佳,亦極喜觀之,鄙人亦曾演映電影,認為極有興味之一事,他日甚愿投身電影界,以促進中國之電影事業(yè)也。”[2]
概括而言,梅蘭芳對于中國舊劇何以富有魅力的理解,強調(diào)了三點:第一,中國戲曲具有程式化之美,對演員技術要求很高;第二,戲曲具有教化之功能;第三,強調(diào)了戲曲角色,尤其是旦角服裝之美。簡言之,就是戲法技術之高,教育功能之大,舞臺裝束之美。梅蘭芳還以觀看《賴婚》以及列舉當時西方電影明星為例來證明自己對電影的喜愛。梅蘭芳還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電影是一門“極有興味”的藝術,表達了投身電影的意愿,但他并沒有過多談到電影藝術的特點,更沒有討論電影和戲劇的區(qū)別,原因在于一則當時他對于西方電影尚停留在觀劇的興趣層面之上,自身研究、實踐不多;二則西方電影剛剛興起,處于默片時代,無論是拍攝技術,還是表導演甚至劇本的水平,尚未達到戲曲的高度。
需要指出的是,梅蘭芳固然認為電影有娛樂的功能,但那種不講究藝術性的電影不在梅蘭芳的喜愛名單之列。1930年梅蘭芳訪美之時,正是有聲片興起的時代,電影藝術和風格都較之默片時代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對于商業(yè)至上的歌舞片梅蘭芳不是特別喜歡,之后好萊塢出現(xiàn)了大量的文藝片和兇殺暴力恐怖片,比較之下,梅蘭芳表達出對后者“這類電影的興趣不大”,[3]32可見梅蘭芳的電影觀之一,認為電影的教化、審美功能高于娛樂功能。
二、電影藝術的獨特性
梅蘭芳在回復外界認為他將把《霸王別姬》一劇拍攝為有聲電影的傳聞時,就戲劇攝成電影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蓋舊劇之作風,與影劇絕對不同,將來攝制是否,須將舊劇場次及其表演,稍加修訂,亦為一大問題,在片上發(fā)音,與說白及歌唱方面,業(yè)告成功,然以制舊劇,凡所表演,一舉一動,均須受音樂之節(jié)奏,則當如何使有更進一步之成功,方能益臻美善,故目下關于收音及戲劇,君須俟研究滿意后,再開攝制。”[4]
隨著拍攝經(jīng)驗的增多,梅蘭芳對電影藝術獨特性的認識逐步加強。1924年在拍攝了《木蘭從軍》和《黛玉葬花》后,他就認為戲曲舞臺時空變換自由,苑囿于當時電影技術并不完善,時空變化大的戲劇就不適用于拍攝寫實的電影,所以他說:“我覺得京戲里像《黛玉葬花》這一類故事題材,比較適合電影的要求,可以使演員不受約束,盡量發(fā)揮。”[3]21
20世紀30年代以來,梅蘭芳對電影藝術的理解越發(fā)深刻。1935年訪蘇期間,當時梅蘭芳和電影導演愛森斯坦合作拍攝有聲影片《虹霓關》中東方氏和王伯當對槍歌舞一場。愛森斯坦說:“這次拍電影,我打算忠實地介紹中國戲劇的特點。”對此,梅蘭芳就表達出對拍攝此劇的看法:“像《虹霓關》這場‘對兒戲’,有些舞蹈動作必須把兩個人都拍進去,否則就顯得單調(diào)、孤立。所以我建議少用特寫、近景,多用中景、全景,這樣,也許比較能夠發(fā)揮中國戲的特點。”[3]51這些建議的合理成分就被愛森斯坦予以了肯定。其實梅蘭芳第一次拍攝的電影是昆曲《春香鬧學》和京劇《天女散花》,也是基于認為這兩出戲身段較多,適合拍攝電影這個原因。
1948年拍攝《生死恨》時,因為此劇不是舞臺劇紀錄片,而是電影藝術片,布景就需要認真設計,對此,梅蘭芳就給導演費穆提了很多意見。梅蘭芳說:“《生死恨》是宋朝的事,在用景方面,更要注意這一點。但我并不是說要按照時代來設計布景道具,當然還是應該根據(jù)戲劇的習慣來適應電影的要求。”[3]69在以后的拍攝中,導演費穆就對梅蘭芳的觀點給予了充分考慮。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文化部準備給梅蘭芳拍攝一部大型彩色紀錄片,梅蘭芳認為要想拍好這次的影片,必須注意以下幾點:“首先是劇目問題,有些戲雖然在舞臺上很出色,但未必適合于拍電影,因此要選擇合乎電影藝術要求的劇目。另外,有關布景、化妝、服裝、表演程式等方面的許多問題,也都要仔細推敲。”[3]80在以后實際拍攝過程中,梅蘭芳更是從劇本、特技、色彩、化妝等方面都提出了很有價值的意見。比如他說:“我總覺得,電影藝術表現(xiàn)手段的有利條件就在于能運用鏡頭的遠近和不同的角度來強調(diào)劇本中突出的思想,贊成什么,反對什么。”他還舉出特寫鏡頭在《宇宙鋒》中的運用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梅蘭芳還認為“有些戲在舞臺上不好處理”,但是只要導演和攝影師熟悉戲曲舞臺的特點和結(jié)構,“靈活運用鏡頭,使電影藝術與戲曲舞臺藝術巧妙地結(jié)合起來,做到水乳交融,似斷還連,互相促進,互相補充,就能使二者的結(jié)合臻于完善的境地。”[3]105-106至于如何把戲曲寫意、洗練的特點和電影寫實的特點有機集合起來,就需要雙方工作者共同研究解決。
三、電影的局限性
梅蘭芳滿懷對電影的喜愛和熱情,也認識到電影具有獨特的藝術特點,但不意味著他對電影發(fā)展的盲目迷信。1935年梅蘭芳赴歐回國抵達香港時發(fā)表了談話,對歐洲各國的戲劇給予了評價,認為通過對蘇聯(lián)二十幾個劇場的參觀考察,“只有一家演出宣傳意義之戲劇耳”,意謂戲劇替無產(chǎn)階級宣傳的時代過去了,已走上了百花齊放的道路,并對當時輿論界過分夸大電影發(fā)展態(tài)勢的聲音給予批評。他說:“至于電影有占據(jù)舞臺劇取而代之之問題,則余等以為戲劇有其固有之藝術,如顏色方面,立體方面,感覺方面等。電影雖然進步,似對‘取而代之’方面,有不可能之事實,何況電影可以剪接修改,而戲劇一經(jīng)演出,即不可收回乎。”[5]這種觀點梅蘭芳在蘇期間和電影導演愛森斯坦交流時候就曾表達了出來。梅蘭芳說:“電影雖然可以剪接修改,力求完善,但舞臺劇每一次演出,演員都有機會發(fā)揮創(chuàng)造天才,給觀眾以新鮮的感覺。例如我在蘇聯(lián)演《打漁殺家》就與在美國不同,因為環(huán)境變了,觀眾變了,演員的感情亦隨之而有所改變,所以電影對舞臺劇‘取而代之’的說法,我是不同意的。”[3]54
無論是訪美還是游歐,梅蘭芳都和電影人有過密切接觸,電影藝術也隨著科技發(fā)展而強勢崛起,但是梅蘭芳基于對包括中國戲曲在內(nèi)的戲劇本體的深刻理解,清醒地認識到電影較之戲劇有很多的局限性,尤其從戲劇藝術固有之美處與電影藝術進行觀照,從而得出電影不可能取代戲劇的結(jié)論,這種觀點在新媒體如此發(fā)達的當下,仍然是經(jīng)得住考驗的。
四、電影傳播的重要性
梅蘭芳認為電影藝術可以為我所用,豐富自己的舞臺藝術。梅蘭芳說:“在早期,我就覺得電影演員的面部表情對我有啟發(fā),想到戲曲演員在舞臺上演出,永遠看不見自己的戲,這是一件憾事。”他還舉出楊小樓也有這樣的想法:“你們老說我的戲演得如何如何的好,可惜我自己看不見。要是能夠拍幾部電影,讓我自己也過過癮,這多好呀!”[3]3
有署名“聊止”的《梅蘭芳今后之事業(yè)》一文,對于梅蘭芳赴美提出期待:“一、考察歐美劇場狀況,及戲曲學校情形;二、赴電影中心之好萊塢,考察電影事業(yè);三、表現(xiàn)中國舊劇之奧妙,以及音樂行頭之美。”“歸國后,梅應建設之事業(yè),一、建筑大劇場;二、開設戲劇學校;三、組織電影公司。此于三項中,為著手改良中國戲劇與電影之準備。”[6]可以看出隨著對電影認識的深入,梅蘭芳有了投身電影界的愿望,外界也對此多有希望。
1930年梅蘭芳在美考察了好萊塢,看到了美國電影的發(fā)達狀況,更加激發(fā)了他投身電影界的熱情,尤其對攝制有聲電影很是期待。“他說,要演制有聲電影的主因,不是希望銷流在美國里的,他的志愿是演制聲色雙全的影片,貢獻給居住在中國邊疆和孤寂的村鎮(zhèn)城邑里的居民,好讓他們有機會領略本國古派名貴的戲劇呢。梅蘭芳說,一個伶人,就是消磨了終身的時日,也不能夠周游中國境內(nèi)一萬五十萬方里以表演他的藝術的,這回卻好利用西方新式的機械做成彩色而發(fā)聲的影片,把中國世代傳下來的名貴劇本——有些竟是原始于第三第四世紀的了——傳遍遐邇呢。”[7]
如果說梅蘭芳早期對電影的實踐出于愛好和商業(yè)需要的話,那么隨著對此項藝術認識的深入,他一方面認為戲劇較之電影有無可取代的地方,一方面也認識到電影作為傳播媒介的威力,尤其是電影的可復制性,為戲曲藝術的傳播打破時空限制提供了可能。隨著年齡漸長,特別是梅蘭芳歸隱復出后,自覺受制于身體因素的限制,舞臺藝術在演出、傳承上都是個很大問題。在漫畫家豐子愷對梅蘭芳的訪談中,梅蘭芳就表現(xiàn)出攝制影像的方式保存自己舞臺表演藝術的迫切感。[8]在他預計拍攝的宏偉計劃中,包括完整的《貴妃醉酒》一劇,《霸王別姬》一出,以及將《洛神》《思凡》《生死恨》《穆天王》等劇的緊要場次。[9]后來在選定《生死恨》作為中國第一部五彩電影的拍攝劇目,有記者問起“此片問世之動機”時,梅蘭芳說:“我這次拍演電影有兩種目的:第一點是許多我不能去的邊遠偏僻的地方,影片都能去。第二點,我?guī)资陙硭鶎W的國劇藝術,借了電影,可以流布人間,作為我們下一代的藝人一點參考的材料。”這和他訪美后的想法是一致的。導演費穆也說:“梅博士和他的時代的伙伴,——例如周信芳、蓋叫天兩位先生,——幾乎一致地有了這樣的警覺,他們認為當代的評劇家的任務,已不僅在登臺獻藝,供奉觀眾,也不僅在改革舊劇內(nèi)容,硬放天足,主要的,有意義的工作,不如把夠得上水準的演技記錄了,在夕陽黃昏,稍縱即逝的時候,留給人一點‘規(guī)矩’,給人批評和給人觀摩。”[10]
以梅蘭芳為代表的梨園藝人充分認識到了電影藝術的復制性在傳承后人方面具有獨特的價值,所以不遺余力,在有生之年攝制保存了大量的舞臺作品,使得后人能夠通過影像直觀感受到中國戲曲的魅力以及他們代表的流派風格,在當下戲曲式微的語境中,這種憂患意識對我們更具有警醒和借鑒意義。
五、結(jié) 語
從1920年拍攝《春香鬧學》《天女散花》一直到1959年拍攝《游園驚夢》為止,梅蘭芳始終和電影相伴,并在實踐中形成了自己對電影的獨特理解,作為一個戲曲演員,這點難能可貴。梅蘭芳對電影藝術的實踐,凸顯了他對新媒體、新藝術發(fā)展的敏銳感覺,尤其應當指出的,梅蘭芳認為隨著電影藝術的發(fā)展,戲曲電影也會發(fā)生革命性的變化。1958年梅蘭芳參與了蘇聯(lián)導演柯米薩爾熱夫斯基全景電影《寶鏡》的拍攝,他說:“我這次拍過全景電影之后,對用全景電影來表現(xiàn)戲曲藝術有些想法,覺得全景電影的鏡頭給演員的活動范圍較為自由,在表演時不必顧慮到動作是否會出畫面;雖然有兩條縫線,但容易避開,不致成為演員精神上的負擔。我想今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這兩條接縫的痕跡是有可能完全消滅的。”梅蘭芳認為:“全景電影適宜于拍攝風景和大的群眾場面,在各種電影形式中是別具一格的。”1960年梅蘭芳第三次赴蘇訪問,看到了環(huán)幕電影,這讓他“興奮不已”[3]134。梅蘭芳還說:“隨著電影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發(fā)展,如何運用寬銀幕電影、全景電影,以至環(huán)幕電影來記錄和表現(xiàn)我國的古典戲曲藝術,都將逐一作為新的課題提到我們的面前,有待我們?nèi)崆樘剿骱团︺@研。”[3]166當下電影藝術發(fā)展已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也有力詮釋了梅蘭芳與時俱進的理念。
總之,梅蘭芳喜愛電影藝術,一方面為了觀賞,一方面為從銀幕上吸取藝術素養(yǎng)來豐富自己的舞臺藝術。從娛樂到實踐,從感性到理性,梅蘭芳的電影觀念始終與戲劇相互觀照,特別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梨園藝人,他固然認為戲劇藝術具有自己獨特的魅力,但包括唱片、電影等新興藝術的可復制性和傳播迅捷性都是舞臺藝術無法相比的。梅蘭芳對電影藝術的實踐,有利于其藝術的傳播,對他海上形象的樹立具有重要作用。梅蘭芳等藝人灌制的唱片和攝制的戲曲影片成為珍貴的資料,而他們保留聲音、影像,傳承藝術的想法富有遠見,更是值得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