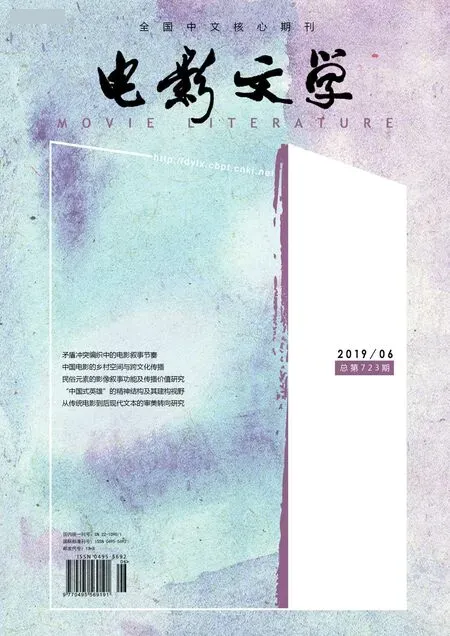《江湖兒女》的空間變異與性別辯證法
韓旭東 (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3)
《江湖兒女》的象征性敘事元素的運用體現了導演創作譜系內的自我互文意識,舊作中的物象/意象、場景、人物出現在新文本中的視覺/記憶“重復”,是創作者對此前作品的致敬以及對逝去時代的招魂。不同于賈樟柯此前創作譜系中對中國社會底層偏執化的影像記錄,新故事中男女之間辯證化的兩性關系、女性在社會/江湖空間中的身份與地位、女性角色身上彰顯出的忠、俠、義等精神是新作所譜寫出的主旋律。
二元對立指的是主體在獲得理性優勢的前提下,以審視、優越的目光將他者放在被支配的位置,“主體永遠處于優越的地位,客體只能作為主體的對立面而卑微地存在”[1],主客體之間是絕對的差異關系。道家哲學中的陰、陽二者則各占一極,事物隨時間的變化而發展,它的運動和發展是向對立面的轉化,沒有絕對的主客、高下之分。《周易》中陰始終處于陽一極之下是應然,陽凌駕于陰之上為“承”,而陰處于陽之上時則多為“乘”,體現出該書扶陽抑陰的思想。根據六十四卦中所涉及卦內二爻運動變化的狀態不同,陰有壓制陽的可能性與合理性。斌斌與巧巧分別代表陰陽格局中的兩極,他們之間的兩性關系體現了中國哲學“變”與“通”的思維模式。本文從陰/陽、男/女、主體/客體之間的辯證轉化入手,考察文本中的女性在建構性別主體意識時,與男性本體性別氣質的消解所構成的對位變化現象;在以性別政治的變遷為立論前提時,觀照兩性所處的江湖/社會空間性質的變異以及時代/歷史、空間/江湖、性別元素之間的互為關聯性。
一、作為側影的女性
第一個敘事組合段中的巧巧是作為斌斌的側影、附庸而存在的。就鏡頭技法而言,她多次出現在雙人中景、近景內,而鮮少有單獨給巧巧的特寫人物鏡頭。未建構性別主體意識/女性主體性時的巧巧不具備獨自占據單個畫面的資格,她是一個“不完整”的影子。該段落中的江湖空間是典型的男性陽剛世界,畫面的色調鮮艷、飽滿,鏡頭間剪輯的速度較快,它的內在核心是文本中多次復現的以關公銅像為代表的忠、義、信。民間的關公崇拜源自《三國演義》和宋代開始的關公戲,關羽自桃園結義后忠于弱勢的劉備和蜀漢,拒絕曹魏所給予的官職待遇。民間俠客因崇敬故事中關羽的忠義氣節,而將其尊奉為江湖規則的裁定者以及共同體的內在規約符號。
斌斌的江湖大哥地位、忠義信精神體現在處理裁決還錢事件、為二勇哥辦喪事、放走對自己行兇的年輕人等事件上。首先,老孫與老賈的還錢糾紛并未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而是被斌斌請出了關公銅像,對著江湖規矩的象征來裁決債務糾紛。糾紛的解決說明前現代、未完全被現代化的90年代江湖空間自有一套內部規則,遵守關羽信仰才能在這個封閉的空間中存活。其次,斌斌為二勇哥解決兜售別墅時遇到的鬧鬼謠言、在二勇哥的喪事上請來他生前最愛的國標舞演員表演以及安慰他的年邁老母與妻子,都體現出江湖朋友之間的責任與道義。最后,斌斌得饒人處且饒人,放走了誤用鐵棍打斷自己腿的年輕人,且沒有對他們趕盡殺絕,這體現了江湖中的晚輩一旦認錯低頭,前輩便會大度原諒其錯誤的寬容意識。斌斌雖身為大同黑社會的頭目,但并沒有打家劫舍、欺凌弱小,而是踐行了共同體內部的忠、信、義、仁精神。隱含作者通過對斌斌忠義精神的肯定,抒發了對前現代江湖空間、90年代民間規則的懷悼意識。
但吊詭的是,身為江湖中父輩的二勇與斌斌等人,卻被不守規則、大膽的子一代們顛覆了自身話語權威,并因此而喪命或受傷。這象征了隨著現代性時間的進展,子一代已經不再遵守父輩所留下的規則,他們睚眥必報、下手陰毒,“這幫年輕人不知深淺”。前現代江湖空間中的斌斌在大同當地有著顯耀的社會地位,解決朋友的困難時能夠呼風喚雨;且從是否要作為巧巧的家屬去新疆的態度上可以看出,身為陽一極的斌斌拒絕做陰/女性的附屬,他是空間內至陽的權力中心點。但男性表面的陽剛形象如同影片中放映的血腥暴力港片與香港金曲類似,男性氣質是一種被虛構出的意識形態。觀看電影時的斌斌將自己想象/重合為片中的黑幫老大,這種假想的鏡像/幻想被年輕人弒父/去勢般的毆打/斷腿所消解與嘲諷。此外,從煤窯廠因內部貪污而倒閉、老員工們被迫的搬遷、巧巧父親對廠長的不滿可以看出,故事中的江湖中人實際上也是由大同的社會底層民眾所構成,庶民們在國家大政方針、流動的巨型資本面前就是一群微小、無話語權的他者/弱勢群體。而第一段落中的巧巧是作為一個賢妻孝女的形象存在的,從開場所使用的第一個跟拍無正臉長鏡頭到坐在斌斌身旁抽煙可以看出,此時的她是江湖大哥的附屬。斷腿事件后的斌斌象征著陽一極的權威開啟了辯證過程中的轉化階段,腿/菲勒斯被打斷是他在影片中的第一次被閹割/去勢。所以,此前一直是被長鏡頭背影、雙人中景中附庸的巧巧,在被斌斌教會使用槍的那一刻,開始走向建構性別主體意識的起點,即陰陽即將開始轉換、陰對陽的吞噬。
二、漂流的女性主體
從巧巧開槍保護斌斌的時刻起,女性開始擁有獨自占據單人特寫鏡頭的資格。開槍事件中的單人近景與中景鏡頭一直自車內跟拍巧巧到車外,長鏡頭水平勻速移動,巧巧干練的馬尾辮、手開扳機對天空開槍等細節說明此時的女性已經開始建構性別主體意識。巧巧在得到男性的啟蒙/開槍教學后,理性意識和積極自由權表征了她的主體性內核:主要體現在保護斌斌的責任意識、主動承擔非法持槍的罪名、在獄中被監禁五年,此時巧巧為斌斌所承擔的是戀人之間的情。但女性主體性生成的時刻,卻是男性權威被消解,向陰一極轉化的開端。斌斌因被女友保護失了面子、入獄后昔日風光不再等自卑心理,出獄后也并未曾探視過巧巧,離開大同,遠走他鄉。
第二組合段中的江湖空間不同于第一段中的濃墨重彩、血腥暴力、暗為主色調,男性為中心點、鏡頭快速剪切等,該部分還原了《三峽好人》中的以白、黃、灰等冷色系為基礎濾鏡色彩,單人近景鏡頭隨人物在空間中移動的步伐慢速切換。巧巧在山西、湖北、新疆之間的移動,說明個體通過個人的積極自由選擇權開始了不同空間之間的漂流。如果說前現代空間中鐵板一塊式的“捆綁”隱含了對空間中人的保護作用,那么新空間、空間之間的漂移/個體化現象則是以讓度個體的人身安全與提高風險概率來換取女性更多的選擇與行動自由。[2]巧巧所遭遇的風險包括人身、財物安全以及情感的創傷。她在長江客船上被假女基督徒偷走了錢包和身份證,以及搭乘摩的時遭到司機的性騷擾和言語猥褻都說明異鄉人、女性是作為新江湖空間中的弱勢而存在的;但新空間的風險也是“娜拉”們成長過程中建構性別主體意識的外在刺激力。巧巧行走江湖時對司機假意應承,隨后卻支走了他并騎走了摩托車,只留下司機一人在雨中哭喊;身上沒有錢卻用一朵玫瑰花裝作新婚新娘的同學,在婚禮上騙吃騙喝;以裝作被騙少女的“姐姐”,故意騙取婚外情大款們的錢財,來解決自己錢包被偷的燃眉之急;再遇女騙子時先幫她打走了圍毆的眾人,隨后向其索要身份證;失戀后意圖尋找到新的開始而跟隨“教授”前往新疆,亮明囚徒身份而遭到警惕后果斷地離開滿嘴鬼話連篇的小賣部老板/“教授”等個人抉擇都說明遭遇風險的“陰”之勢力不斷上漲,巧巧變成了行走于新空間內的江湖女俠。她亦正亦邪的選擇與行為也體現了在底層社會之間漂流與歷練來建構性別主體意識的行動需要來自民間的狡黠與智慧,民間/江湖并非是完全充滿忠義精神的存在,它也會藏污納垢,有著不為人所見的粗鄙與陰暗面。但總體而言,隱含作者肯定了她的獨立、自強乃至“行騙”,同情她被斌斌所辜負,獨自在社會上行走時的孤單與無助。
巧巧漂流/移動的前提是她對斌斌還有“情”,目的是為了找到他并詢問雖提前出獄卻一直消失的原因,以及為他們二人之間的“名”分討一個說法。而斌斌在武漢卻一直故意躲著她,無法面對自己男性氣質/權力被消解、被陰一極所庇護/壓制的現狀。此外,陽一極處于弱勢的原因是斌斌無法面對自己昔日的手下在當下的實力都超越了自己、自己只能躲在林氏兄弟的手下打工居無定所、開槍事件中自己是被女人所救、目前在異鄉混的境況大不如從前等。賓館會面中的一組雙人中景、近景長鏡頭的推移使用,歌曲《有多少愛可以重來》都表明了隱含作者同情斌斌當下的境遇以及對時間/舊時代不再“重來”的惋惜與傷懷。
三、陰性的她者世界
第三個敘事組合段中的巧巧已經覺醒/建構了性別主體意識,成為當下江湖空間中的核心與支配性人物,而男性/陽/斌斌卻淪為被巧巧庇護的對象,他是“陰”的附庸。該段落中以白、灰、淡藍等冷色為基本調的濾鏡以及多次對焦斌斌臉部的單人近景鏡頭等都凸顯了被去勢后的男性之無助狀態和落魄大哥晚景的凄涼;而對巧巧照顧斌斌時所使用的仰拍單人中景鏡頭、遠景空鏡頭中巧巧的入畫過程都意味著新空間中的女性是一個需要被人仰視的強大主體。
不同于舊江湖的忠、義、信精神和漂流過程中的風險、狡黠與智慧,當下的江湖空間是失去了規則與秩序的混亂所在。就人在空間格局中的位置而言,斌斌在棋牌室里并沒有自己獨立的處所,他需要借用廚子的臥室吃飯,并被廚子呵斥;斌斌昔日的部下老賈敢當面挑戰他的權威,意圖以拍賣他所坐的輪椅來羞辱他的顏面;棋牌館中的看客們通過代表現代化科技的手機,來“看”并在網上轉發老賈羞辱斌斌的過程,表明技術媒介之“眼”已經異化了昔日江湖中尊卑長幼的秩序與規則。對“囚犯”的露天展示與圍觀性羞辱,所造成的心理傷痛要大于來自肉體的懲罰。[3]坐在輪椅上、拄著拐杖行走、頭頂扎滿針灸、左手穿衣行動不便等身體的殘缺都說明了當下(2018年)性別意義上的“陽”已經變為權力格局中的“陰”,陰陽辯證過程的推動力以及變化的臨界點是無法扭轉的線性現代性時間。為了懲罰羞辱斌斌的老賈,巧巧把茶壺拍到了他的頭上。棋牌館中性別的“陰”是權力格局中的“陽”,斌斌也正是因為這最終的“羞辱”而主動離開巧巧,在微信語音中留下一句“走了”。隱含作者借單人近景、臉部特寫等鏡頭同情斌斌的晚年境遇,昔日江湖大哥的衰老說明了一切堅固的東西終將煙消云散;同時,隱含作者又用仰拍鏡頭、中景移動鏡頭跟拍巧巧在棋牌館中的左右逢源,都肯定了建構性別主體意識的江湖女俠之強大與自信。
四、結 語
綜上所述,一方面,就文本中人物之間的性別與權力關系而言,舊空間中的女性一直作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二者的性別身份與權力關系是“正常”的陰陽狀態;開槍事件以及尋夫過程中的巧巧開始由性別的“陰”轉化為權力的“陽”,而落魄、被去勢的斌斌則變為性別的“陽”、權力話語中的“陰”。最終,在最后一個組合段的權力敘事中,巧巧成為壓倒“陽”而獨立的“陰”,以貴柔守雌消解了斌斌的男性氣質。男女之間在性別位置、權力話語之間存在明顯的對位性變化,即一方通過吞噬、拆解另一方的存在而建構自我的主體意識。另一方面,三個敘事組合段中變化的是隨時間逝去而老化的人之心態及身體機能:從忠義江湖到風險江湖,再到性別江湖的變化過程實質上象征著“空間的時間化”變異。只有當它與生存在空間里的人、現代性線性時間發生互動關系時,空間才會反過來對人產生構造作用。